|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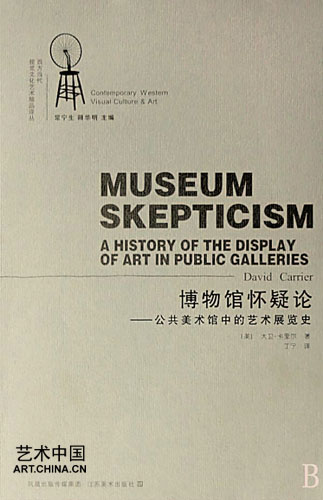
〔美〕大衛·卡裏爾著丁寧/譯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
2004-2006年三部大部頭的論文集的出版——唐納德·法拉戈的《把握世界:博物館的觀念》、貝蒂娜·麥克唐納的《博物館研究指南》標誌著博物館研究時代的到來。總共128篇文章及近2000頁的文本,並伴有些許的內容重復,(它)指向了跨越不同學科的關於學術的豐富界面——藝術史、歷史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博物館研究已經作為一個跨學科以及智性活力的樣板而出現。大衛·卡裏爾的《博物館懷疑論:公共美術館中的藝術發展史》新近被譯介的這本著作,無疑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經典之作。這本書恰好也是在2006年于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上文當仲介紹的著作屬於文集的話,此書是極具個人印記的經典論著。如果聽過這位學者激情澎湃的演説而又對比其著作或者文章進行回味時,我們不難發現這位學者在自如的説辭表像之下的嚴謹之風。作為著名美學家阿瑟丹托的弟子,當我們閱讀他的文章之時,我們往往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才能應對作者在文中所涉及到的大量原典及例證,伴隨著隨處可見的對一個實例的反覆論證,當然最常見的是與其美學訓練息息相關的思辨性的反思與質疑、閱讀卡裏爾的文本,我們似乎能一以貫之地感受到不同形式的質疑:對權威的質疑,對自身的質疑甚至對於質疑的質疑。《記住往昔:作為記憶劇場的藝術博物館》是卡裏爾的一篇精彩的論述博物館的文章,在文中,他反反覆復地陳述許多世界著名的藝術博物館的入口變換的故事,緊緊圍繞的中心便是“原位性”,筆者在這裡談到這篇文章是為了説明卡裏爾對博物館的關注的起始點也許就是“原位性”是他的興趣的核心,在《博物館懷疑論:公共美術館中的藝術發展史》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卡裏爾對這個核心問題的關注。他提及法國批評家卡特勒·梅爾坎西,此人對於拿破侖從歐洲其他國家擄掠的藝術品而在法國建立盧浮宮博物館表示質疑與不滿。“原位性”是不可替代的,即使藝術品是“原作”也於事無補,因為所劫掠來的藝術品並非在原始的情境當中進行展示。在另一篇論文《藝術博物館,老的繪畫即我們對於往昔的知識》這篇文章當中,卡裏爾花費了更多的筆墨來論述這個問題,文中討論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藝術家皮耶羅·弗朗切斯卡的名作《施洗者約翰》的陳列的歷史,本文的不同尋常之處是卡裏爾圍繞著一幅想像的畫作——《皮耶羅的〈施洗者約翰〉的旅行和苦難》。這同時也涉及到作者在《博物館懷疑論:公共美術館中的藝術發展史》當中對“時光之旅”的觀念,顯然作者是反對運用這個概念的。卡裏爾的對於博物館懷疑論者的一種反應,便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雖然藏品在物質上是相同的物件,但是其價值與意義會隨著時間以及處所的變換而隨之發生變化。引用漢斯伽達默爾的話,“對於一件藝術作品的真正意義的發現‘永不會停止’……因為真正的歷史物品根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個在由藝術家所創造的人造物品與其闡釋者之間的遭遇的投射。”因為那種所謂“創造性的遭遇”大多發生在藝術博物館,卡裏爾認為,去理解在物品和觀者之間進行調停的那種機構化的框架是一種強制性的方式。他非常熱切地想揭穿這樣一個觀念,即藝術博物館會像一台時間機器那樣發揮其功能,將我們帶回到往昔而且與遙遠的文明進行接觸。在卡裏爾看來,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夢幻,並且是一個我們需要摒棄的白日夢。
如果先閱讀完卡裏爾的這本著作的原典,再對照中文版進行比較,便是一個饒有興趣的歷程,正如譯者在譯後記當中所提及的,譯者在翻譯過程當中對原文當中的一些衍文進行了適當的處理。卡裏爾的中譯本序言也使此書增色不少,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讀者他寫作此書的過程與意圖,這可能是作為讀者而言所常常忽略的事情。比如卡裏爾在序言當中提及他的論述範圍只是討論他在美國以及歐洲所走訪過的藝術博物館。另外,我認為他在序言當中的一句話給讀者在閱讀此書的思路上以相當大的啟示,“拙著著重討論一個從歐洲文化中産生的特定問題,即古代大師的藝術如何依然讓公眾可以接近。”我想如果讀者注意這句話就較容易融入此書的思路當中。荷蘭學者米克貝爾對於博物館受到空前的關注的原因作出過解釋。她指出,“在過去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裏,人文科學對於自身的限定性有了越來越充分的意識,這種限定性包括其學科界限的武斷性、人文學者的大量工作所依賴的美學中所涉及的、常常是排他性的種種假定,以及那些放逐給社會科學的諸種真正的社會問題。這三種自我批評的聲音或可以解釋為什麼博物館成了迷人的研究對象。雖然自我批評在某些人看來是瓦解性的,但是博物館所要求的卻是一種整合性。它需要跨學科的分析;它將美學爭論提到了議事日程上;同時,它在本質上是一個社會性結構。博物館看起來成了當代人文研究的合宜對象。”
正如譯者丁寧先生在“譯後記”當中所指出的,當前博物館當中的專業人員、教育以及理論工作者們都應當更多地關注和深入研究藝術博物館的問題。而于這種迫切需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與博物館問題相關的論述,尤其是催人深思的理論探索,無論是在中國或者西方國家,畢竟太少了。所以,《對博物館的質疑》帶給國內讀者的無疑是一股清新之風,我們閱讀卡裏爾的論著,並未感受到那股對時下流行的、作為熱點的“新博物館學”的趨合時尚的浮躁之風,而是針對一個個諸如巴恩斯基金會、加德納博物館、歐內斯特蓋蒂博物館的形成與其內在展品的佈局關係的探討,還有對藝術博物館未來的探索等等,都可見出卡裏爾的深厚的理論素養與敏銳的洞察力和冷靜的頭腦。當然,對於卡裏爾的這本著作的批評也會隨之而來,例如安德魯麥克萊倫指責卡裏爾不加入任何陣營——博物館的熱情擁護者以及反對者之間。當然卡裏爾在書中為自己做了辯護。譯者同樣在《後記》當中自謙地認為,自己只是在與著者一起的旅途當中探討過此書的寫作構想。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譯者可能是向國人介紹此書的不二人選,因為早在此書出版之前,大衛·卡裏爾的另外一部重要的著作《藝術史寫作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次印刷)就是由丁寧先生的介紹而被譯為中文的。並且譯者本人長期以來對藝術博物館及藝術展覽、文化遺産歸屬及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探討投入了不少的精力與關注度,並有《圖像繽紛——視覺藝術的文化維度》這本個人自選集出版。所以他們之間在學術上的往來頗有伯牙子期之風,願我們看到更多的介紹藝術博物館的經典之作進入我們的視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