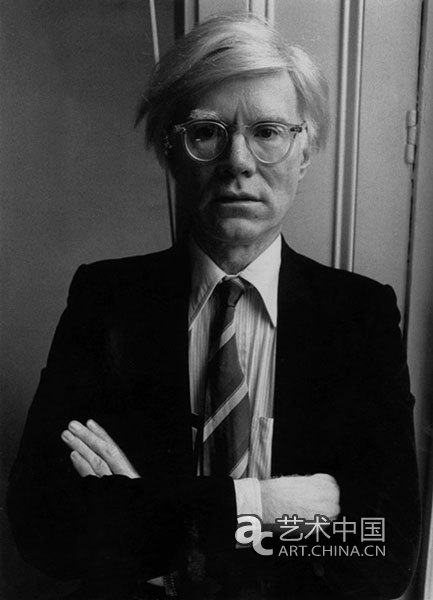
“我無法告訴你什麼是波普藝術:它只是把外面的拿來放在裏面,或者把裏面的拿來放在外面,將平常的事物帶到家裏。波普藝術是給每一個人的,我不認為藝術是給少數人的,我認為應該要給美國民眾,反正美國人通常也接受藝術。”這段刊載于1966年11月《另一個東村》雜誌的安迪語錄不啻是對波普藝術的最好注解:波普藝術從來不像藝評人企圖挖掘的那樣深奧莫測,它只是通過將日常事物或者人們習以為常的大眾圖像引入藝術,重新定義了藝術的疆界。 1928年8月6日,安迪-沃霍爾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工業中心匹茲堡。其父母是來自前奧匈帝國的工人階級移民。三年級時,他得了聖-維特舞蹈症,一種會導致無意識動作的神經系統疾病,時常住院的童年經歷引發了安迪對醫生和醫院的恐懼。
早在卡內基工學院學習商業藝術的時候,安迪便初顯藝術才華。1949年,他移居紐約,開始為雜誌和廣告繪製插畫。他隨意而鬆散的、以水墨繪製的鞋的插畫在業內廣受好評。1954年,他自費出版了一本名為《二十五隻貓名叫山姆和一隻藍色小貓》的書,限量印刷了190冊編號本。當時安迪大概不會想到:這本早年私印的遊戲之作在2006年竟然賣出了三萬五千美金的高價。一切是從康寶濃湯開始的。1962年11月,紐約斯泰博畫廊為安迪-沃霍爾舉行了一次個展,展品包括用絲網印製的康寶濃湯罐頭、瑪麗蓮-夢露肖像、美金紙鈔和可口可樂瓶。幾星期後,在紐約現代藝術館的一個座談會上,藝評人首次提出了“波普藝術”(Pop Art)之名,波普的季節由此開始。
把超市裏司空見慣的日常物件原原本本地畫出來,令一些藝評家質疑“你怎麼能説這是藝術?”而另一些則認為安迪追求的是商業繪畫中的表現性,在嘲諷商業藝術的同時嘲諷了美國的現狀。但在1962年與藝評家戴維-鮑登的訪談中,安迪這樣説:“我只是剛好喜歡平凡的事物,當我畫它們的時候,我沒有想把它們變得不平凡。”但無論如何,一個看過康寶濃湯展覽的人,再走進超市看見康寶濃湯的時候,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吧?安迪-沃霍爾的波普藝術,“將我們看身邊事物的眼光獨立了出來”,令人們“可以看見一般東西裏的價值”。另一方面,絲網印刷的方式令藝術家在藝術産生過程中的參與程度降低了,這與安迪“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一部機器”的觀點不謀而合。在1963年《藝術新聞》的關於“什麼是波普藝術”的問答中,安迪進一步解釋為何喜歡事物就是喜歡做機器:“因為你每次都做一樣的事情,你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樣的事情。” 1964年,在上東區的一家畫廊舉行的“美國超市”展上,一切都裝飾成超市的樣子,只是沒有貨架上的超市物品,只有懸挂在墻上的畫作。安迪的一幅康寶濃湯賣1500美元,而由他簽名的濃湯罐頭賣6美元。波普藝術首次廣泛面向大眾,也向更多的人群提出了“什麼是藝術”這個終極問題。
成名後的安迪並未停步。一方面,他繼續自己獨特的絲網印刷及繪畫,題材逐漸超越了濃湯和名人。他利用報紙新聞剪貼,開始涉足“死亡和災難”等一系列較嚴肅的主題。在工作室進行的“小便繪畫”同樣引人注目,安迪曾打趣説,尿液裏維他命B越多,畫布的顏色就越好看。安迪後來出版的日記顯示:在1977年12月該系列開始製作時,安迪曾使用過自己的小便。評論家一般認為:安迪的“小便繪畫”是對抽象表現主義和傑克遜-波洛克的戲倣。另一方面,安迪的實驗開始涉足更多的藝術種類:他參加行為藝術表演,為地下絲絨樂隊設計唱片封套,拍攝各類照片,但其最主要的實驗方式還是電影——或者更準確的説,實驗電影。他的第一部電影《睡覺》長達八小時,但八小時全是詩人約翰-焦爾諾在睡覺。安迪這樣描述:“就是約翰睡覺睡了八個小時。他的鼻子和他的嘴巴。他的胸在呼吸。偶爾,他會動一下。他的臉。哦,實在太美了。”在安迪最著名的訪談“我的真實故事”裏,他説:“看我電影的時候你可以做比看其他電影更多的事,你可以吃、喝、抽煙、咳嗽,或看看別的地方再回來看,電影還是在那裏,它不是典型的電影,只是我的電影。” 其實安迪的“非典型電影”和他崇尚表面和真實的哲學一脈相承。在1965年《電影文化》雜誌的採訪中安迪被問及是否想與當時的女明星卡羅爾-貝克合作,安迪説不想,因為“對我而言……她太有演技了。我要真實的人。安迪的早期實驗電影無一例外地追求這哪怕令人覺得無聊的真實:《帝國》是長達8小時的關於帝國大廈的真實影像,《口交》是連續35分鐘拍攝一名男演員接受口交時的面部表情,《吃》是一個男人花45分鐘吃掉一個蘑菇……安迪把這些電影稱為“直率的電影”。而他最著名亦最成功的電影當屬1966年的《雀西女郎》。他在電影裏同時使用兩個16毫米鏡頭講述不同的故事。其多重敘事的手法至今仍被廣泛應用。
在1967年接受《藝術》雜誌採訪時,安迪這樣評論道:“這是一個關於人類情感和人們生活的實驗電影,所有和人性相關的,我覺得都不錯。”至於用雙銀幕,安迪認為這“可以讓觀眾緊張並且困惑,有很多事在發生——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1968年6月3日,瓦萊裏-索拉納在安迪的工作室“工廠”企圖槍殺安迪,安迪的胸部嚴重受傷,在醫生進行人工按摩後才幸運地脫離危險。在此之前,瓦萊裏-索拉納是工廠的邊緣人物,她成立了一個名叫S.C.U.M.的分離派女性主義組織,並參演了安迪1968年的電影《我,一個人》。在襲擊發生之前,索拉納曾到工廠欲向安迪討回她的劇本但遭拒,原因很明顯:安迪已不知將它放在何處了。教人不寒而慄的是,安迪曾在兩年前的一篇訪談中談及這個劇本:“一個女孩打電話來要給我一個電影劇本,叫做《抬起你的屁股》,我認為這個名字很好。”
槍擊事件發生後,工廠加強了保安措施,但槍擊事件對安迪的影響——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依然顯而易見。安迪此後將他的電影事業交給了保羅-莫裏森打理,雖然依然打著沃霍爾品牌,但電影逐漸趨向敘事主導的主流B級電影。槍擊事件直到如今還激發著電影人的靈感。1996年,導演Mary Harron決定將此事件搬上大銀幕。他最初的想法是拍一部紀錄片,但他發現根本沒有索拉納的影像資料,也沒有什麼當事人可以談論她。於是他只好自編劇本,將之拍成了劇情片《我槍擊了安迪-沃霍爾》(I shot Andy Warhol)。Harron獲准複製安迪的部分繪畫和絲網印刷品用於電影拍攝,條件是電影拍攝結束後必須銷毀。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在西雅圖和斯德哥爾摩電影節上獲得4項大獎。
與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相比,安迪在七八十年代要安靜得多。除了在1973年製作了著名的***肖像外,他在這一時期更多顯示了他的企業家才能,他出版了《安迪-沃霍爾日記》、《安迪-沃霍爾的哲學》、《波普主義》等多本著作,創辦了時尚雜誌《訪談》(Interview),並提攜了包括Jean-Michel Basquiat在內的年輕藝術家。 他在大量訪談中名言迭出,仿佛一個品牌經理維護著他特有沃霍爾標簽。他糾正了自己六十年代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他説對那句子他已經厭倦了,他把它改成了:“在15分鐘之後,每個人都會出名。”在接受《芝加哥太陽報》採訪時,他又説:“我只是覺得人們應該在同一時間做兩件事情。”他的名言總是那麼直接而表面——“我從來沒有不在狀態,因為我從來沒有狀態”。“你仔細想想看,百貨商店就是一個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