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現場
2012年10月20日下午,題為《自戀》的藝術家群展在798藝術區的星空間開幕。
本次展覽由煙囪策展,展出了包括:陳天灼、大瓜、金寧寧、宋琨、溫淩、烏青、謝其、煙囪、張雯在內的藝術家數十件作品。展覽將展至11月20日。
關於自戀
因為星空間10月有個空檔期,我想空著也是空著,不如我找朋友們一起做個展覽吧,但不確定做什麼題目。到了晚上我突然想到了一個四格漫畫故事,大概內容是這樣:我經常在網上看到比我畫的好的人,我的想法是“操”;當我發現他們年紀比我小的時候,我的想法是“還是90後,讓不讓人活了”;我開始自暴自棄,“我老了,不行了”;但最後我又回到書桌前畫畫,終於畫出一張好作品,我覺得自己太牛了,“我簡直是世界之王 ”。我發現這就是自戀的破滅與建立,我一直在這樣的過程中慢慢成長。
我想起看過一部關於Robert Crumb的紀錄片,裏面有幾個片段我印象很深刻。通過這部影片,我還總結出了自戀的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天才,但是飽受社會淩辱,不被社會承認,最後索性脫離社會,我行我素,這是一種天生的自戀 。
第二類,同樣飽受社會淩辱,但是堅持自我終被社會承認,但是在被承認後因為壓抑太久,只會索取,不會給予。是一種自我認知,保護性的自戀 。
第三類,靠自覺不自覺的自我欺騙式樣的自戀活著,一種被強迫的自戀 。
我發現我不是第一類,而是二、三兼有的類型,我很高興,甚至發現第三類人裏的有一些是我特別羨慕和崇拜的。自戀這個帶有療傷,催眠,致幻的東西幫我度過了很多艱難的時光,甚至幫我變的強大。我大學時代第一次給我的偶像Anke Feuchtenberger寫信,她回信稱讚我畫得很優秀,於是我就真的自大到感覺自己和偶像已經在同一起跑線了。她對我的肯定説明我離她不是很遠,我有追趕和超越她的可能性。抑或是在創作中,我感覺畫得不錯就馬上發給別人看,如果他/她稱讚,我就堅定了自己的信心;但是畫得不好,我也會發給別人,對方如果對我批評得不得要領,我則在心裏罵他/她,從而獲取優越感,然後再去仔細地審視自己的作品,得出一個合理的判斷。總之,我很自大,但一方面也在吸收和消化,不至於被擊潰。
這次展覽我邀請了一些我覺得符合這些條件,同時作品有明顯的“自戀”傾向的藝術家,與我一同參展。向你介紹他們:anusman、陳天灼、大瓜、金寧寧、宋琨、溫淩、烏青、謝其和張雯。
溫淩,我覺得他是第一類,他是天才畫家,但是往往被認為是低技術,太簡單,但是沒人知道他對自己的作品有多苛刻,不過他已不在乎那些膚淺的評論了。 我的好朋友金寧寧和張雯,她們是第一、第二類兼有的,一方面迫切希望得到讚揚,一方面卻對他人的評論滿不在乎。 anusman,我常常在他的作品裏看他的孤獨表演,一個人飾演各種不同角色,自説自話。宋琨,我覺得她幾乎完全等同於“自戀”,她一直在持續地觀察自己,紀錄自己覺得應該被銘記的瞬間,她創作的裝置作品極具私人收集品的氣息,而且一直不受任何外界干擾。謝其之前畫的樊其輝讓我感動,這次她的4張畫都是和性器官觸感的經驗有關。我最喜歡《No.1》,乳頭、陰莖,和不知道是腳後跟還是肘關節之間的澀澀碰觸,懸在半空中半張的濕潤嘴唇,它們加一起延伸出來的那種觸感體驗,讓我直起雞皮疙瘩。陳天灼的“刺身”計劃——在微網志上向自願者免費提供自己設計的紋身圖樣,並回收紋身完成的圖片證據——我尚不知道目前有多少人自願參與了,不過這個在別人的身體上紋刺自己作品的做法已經相當“自戀”了。大瓜,我記得她大學時代的攝影都是在拍同學跳舞,或是惡作劇式的從樓頂俯拍假裝跳樓摔死在草地上的人。但是她工作後做的攝影集冊裏,那些快樂的情感都沒了,拍了很多年輕學生——她對學生時代活力的懷戀,羨慕;還拍了好多麻木,不知所謂的成人——對成人機械茫然生活的觀察,似乎帶有批判他們的意味;另外有好些自己茫然狀態下的自拍——紀錄自己成長的變化,這點比溫淩更為勇敢。不知道這算不算自我保護性的“自戀”,但我覺得這是一種無法找尋歸屬的恐懼和孤獨。另外,還有詩人烏青,我聽過一些關於他的事跡。他的詩歌我看得不多,但有兩篇小説,我特喜歡:
《向你介紹一部錄影短片》
有一段時期我非常喜歡《大白鼠》,常常在半夜一個人坐在家裏觀看這部錄影短片,而且一看就是五六遍。我總是關了燈靠在我的破沙發上,一邊抽煙,一邊喝水,一邊看,如果餓了就會泡一包康師傅速食麵。這時候四週特別靜,而且還有點冷。我往往每看一遍就上一次廁所,有時候小便有時候大便。這幾乎成了一個習慣,我蹲在廁所裏抽著煙,拉了一點點屎,我越想越激動,終於鼓起勇氣,洗了手,給多紫打電話。她一接電話我就説,對不起吵醒你了,我是烏青啊,我要向你介紹一部錄影短片《大白鼠》,拍得太好了,太舒服了,簡直舒服死了。多紫説,哦,你昨天打電話來説過了。我説,真的,真的很棒,你看過嗎?多紫説,我沒看過——你還有別的事嗎?我説沒有了。我又説,你一定要看一看啊。
《我女朋友的男朋友》
有一天半夜,我給我的女朋友打電話。我説,吵醒你了吧,我是烏青啊,我要向你介紹一部錄影短片《大白鼠》,拍得太好了,太舒服了,簡直舒服死了。多紫説,哦,你昨天打電話來説過了。我説,真的,真的很棒,你看過嗎?多紫説,我沒看過——你還有別的事嗎?我説沒有裏了。我又説,你一定要看一看啊。這時候我聽到她旁邊有個男人的聲音問誰啊?我問多紫,你旁邊的男人是誰?多紫沒有説話。
電話裏突然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喂,你是誰啊?我説你是誰?對方説,我是多紫的男朋友。過了一會兒。我説,你好,你看過錄影短片《大白鼠》嗎?對方説,《大白鼠》,看過看過,拍得太好了。
我開始覺得小説裏的“我”是我最欣賞的第三類人。但今天我又想了想,他應該是第一或者第二類:一個迫切需要別人認同的“自戀”者。真是太可憐了。
——策展人,煙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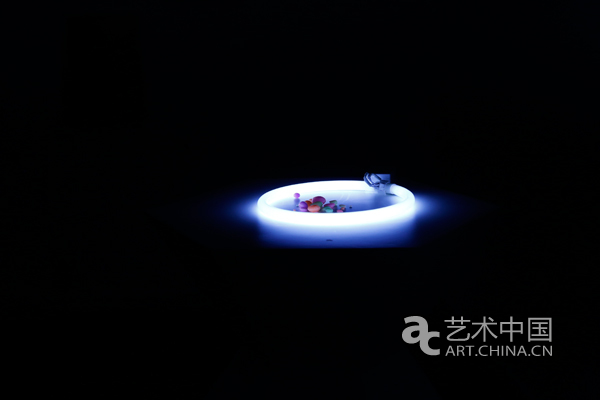
展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