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個移民社會,人民是從世界各地、各國來的,他們移民到美國都是因為不同意或放棄原有社會的某種生活習慣、方式或理念,個人目的就是想為自己或下一代的未來開創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裏,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自我實現生命的意義,我們都稱之為“美國夢”。
每個到這裡的個體都明白,要在共同維持法律的平等原則之下,社會公平的良性競爭才有機會實踐個人的美國夢,因為這裡沒有世襲的貴族、沒有傳統宗教掌握信仰的教會、也沒有皇家貴族的特權,只有當自由有紀律的競爭、事業有理性的公平、能力有改善的功能,個人的努力才有機會説他對美國有所貢獻。
所以在美國,雖然她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要比對國家的貢獻來得重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社會事業,或者説,非營利組織的事業。
美國博物館所面臨的革命性變革
20世紀以來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國的博物館仍主要強調其內向性的典藏保存功能。有一幢建築物、有收藏、有館員照顧收藏、有足夠的財力支援,美國的博物館主要的表現是針對其原歐洲移民所做的收藏,或者美洲自然與人文的特點收藏,一開始就是以到美國移民如何了解這個“新世界”為目的,建立他們到美國的共識,這個“教育新移民了解美國社會”的意義是美國自從有博物館成立以來的共同目標。
例如大都會博物館,當初向紐約州政府要求蓋一個建築,專為存放與展覽從歐洲各得的大師級作品時,就誇口,這個博物館是要紐約市民不離開紐約就可以看到人類自有藝術以來的作品,從1870年代開始就創下這種公私合營的博物館社會事業的模式。一直到1990年代洛杉磯成立的日裔美國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American),館內主要的常設展就命名為“共同的起點——社區的心臟”(Common Ground – Heart of the Community),它讓我們了解到美國的博物館服務的對象就是社區,在這種社會發展的新趨勢下,美國的博物館面臨著兩項革命性變革。
目前,“外向性”已經成為博物館的主要導向,公共服務成為美國所有博物館最重要的定義。博物館要為它所在的社會提供教育與社會服務。而曾是博物館“存在原因”的收藏,現在僅僅是用來完成公眾服務的多數資源之一。
第二項改變是仍在進行中的變革,其範疇卻並不僅限于博物館,而是整個在美國所謂的非營利組織,或説政府管理部門、營利工商業部門之外的所有第三部門範圍內的變革——這些機構包括了超過一百萬個與私人非營利組織有關的文化、教育、健康與社會服務的組織,目前美國35000家博物館的65%都屬於這種社會事業。
美國“非營利性“組織的變革
“非營利性”組織變革的核心是期待這些非營利機構能執行公眾服務義務的成長。每個非營利機構不但要整合,而且要利用他高層次的能力來實踐一項具體性的成果。在“非營利性”變革的壓力之下,美國曾出現過“義工領航”與慈善性基金管理的組織,如今已轉型而成為有動力的社會事業,而每個社會事業團體最後無論是成功或是失敗,都是以這個機構它對特殊結果的運作能力來判斷,要尋求這項特殊結果是以他日常運作的能力來累積完成社會效益。也就是説,美國博物館是以實踐為結果導向來運作的,也就是説它所服務的社會是否可以累積這份結果而強化社會的軟實力,這是美國社會非營利組織傳承的意義。

博物館“非營利性”變革是一種新的組織概念,這種社會事業的新概念最有力的提倡者是迪斯〈J.Gregory Dees〉教授,他曾在哈佛商學院與斯坦福商學院任教。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組織可分為:非營利組織(他稱為社會事業)與營利事業(他稱為商業事業),基本上我們可以認為兩者是相似的組織,但是他們之間最主要的不同則在於:
1.追求目標的性質:工商業事業經營運作的具體目標是經濟成效或利益,而社會事業經營運作的具體目標是社會效益;
2.産品與服務的價格:工商業事業的産品或服務是市場取向的,而社會事業通常提供免費或低於其成本的産品或服務,這種服務是以改善社會為取向的;
3.資源補充方式:工商業事業除了維持員工就業機會之外,所獲取的利益可以用來擴充事業範圍,繼續獲取更多的利益;而社會事業不像商業事業有力量去買他為生産而應有的需求;社會事業可能要全部或部分依賴捐獻的財力、物力和服務,因為他的産品已經對服務對象産生社會效益而消耗殆盡,必須依賴社會資源的補充。
美國聯合陣線(the United Way,以下簡稱“聯合陣線”)是美國最大而且最具影響力的非營利責任單位,其成員有1,400個以社群為基礎募款的組織,它每年收入的錢有70%是直接由其成員的薪資支付的一個聯邦性組織,1996的年度報告它得到的捐款是35億美元,這筆捐款分配到一萬個地方性的組織。過去聯合陣線捐款分配的決定是基於申請項目的評量,也就是説一項補助是否通過,取決於申請補助案件的節目課程是否合於參與者的需要。但是到了1995年,聯合陣線不再採用這一套方法,而是將關注焦點對準成效(outcome)、結果(results)與節目的執行(program performance)的過程。

總之,評量標準不再是服務提供者要服務什麼,而是接受者是否需要這項服務;不再是節目的受歡迎程度,而是它是否真的有用。聯合陣線的捐助要指導社會服務單位以成效為基礎來評量,要節目與活動産生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力,而且期待透過全美國捐款的社群來實踐這項社會效益的評量。這些捐款的社群包括基金會、公司捐贈人、政府機構。
此後,捐贈者對於多種申請者都要更深入的要求,不論是文化組織、社會服務單位或健康服務單位,要回答有關他們希望做出成效的細節問題,或確定要求他們透過建議中的節目所要達成的期望,用這些來決定這些特殊成效事實上有沒有成功。
美國1993年頒布的《政府績效與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以下簡稱“績傚法案”),是各國政府績效改革浪潮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代表性立法。績傚法案全面規定了實施政府績效管理的目的、內容及其實施進程,並著重鼓勵行政管理中的放權與減少程式控制。
當2000年開始執行時,其影響力大為擴張。美國聯邦政府每個單位要建立每個計劃特定的執行目標,並且有具體目標、可能合格的、與可測量的條件下,他們要做的每一個節目的評量,而且還要每年向國會報告是否完成或未達成該目標之處。美國政府單位在早期立法中已負有控制詐欺及濫用的責任,而在此績傚法案之下,政府採用可以構成高一等的整套機制,使政府的推動真正有助於完成他們企圖達成的成效,使聯邦政府的錢誠實的而且有效的花用。我們可以看成:美國政府自認是一個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性”變革下的美國博物館
在這項“非營利性”變革與其他力量的驅使之下改變著美國的非營利組織,也包括了博物館的運作。這種新氣像是很現實的而且減弱了傳統的信託與溫和性慈善,過去的公眾仍把博物館視為是慷慨的慈善機構,現在卻必須把握這種對公眾福物的堅持,才能當作博物館運作獲得更高信度的評量指標。
在早期,博物館的存活在於某種“善”的信念上:相信博物館的存在本質是一個機構重要的因素,相信這個善的本質只要存在就會增加這個社群的福利。可是這次的“非營利性”變革卻提出有關博物館能力與目標是否有意於民眾的問題,不是僅有那項慈善性的傳統信念就能完成社會效益軟實力的累積。
如果美國的博物館不能以改變人們生活的品質為其最終目標的話,它還能以什麼來要求公眾的支援呢?當美國博物館要應付“非營利性”變革尋求辦法之際,效益(efficiency)與效率(effectiveness)之間的區別就非常重要。要有效率是成本(cost)的計算,而效益則是運作績效(performance)的計算。效益是要説明一項計劃的節目與花在達成這項運作績效的資源之間的關係。
雖然在工商業營利事業中,效率與效益之間有很多實質的重疊之處,而社會事業就不一樣,儘管它在效率與效益上仍是有區別的,這種概念是:博物館可能在産生社會效益之後才能去計算是否有效率,所以博物館不是消化了預算就解決社會效益産生的問題,預算執行完了沒有社會效益就是博物館浪費資源,完全沒有效率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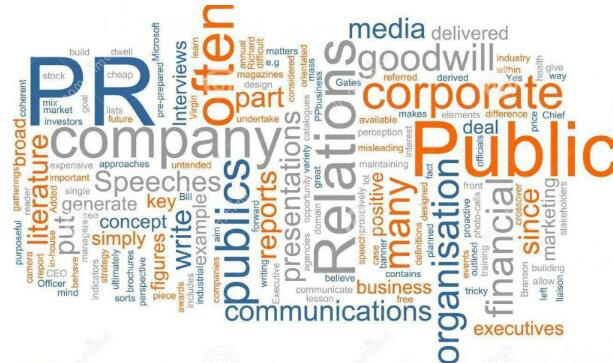
所謂效益就是博物館的意圖與因自己本身條件而採用可以被公眾接受的運作産品。例如,在博物館有些特定的手續、規定有期限付薪的售貨員、在博物館裏做對話性的考察、對外進行貸款等類似營利的活動——當然,博物館可以有這種取向的運作,但這些活動絕不會成為博物館本身的基礎收入。
博物館在他們的起源、原則、規模、主管機構、募款來源、成就、招募從業人員、設施和社區環境等方面都非常的多樣化,而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按一個模式運作,甚至不能和其他博物館的基礎收入做有意義的比較,特別是在效益方面。一個博物館的效益只能以有關於它想要完成的工作是否符合它要服務的對象之需求來做決定。
波士頓的美術館和紐約大都會的博物館都是在1870年成立的,都以英國的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的博物館的模式為範本,他們最開始時就意指著其性質要以教育歐洲移民為主。至1905到1910年他們又重新把他們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收集原始的、經常是唯一的美術作品。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博物館界不屈不饒的爭論著對外取向與公眾信度的博物館,例如史密森機構早期的副秘書長古德(George Brown Goode),1889年在布魯克林研究院(Brooklyn Institute)演講時説:
過去的博物館必須置之一旁,重新解構,從小古董的墳場轉型為活躍思想的看護所。博物館的未來必須與圖書館與實驗室并肩而行,成為大學與學院教學設備的一部份。在一個大都市裏,他應與公立圖書館合作,成為人民啟蒙教育的主要代理機構之一。
George Brown Goode
到20世紀初年的代表人物就是達納(JohnCotton Dana)。這是一位社區性紐瓦克博物館(Newark Museum)最早的倡導者與創立者。達納在1917年的文章中描述,美國大部分的博物館與其他東岸的博物館,都在為歐洲所流失出來有關過去不可得的美術作品加速的收藏,他們這種“大理石建築中填滿了所謂的文化象徵、稀有而且昂貴又奇巧的物件”,他認為那:“是國王、王子、及其他有錢有權的人所建構出來的。”不會帶給常民快樂或利益,也不可能完成達納認為每個博物館最首要、最明確的工作,那是:“為社區的成員增加快樂、智慧、與舒適。”

紐瓦克博物館
最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達納就了解到,公眾支援的博物館基礎面是一個交易行為。也就是説,公眾要對博物館的運作與功能做一種價值評估的回報。他更具前瞻性的預見到為了確保公眾的利益,博物館必須為提供這些價值來贏得公眾的可信度,它必須是肯定的、可信的公共服務機構,事實上這種概念已經深植于現在美國博物館傳統之中。
面對變革,美國博物館的挑戰與機遇
以下我們針對“外向性”和“非營利性”的變革對美國博物館界所産生可能後果,其中有五點值得我們注意的:
1.學科性(disciplinarity)
考察發現,只有15%的博物館真的是跨領域的,其他85%都僅僅與一種特殊學術學科有關。所以當博物館的焦點轉移到公眾服務時,博物館這種僅具有特殊學科的收藏在社區需求的運作導向上所具有的意義就不大了。在這種新環境趨勢之下,博物館必須從這些有關學科性的限制下解放出來,擴充他們項目的範圍。達納認為,形塑博物館節目最適合的方法是博物館透過與社區進行對話,“博物館要學習用什麼服務去幫助社區的需要。”
2.博物館界本身模糊的界線
當博物館主要的項目都集中于有關於其特殊搜藏、保存與陳列收藏品,博物館就傾向於孤立與孤單。如今,博物館重新定義的主要目標,從收集一項藏品走向提供公眾服務,它的存在是要與更廣大範圍的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眾服務團體合作,或常常要交換功能。從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組織的角度來看,博物館這種潛在的新關係,或者説它這種新的、非傳統的設定角色,與它曾經有過的、清楚的“善”的身份有了區別。
3.博物館的內部組成
博物館的內部組成:例如博物館如何招募館員與如何分配預算。當藏品做為博物館的核心問題時,負責博物館收藏的那些人就是主控者;而演進到以外向為焦點時,典藏人員被迫要把他們的主控權分給其他專業人員:教育人員、展覽策辦人、公共節目策劃人,甚至負責行銷與媒體的專業人員,不論是他們的主控權還是預算權都一樣。因為博物館的焦點以外向為主導,其運作成本的分配增高,特別是薪資,必須按照可獲得的資源來分配,從藏品的研究與保存的費用而轉向其他服務功能的使用。
4.預算方面的後果
博物館急需利用新的評估技術,來評量節目在對個人與社區所産生的影響。以運作績效為基礎的評量是源於社會事業的領域,這種評量可以呈現的不但可以用於博物館,其他有關公眾組織的特殊問題,例如宗教團體、人文藝術學院、保育立法團體等也可以採用。然而博物館的影響比較含蓄,不直接並且經常需要時間的累積,而且與其他正式、非正式的教育經驗,例如學校、教堂、與其他類似的團體的資源所産生的影響有關連。一座博物館的價值可以增加社區的福利,卻不一定可以自我證實,至少不能像戒毒或是生育計劃一樣,可以立即的發展出一項有信度的方法來報告這份工作的價值。就像我們説,展覽評量(exhibition evaluation)不一定會産生最好的展覽,可是一定可以改善展覽。
5.博物館要有更明確的定義
博物館實踐的每一種活動都必須以此目標作為持續而且經常性的背景説明。在這兩項變革的影響之下,博物館的運作績效將是繼續得到公眾支援的關鍵。1895年史密森的古德在對英國的博物館協會提出的一篇文章中就説明瞭這一點:“博物館工作如果沒有目標,就會導致以共犯的方式而浪費力量,致使部分或是全部的工作失敗。”
結語
1978年美國博物館協會選史達爾博士(Dr.D. Kenneth Starr)為主席,後來他當米瓦奇公眾博物館(MilwaukeePublic Museum)的館長。在他早期是中國藝術史家,經常應公眾需要開課,他常提醒聽眾一句中文,“危機就是危險與機會的集合體”。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的變革:從內向的博物館走到外向,從被接受為信仰的博物館走到必須呈現它的能力來達成肯定的成就,那麼我們對每項變革要用兩個問題來做結論:危險在何處?機會在何處?
我想美國博物館的危險就是倒滑回以收藏為核心的方式,使它本身運作與社會不相關。而博物館的機會是抓住現在,首先要厘清目標,從此目標繼續發展,以可以呈現與持續的方式,用堅固的管理技術與策略,來確保完成這些目標的能力。博物館“外向性”和“非營利性”變革,使博物館工作人員的職責發生變化,那將是更高層次的社會秩序。這種博物館必須要具有專業能力,這種事業可以用很多出色的方式來豐富我們社區的共同福利。
這些都是美國社會事業這兩項變革釋放給美國博物館界的方法,所以現在的美國博物館界都利用“展覽評量”、“博物館認定程式”(Museum Accreditation Process),來證明博物館專業人員對社區、社會效益所運作出來的績效。
注:徐純,社團法人台灣博物館專業協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