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imiliano Gioni,這位去年十月在新美術館上任總策展人的人,並非把全部關注的重心放在那些時髦的玩意兒上。他既不是被釘在某個“ism”理論釘板上的老古板,也無心和詹姆士·弗蘭科或者拉瑞·高古軒等人稱兄道弟。事實上,他自己表示,想要挖掘在切爾西或布魯克林之外的藝術:“我最早來到紐約的時候,對於所感受的東西都非常有興趣,盡可能地多學多看。如今我倒是很想知道紐約有什麼沒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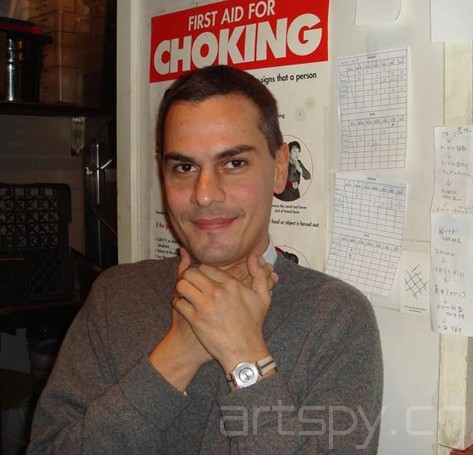
Massimiliano Gioni
這聽上去就像美術館的長期信條(比如“新藝術,新想法”)。如果説他真的能把活力帶到那些畫廊中去,Gioni將是新美術館急切需要的那個人。自從新美術館2007年在Bowery重建,這座34歲的建築總是令人心裏沒底兒似的。又冷又小的展廳對比建築外觀的閃亮,成為眾人詬病的重點。很明顯,藝術內部人士的金錢政策依然起效:一個專門為希臘億萬富翁Dakis Joannou所做的展覽惡評如潮,但是畫廊還是得靠著這些人,比如Gavin Brown。Gioni的觀點得到了許多人的肯定,就像呼吸了一口正直的新鮮空氣一樣,被認為能夠拯救這所生病了的機構。“如果他做不了,那麼在現階段就沒人能做了。”一位主策展人這樣説。
新美術館,這所沒有一個常設展的機構,幾乎是站在了流行藝術與藝術世界的孤島中間(從一定程度上説,比起美術館,它更像一個體積很大的畫廊)。Gioni努力把他的身份從一些東西中抽離出來:“有許多與我的構想相符的東西,也有必須去對抗的。”他做的兩個展覽,一是對住在倫敦的觀念藝術家Gustav Metzger的致敬。這位藝術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被人們所熟知,成就即是造就了藝術,並逐漸摧毀了它。另外一個是對於泰國導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致敬,他的電影夢幻並帶有冥想的意味,並非適合所有人。
“他的角色很重要,”獨立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説。他也是在2003年提議讓Gioni組織威尼斯雙年展小館的倡議者:“一定程度上説,美國藝術有它目光短淺的一方面。Gioni正在與它的封閉性作鬥爭。”這麼説的還有Gioni的好友和合作者、藝術家Maurizio Cattelan:“他十分想讓藝術館成為更好的地方,能展示更多不被立即理解的、未知的東西,並與那些已知的形成平衡。他知道紐約缺什麼,以及新美術館少了些什麼。”
這可能是因為,Gioni並非生來就在藝術行業。他出生在米蘭郊外附近的一個小城,打個比喻,就像是紐瓦克市(美國新澤西州港市)。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組過一個受到Sonic Youth影響的樂隊,並出售自己做的藝術T恤。“那兒有很多迷人的怪人,人們都接受他們。”Gioni這樣形容他的少年時代。在西20號大街,他和幾個朋友鼓搗了一個畫廊名叫Wrong Gallery。剛開始的時候,它很簡陋,只有上著鎖的大玻璃櫥窗。“沒有要賣的,”Gioni説。他和他的夥伴能免費租用那個空間,條件是他們要展出這塊地主人妻子的油畫作品。
他們在裏面開展的項目既有失體統又趣味橫生。從聲音裝置到光線作品,還有房頂上寫著“我們關門了”的貼紙,逐漸,這個小空間得到的關注越來越大,甚至那些策展人也開始有興趣。2006年他們參加了柏林雙年展,以及後來在南韓光州的一個雙年展。The Wrong Gallery本身甚至被搬進了泰特美術館呆了幾年,自從它被從切爾西驅逐出去之後(它在2008年關的門)。
儘管Gioni是圈內人關注的熱點,他自己還是有點兒孤獨。他讀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書,比如《戰爭與和平》,還有一些納博科夫。“我認為把錢花在書上,與花在機票上同等重要。我很討厭人們認為策展人就是個全世界範圍的觀光者。儘管這是你需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當然更包括學識以及研究工作。”他把那些能夠飛來飛去的機會視為自己能看到更多古怪、被忽略的,以及暫時掩埋在地下的新藝術。
Gioni的下一個展覽依然走的是上兩回的路數,但是可能更寬闊一點。他説他想這個展覽的事兒已經很久了。展覽名為“Ostalgia”(編者注:直譯為“骨痛”,但可能是從“鄉愁”nostolgia這個詞來的一個文字遊戲),即將於7月14日開幕,將展出許多不為人知的歐洲藝術家的作品,主題是關於前蘇維埃聯盟。“最近,我對於那些被遺忘的東西很感興趣,”Gioni説,“它們並不令人感到愉悅。在紐約,潛意識裏,有種‘需要取悅什麼’的趨勢存在在這兒——太多了。我不想弄一些能讓人們説出‘嘿夥計,一塊兒來!’這樣話的東西。在當今世界最終想要玩兒得徹底或激進,要麼令人無聊,要麼就得嘗些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