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壁劇社正在進行表演訓練

新工人藝術團在藝術節上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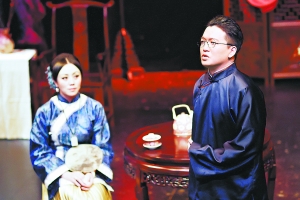
衚同實踐劇社《浮生》劇照

明皓劇社《我們結婚吧》劇照
不久前,北京人藝實驗劇場,一群“圈外人”演出的話劇《滷煮》在觀眾依依不捨的目光中落下帷幕;大屯的一個居民樓裏,由家政女工組成的地丁花劇團正在排練她們自己創作的《勞動者的光榮、尊嚴和夢想》;奧體中心傳奇小劇場,第三職業戲劇聯盟正在演齣戲逍堂的經典作品《有多少愛可以胡來》,只不過海報上多加了三個字“非職版”……
目前,一群非職戲劇人正活躍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臺或排練廳裏,並且日益受到觀眾和專業戲劇工作者的注意。和“圈內人”不同,他們排練時沒有場地,只能四處輾轉;演出時沒有華麗的服裝,只能自己操刀;台下沒有觀眾,只能拉來親戚和朋友;有時甚至連舞臺都沒有,但他們依然享受著戲劇帶來的快樂。他們像是春天裏的野花,雖不精緻美麗,卻依然燦爛綻放,讓人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
現場:“隔壁劇社都是些什麼人啊?”
三里屯街道辦事處藏在幸福二村的深處,週六下午,這裡顯得有些安靜,門口既沒有車,也沒有人。但是推開街道文化活動中心的門,卻有一陣陣開心的笑聲從走廊盡頭的屋子裏傳了出來。這間屋子的面積約有80平方米,裏面坐著二三十個年輕人,他們都是三里屯隔壁劇社的成員。成立於2007年的隔壁劇社,在非職戲劇圈裏頗有名氣,其名字來自著名導演賴聲川的話劇《暗戀桃花源》中的一句臺詞——“隔壁劇社都是些什麼人啊?”
這一天,劇社的成員正在進行表演訓練。訓練的主題很簡單:不許説話、走一段路,然後讓大家猜你想表達的是什麼角色。穿著格子襯衫、戴著眼鏡的阿偉,畏首畏尾地從屋子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看完他的表演,大家紛紛表示沒看明白。阿偉急得趕緊解釋:“我演的是被跟蹤啊!”坐在另一側的“失眠”點評道:“我怎麼看不出你哪點兒值得被跟蹤呢?”一邊説著,他一邊順手抄起手提包,示範被跟蹤時應有的恐懼狀。阿偉邊看邊笑,服氣地點點頭。
“失眠”是隔壁劇社的元老,表演經驗豐富,正在電影學院學習編劇。沒有專業老師指導的時候,他就會親自上陣。“你演撿錢,就要演出撿1塊錢和100塊錢的區別”、“你是演在風景區拍照,怎麼看著那麼痛苦?感覺你家被強拆你拍照留念似的……”他對每個人的點評似乎都很刻薄,卻又一針見血,自然也不會有人急赤白臉地跟他抗議。
在外人眼裏,這群瘋瘋癲癲的年輕人似乎是在玩鬧,可他們自己卻玩得很認真。成員“影弟”總是找不對感覺,還沒想好演什麼就衝上臺去,撓撓腦袋,轉上幾圈,又在大家的噓聲中下場。新人小月是第一次參加劇社活動,但她毫不猶豫地主動舉手要求上臺表演,站在臺上也毫不怯場,當即震翻了大家。在這裡似乎沒有什麼人會扭扭捏捏,每個人都毫不在意地展示著不那麼會演戲的自己,享受著隨性表演的那一刻。
在北京,像隔壁劇社這樣的非職劇社有幾十家之多,在大大小小的劇組活躍著的非職業演員不計其數。隔壁劇社的社長佩佩這樣描述這群人:“年齡最大的50多歲,最小的13歲,二十六七歲的最多,70%以上是北漂,最遠住在六環外。”在工作日,他們是公司白領、律師、醫生、媒體記者,下班之後或是到了週末,他們就搖身一變成為演員。還得套用《暗戀桃花源》裏的臺詞——
問:“隔壁劇社都是些什麼人啊?”
答:“隔壁劇社什麼人都有!”
幕後:“你説我貪慕虛榮嗎?我承認”
晚上7時30分,《滷煮》即將開演。6時45分,在劇中飾演男二號的陳磊才匆匆趕到。他還不是當天最晚趕來的演員——7時整,飾演配角的王博幾乎跟觀眾前後腳進了劇場。像這樣的“遲到”現象,在專業劇組裏完全無法容忍;但在由非職戲劇人出演的話劇中,卻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作為一名資深“票友”,職業身份是國企員工的陳磊經常會在各個劇組趕場。他參加相聲劇《六里莊艷俗生活》演出時,因為單位離劇場太遠,往往要在演出快一半時才能趕到。
陳磊不肯透露自己的工作單位,生怕自己的行為會被同事誤解,甚至背上“不務正業”的壞名聲。可是只要有演出的機會,他向來都會樂此不疲地參與其中。前兩年有一齣描述80後職場生活的話劇《當司馬TA遇見韓寒》,其中有個角色就是以他為原型塑造的。這個角色有句獨白,是像他這樣的非職戲劇人的真實心理寫照:“在我眼裏,真正的價值,是一群素不相識的人,為你的努力鼓掌叫好。你説我是貪慕虛榮嗎?我承認,可是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會真真切切地意識到,原來我的所有付出都不是白費的。”
並不是每個非職戲劇人都有著和陳磊相似的想法。“很多人參加劇社的目的不是為了戲劇,有人是為了解悶兒,有人是為了練習普通話,有人則是希望多接觸一些人,甚至包括找對象。”北極熊劇社負責人吳嵩認為,很多非職戲劇團體在成立之初就不是以戲劇演出為目的,而更像是一種俱樂部。佩佩就把隔壁劇社每週一次的表演訓練形容為“派對”,“我們不是表演培訓班,我們也不負責排練你的劇本。你來玩我們歡迎,你想成名請去別的地方。”
不過,也有些非職戲劇團體正在變得越來越專業。比如石景山區文化館話劇團,不僅有知名演員李丁擔任督導,團長李玉山也曾是山西話劇院的國家一級演員,文化館還派了業務幹部專門管理劇團事務。“有個從內蒙古來的姑娘,本來是幼兒園老師,一心抱著明星夢,辭了工作來北京。沒事時就在劇社訓練,現在已經能夠接到戲了。”李玉山説。
處境:“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當聽到“格致劇社”這個名字時,呂剛的直接反應是愣了一愣,遲疑了一會兒,他才反應過來。格致劇社成立於2009年,是一個由大學生自發組成的團體,呂剛正是這個劇社的發起人。他有些尷尬地表示,劇社的名字雖然還在,但其實有一年沒組織過任何排練和演出,事實上已經處於解散狀態了。
呂剛記得,劇社排練過的最後一部作品,是薩特的作品《骯髒的手》。一千多元的舞美道具費用,都是劇社成員自己從生活費中節省下來的。呂剛原本打算帶著這齣戲參加專門為非職戲劇人成立的非非戲劇節,沒想到並沒有被戲劇節主辦方選中。結果,這個排練了一個多月的戲,甚至連演出的機會都沒有就宣告夭折了。“弟兄們搭上伙食費排練了那麼久的戲,連演都沒演,我作為發起人幾乎沒臉見他們了。”呂剛説。
像格致劇社這樣解散了的非職戲劇團體,並不在少數。每年九十月份,非非戲劇節的主辦方都會向參加過上一年活動的劇社發出征集劇目的電子郵件,但只有一半的郵件能夠得到回復,其他劇社基本上已難覓蹤跡。有人把非職戲劇團體形容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大多數都扛不過一年就無聲無息了。
沒場地、沒資金、沒演出的“三無”困境,是大多數非職戲劇團體所面臨的最大生存威脅。銜蘆劇社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因為沒有資金,這個劇社的排練場地,只能設在北五環外一個菜市場邊上快要拆遷的門面房裏。每個週末,劇社成員都要“千山萬水”地跋涉而來。他們中有人來自南二環,有人來自南三環,在路上就要花費一兩個小時。
曾經在戲劇圈內頗有名氣的北極熊劇社,目前也已經進入“休眠”狀態。以前,這家劇社是靠社長吳嵩自掏腰包來作為資金支撐,但他現在漸漸有些掏不起了:“我已經30歲了,也要娶媳婦、生孩子,家裏人不允許我再把錢都投在這上面。”另一家非職戲劇團體明皓劇社,則是靠收取會費來維持運營。這家劇社的成員大多來自CBD一帶的白領,每人每年繳納的會費為200元。考慮到收入水準的差異問題,這種做法很難在其他劇社中推廣。
思路:“戲劇雖然小眾,也是文化需求”
為了參加今年非非戲劇節,石景山文化館話劇團獲得了5000元前期資金用於排練。儘管錢數不多,但卻足以讓其他非職戲劇團體羨慕不已。事實上,像石景山文化館話劇團和隔壁劇社這樣,能夠依附於基層政府部門,並因此獲得資金和活動場地支援的,在這個群體中屬於鳳毛麟角。而這些劇社的運氣,更多取決於基層文化管理者的態度和認識。
隔壁劇社與三里屯街道的合作純屬偶然。在一次朝陽區舉行的小品比賽頒獎典禮上,佩佩和街道負責人碰巧站在一起,兩人攀談後發現,彼此可以互相幫助。隨後,劇社便入駐三里屯街道,連社名也變成了“三里屯隔壁劇社”。無獨有偶,創立於2008年的衚同實踐社,曾向宣武區文化館申請場地支援,但對方以現有群眾文化團隊太多、無法保證場地為由,婉拒了申請。但是,當他們輾轉找到金融街街道後,卻因為得到對方的賞識,而很快解決了場地問題。
事實上,基層部門並不缺乏文化活動經費。據北京市文化活動中心主任黃海燕介紹,通過文化項目“轉移支付”,2009年開始,全市每個街道每年都可以獲得5萬元到10萬元的經費用於文化活動,每個社區從市裏獲得的文化活動經費就有5000元到10000元。此外,有些城區還會另行撥款予以支援。比如東城區,每年就有200萬元的資金作為專項文化活動的獎勵。
但是,和街道社區遍地開花的舞蹈隊、合唱隊、書畫隊相比,非職戲劇團體要想申請資金和場地,往往更困難。
有群眾文化工作者認為,這可能與目前群眾文化工作的考核標準有直接關係。據了解,在文化部出臺的文化館評級標準中,只考核館舍面積、行政管理、隊伍建設、對外服務,而對於群眾文化團隊的類型建設上,並沒有做特殊要求。而在北京乃至全國的群眾文化活動中,合唱、舞蹈、書畫、攝影的比賽很多,但戲劇類比賽卻很少,扶持戲劇團體對提升基層文化組織工作的業績作用並不明顯。
另外,即使參加像“群星獎”這樣包含有戲劇類獎項的群眾文化活動比賽時,一些街道和社區為了保證能夠拿獎,更願意邀請專業的戲劇工作者來進行創排,而非職業的戲劇人反而可能被攔在門外。“你有時會感覺自己就像透明的一樣,所有人都看不見你。”曾經四處尋求資金支援而碰壁的吳嵩略帶傷感地説。
朝陽區文化館一直對非職戲劇呵護備至。如今頗有知名度的非非戲劇節和大學生戲劇節等非職戲劇活動,都是這家文化館搭建起來的。文化館館長徐偉認為,目前一些政府機構對於非職戲劇團體的幫助,往往還停留在福利發放階段,非職戲劇人能否得到扶持,經常要看緣分、碰運氣,“戲劇雖然小眾,但也是群眾的文化需求,成立非職劇社是他們的文化權益,這種權益應該得到保護。”在他看來,基層文化機構的負責人應該更新自己的觀念,切實保護來自民間的這份藝術熱情。
對話北京劇協秘書長楊乾武:戲劇是最好的美育課堂
記者:現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非職戲劇社?對職業戲劇將産生怎樣的影響?
楊乾武:戲劇作為高度綜合的集體文藝生活,從來就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內需。非職戲劇社的涌現,説明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要求更高了。非職業戲劇可以被稱作是職業戲劇的文化土壤,或者説是職業戲劇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培養更多的戲劇觀眾。比如,9劇場推出的非非戲劇節,其實也是為了吸引更多觀眾走進劇場。
記者:時下的商業戲劇有很多問題,非職戲劇身上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東西嗎?
楊乾武:非職戲劇人熱愛或喜歡戲劇,有自己的藝術追求,卻不以盈利為目的。這種健康理想的非職戲劇蘊含著質樸本源的戲劇精神,推廣普及這種戲劇精神,或許可為當下一些過度娛樂的消費戲劇解解毒,防止劇場退化成低俗娛樂場所。
記者:有人認為非職戲劇降低了戲劇的門檻,影響戲劇的品質,您怎麼看?
楊乾武:當下的中國職業戲劇,尤其是國有主流戲劇,其門檻世界第一。但不是藝術門檻,而是技術、投資、票價等非藝術的門檻高不可攀。藝術門檻卻一低再低,陷於小圈子的自娛自樂,自我封閉,敝帚自珍。非職戲劇的目的正是打破職業戲劇的各種無謂門檻,廣泛普及推廣傳播戲劇文化,吸引更多人參與戲劇活動,關注戲劇的現狀。
記者:很多非職劇社往往受困于資金問題而難以為繼,您有什麼好的建議,政府機構應該如何看待非職戲劇?
楊乾武:一個國家戲劇文化與戲劇藝術的水準,決定了其大眾文化水準的高低。如英國、美國的電影,儘管高度市場化、商業化,卻仍然保持了一定水準,就是因為英美兩國的戲劇高度普及併發達。百老彙與倫敦西區並非孤獨的“空中花園”,支撐它們的是由數倍于百老彙與倫敦西區的非盈利戲劇,尤其是遍佈全國各地的校園及社區的無數非職戲劇構成的。建議各級政府部門,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潮流中,拿出鉅額文化投入的零頭,組建非職戲劇發展基金會,實事求是的幫助扶持全國各地的非職戲劇活動。同時制定落實相關的文化免稅政策,引導鼓勵企業資助非職戲劇的發展。另外將戲劇融入中小學素質教育課中,戲劇活動本來就是最好的集體美育課堂。
記者:您怎麼看非職戲劇未來的發展?
楊乾武:現在,非職戲劇的主力主要存在於大學校園,以及一些社區或單位之中。伴隨著教育改革,以及應試教育的慢慢淡化,希望戲劇活動逐漸向中小學普及推廣。社會上自發獨立的非職劇社,可以主動與各社區合作,將非職戲劇的發展與社區文化建設相結合。既可以提升社區文化的內涵及品位,也可能獲得社區政府的資源及資助,找到一個家,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