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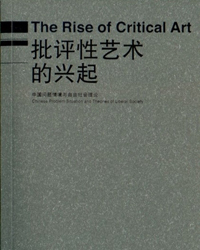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藝作品中,師傅帶徒弟往往是“又紅又專”模式主題的重要題材;到了“文革”時期,“紅”強“專”弱,階級鬥爭教育、無産階級專政教育甚至後來的評法批儒運動,都成為文藝作品中師徒之間最重要的交流內容。一種本來屬於技術知識傳承、生産技能培訓的關係,在政治話語和文藝表達的層面上被置換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與被教育關係。但是,恰好是在價值觀念的相互影響方面,現實生活中呈現出另外的真相:一些年輕的師傅帶著徒弟偷聽香港電臺、躲在廢棄倉庫裏唱鄧麗君、為偷渡而練習游泳,技術和生活經驗的交流在一種共同的思想傾向中更好地實現。看來,學徒工制度的歷史研究也應該是多重角度的。
今天,學徒工的技能培訓問題除了在人才招聘中心會受到重視以外,在職業教育或勞動法研究中也有學者關注;面對近年來出現的勞動力技術素質問題,也有不少學者和官員以英國近年復歸新學徒制和德國一直堅持把學徒製作為職業教育的支柱以及澳大利亞、紐西蘭、芬蘭、奧地利等國的學徒制度作為借鑒。但是,這類研究似乎很難進入社會人文學科的主流學術殿堂。然而,美國政治學教授凱瑟琳·西倫的《制度如何演化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經濟學》(王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卻從職業培訓入手研究資本主義國家模式的多樣性,從學徒工和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的産生研究國家政治經濟運作的核心機制的形成,其角度之新銳和挖掘之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儘管作者在開頭就説“職業培訓並不是最閃耀思想火花的主題”,但她相信“在職業培訓故事中含有很多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理論方面有價值的洞見”(前言)。根據作者的表述,書中的這些洞見可以主要概括為:通過深入考察十九世紀技能密集型産業中的僱主、傳統工匠以及早期工會這三個關鍵群體之間所達成聯盟的不同,揭示出德、英、美、日各國技能形成軌跡差異的根源;通過研究各國在早期工業化時期的技能形成體系與集體談判制度、新興工會以及僱主協會之間是如何互動的,進而揭示這些互動方式如何形塑了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發展路徑;研究的結果指出了德國與日本之間(“協調性”市場經濟國家)以及英國與美國之間(“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在技能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相似之處和這兩對國家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從較為具體的範疇來看,雖然德國的技能培訓體系被正確地認為是一種關鍵的制度安排之一,它一直支撐著德國高技能、高工資及高附加值的製造業經濟和“異質多樣化”的生産體制,但是本書對這種體系的歷史起源所作的研究表明,它在十九世紀末的出現是基於深刻的反動政治動機,主要是為了削弱(絕不是加強或者收編)新興的工會運動;這一體系形成以來,經歷了政治體制的變更、戰爭的衝擊、外國的佔領等歷史考驗,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和漸進的適應性調整。從理論上看,作者強調了在考察制度的成因和變遷中,不能把制度的功能與成因混為一談,強調製度是具體的事件進程和政治鬥爭的産物(參見第21-22頁),這種歷史的和微觀考察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對依賴功能模型等理論傾向是一種糾偏;另外,強調了在制度創始與制度再制這兩種分析之間的聯繫,從而有助於認識制度與政治的延續性問題。
把上述問題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多樣性在未來的發展趨勢這樣的論域中考察,作者的研究主旨就並非僅僅是歷史學性質的,而是更具有發展前瞻的意義:了解制度在過去的演化歷史是為了洞察其在今天的變遷發展。我認為對中國的技能培訓問題來説,本書提供的借鑒和啟示是多方面的。比如,技能培訓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而且會對多樣的社會政策與制度安排産生重大影響。在近年來關於“技工荒”的討論中,人們已越來越意識到它的産生和解決都不僅僅是職業教育系統和生産企業系統內部的事情,而是與更宏觀的社會安排緊密聯繫在一起。又比如,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監督管理機制,即便像富士康這樣必須向工人提供一定的技能培訓的企業也無法保障雙方的協調性發展;在國家威權主義的管轄下,企業與工會之間的新型博弈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將受益於一種積極的技能培訓體系。
藝術批評家和獨立策展人王南溟的新著《批評性藝術的興起中國問題情境與自由社會理論》(古橋出版社,2011年5月)是作者近年來對有爭議作品和所策劃展覽所寫的評論集,以中英文對照的形式出版。關於前衛藝術與現代藝術、當代藝術的概念關係,作者作了自己的明晰界定:現代藝術從塞尚到波洛克走完了它的形式自律過程,前衛藝術則從達達主義延伸到當代藝術,主張藝術即生活、藝術要介入社會。只是因為在前衛藝術中出現了沒有觀點和立場的現成品,從而使以批評性為內在核心觀念的當代藝術成為必然,他由此而強調從語言哲學向政治哲學的轉變是當代藝術的理論基礎(第18-21頁)。我想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先鋒派(即前衛藝術)這個比喻最初屬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理想,1878年巴枯寧在瑞士出版的雜誌就取名為《先鋒派》。從一開始就有兩种先鋒派,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在兩位著名的象徵派詩人身上,可以看到這种先鋒的體驗:蘭波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拿起了暴動的武器;魏爾倫因對公社的同情而受到指責。“這一代人不僅熱愛文學,同時也關心政治。”(參見雷納托·波吉奧利《先鋒派三論》)這是前衛藝術的思想根源,王南溟想力圖説明的也正是這一點。
比藝術史概念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從中國符號到中國問題情境的問題。作者強調藝術要介入中國問題情境,反對簡單地挪用中國符號以及在其背後的後殖民秩序。如何從中國符號走向中國問題情境?作者認為藝術家除了要有發現中國問題的能力以外,還要有自由表達的勇氣和社會機制對藝術自由的保障。接著作者舉了兩件作品為例:蔡國強的“龍”在後殖民中是中國符號,又被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解釋為龍在騰飛;而金鋒的《秦檜夫婦站像》讓在岳墳前跪著的秦檜夫婦以雕塑的方式站了起來,由於涉及潛意識道德和現代法律意識之間衝突的人權問題而被禁止展出。不管作者對這兩件作品的解讀是否完全有道理,從中國符號和中國問題情境來進行區分是合理的。
“在一個問題不斷出現的國家,讓討論社會問題成為藝術的關鍵詞。”其實,從“符號”到“問題”這也是當下中國社會人文科學界的中國研究和表述所遇到的共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