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畫壇,何水法無疑是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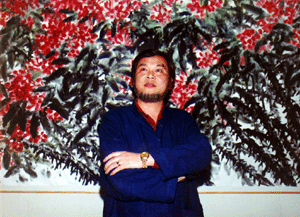
前段時間,出版社的朋友約我編一本寫意花鳥畫的集子,權衡再三之後,還是作罷了。我給我朋友的理由也非常簡單,我説,意筆花鳥畫到了何水法這個境界的實在太少,編出也沒什麼意思。朋友臭我太理想主義,説我太不切實際了云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如此的理想主義、如此的不切實際,儘管誰都知道明清以來的意筆花鳥畫家個個兇猛異常,縱向的比法的確太為難別人。在我看來,上個百年,吳昌碩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暗示一種高峰的確立,然而齊白石以民間色彩入畫,潘天壽以奇險造勢,黃賓虹(花鳥作品)以冷艷取勝,皆開創了一個新的天地,所以,從這個方面考慮,何水法似乎深諳此中道理,並在不斷地實現著自己理想的同時,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他把自己的創作置放在意筆花鳥的發展歷程中予以全方位觀照,並不停地調整著自己的坐標,取得不俗的成績。
我在不止一次的公開的場合上,鼓吹著意筆花鳥在當代大文化背景之下的式微,而且也常提意筆花鳥是當下“做畫”風的一種最有力反撥,當然,在言談中我舉例總會搬出何水法做為我的佐證。
這並不是説,我因為撰寫這篇文章而要為何水法貼上一些“金”。事實上,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根本就沒往深處想些什麼,只覺得在視覺上何水法的畫比較吻合我的欣賞口味。我甚至喜歡他筆下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那些“印象”很濃的像花一樣的植物。或許我所喜歡的是這位極具開放自由精神、敏銳、準確地捕捉了現代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並把這種關係巧妙地融于尺素之中的方式。到了今天,何水法約我為他的作品寫些文字的時候,我才不得不慢慢梳理起案頭的有關資料。
在1973年前,何水法還是用工筆的形式在宋元的遺風中尋找著自己所必須儲備的營養。此時的他甚至還沒動過畫寫意的念頭。開始畫意筆原本也不是他的初衷,據説,是他的老師陸抑非先生要他畫的,他自己並不想畫。1978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讀陸抑非先生的研究生。既然是從師學藝,想不學也難了。兼工帶寫的東西漸漸佔據了他創作作品的份量。直至他進了浙江畫院後,仍然有很長一段時間,創作出的作品也沒有脫離這個範疇。
很難説他的變化是從某年某月開始的。也許是在某次觀摩畫展中,也許是在朋友家酒酣耳熱之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他體內沸騰的O型血液,及他鮮明的個性起到了某種決定性作用。集大氣與磅薄,淋漓與生動於一體的水墨大寫意,與他作為藝術家的“狂”的氣質,達到了一種無形的默契。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曾經與他戲言。我説,這是一場置死地而後生的出走。眾所週知,工筆和寫意是中國畫的兩個端點,想兩者兼得猶如高空走鋼絲,玄得很。別的不説,沒有過人的膽識和勇氣,是很難走下去的。走不出,便意味著可能要在裏面轉悠一輩子,而且哪方面都轉個不三不四;走出來,便是嶄新的另一片天。從某種意義而言,何水法應該是一個冒險家,而且是一個成功的冒險家。
誠然,僅靠膽識來走這條鋼絲是遠遠不夠的。悟性和才氣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作用。1991年,有浙博裱畫間裏看到黃賓虹的一張花鳥畫在裱,其中有一張牡丹,因為筆沒有洗乾淨,摻了一些花青,倒是別有的韻味。黃賓虹可能是無意的,但何水法是有心的,他似乎從中悟到些什麼。在這以後,何水法的牡丹就開始用花青了,鮮艷的紅、亮麗的黃,其中摻和著屬於冷色調的花青,他的牡丹變了,變得渾樸,變得厚道,變得富有了內涵,色艷而不俗,墨韻而不滯。
談到色彩,談到花鳥畫中的牡丹,人們很容易傍上“匠氣”、“俗”這樣的調語。且何水法又是以畫富貴牡丹著稱的,風言風語自然在所難免。其實,何水法的牡丹作品中的用色和他其他作品一樣,色彩鮮亮、透明,有潑的一面,也有收的一面,有儒雅的一面,也有大氣的一面。且在表面形式上與傳統文人畫又有所不同,但總體審美範疇並沒滑出“文人畫”的傳統。他走的是一條“傳統出新”的路,他固守的只是中國文人畫的精神而非形式。畢竟他現在所處的時代、環境等與古人不同了。在這個資訊時代,點擊滑鼠就能知道古今中外的事,這是讓古人想破腦袋也想像不到的。其次,還有他的經歷,個人氣質,認識問題的方式都與他人顯然不同。這樣理解的話,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內在的精神實質和他的獨到的見地。
在表現中國畫與用水之關係中,何水法更是棋高一著。我沒有問過何水法以前是不是就叫今天的這個名字,他的水法名從另一角度就是他畫中一個明顯的“商標”。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水法通則人法通》,文中這樣寫道“我以為,水之用法是否得當,著實是影響一幅畫之意境與神韻的”。由此看來,何水法對水之功用是經過一番思量的。俗話説畫形易而畫神難,神韻就得靠筆墨之表現,水法之妙用,方可得其妙境,超乎象外。何水法大寫意作品。尤為注重水之妙用,無論是一個花一草,皆筆墨華滋,渾然天成,氣韻生動,讓了耳目一新,這與他大膽用水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來,筆墨是中國畫之靈魂,而水之妙用是筆墨中之核心。法度之中合理用水,墨色才活,才能色潤而不枯澀死板,才能顯其神韻。從何水法的畫中不難看出他對明清意筆經典的承繼,同時又透出他自己所獨具的秉性,意在筆先的膽略與氣魄,導致其作品中那成竹在胸的瀟灑自如,從而出現水墨交融,色墨輝映的神妙。
解讀過何水法的作品,還會發現一個頗值把玩的視點。中國畫有中國畫的觀察方法,西洋畫有西洋畫的觀察方法。山水畫有山水畫的觀察方法,花鳥畫有花鳥畫的觀察方法。雖不一一而足,但也有大致定論。譬如,山水畫的觀照方法一般是畫遠景,花鳥畫一般是畫近景,傳統的畫是折枝的多,所謂“賞心只有兩三枝”,便是如此,在以前,何水法也是這般觀照的比較關注一花一木,而近年來他開始轉向全景式的構圖。視覺上觀照的是遠景,而不是近景。這在別人法眼,似乎是本末倒置了,基於視覺觀照的改變,他在不經意中瓦解了一般的品讀習慣,把讀者帶入一個新的視覺空間,其作品也越來越傾向一些感覺的東西。作品的一切首先服從於整體,把筆墨僅作為表現整體的一個局部,或者一個章節,這樣拘泥形的東西少了,發揮的空間和隨意性的東西便多了起來。
在這個張揚個性的時代裏,何水法以其色墨交輝,一味霸悍的風格穩穩地佔據了一席之地。或許這位藝術家的個案並不能證明當代意筆花鳥畫領域的特徵,不過,話説回來,何水法的觸角以及他的實踐卻讓人們看到了意筆花鳥畫領域可待挖掘的資源還有不少。
(作者: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