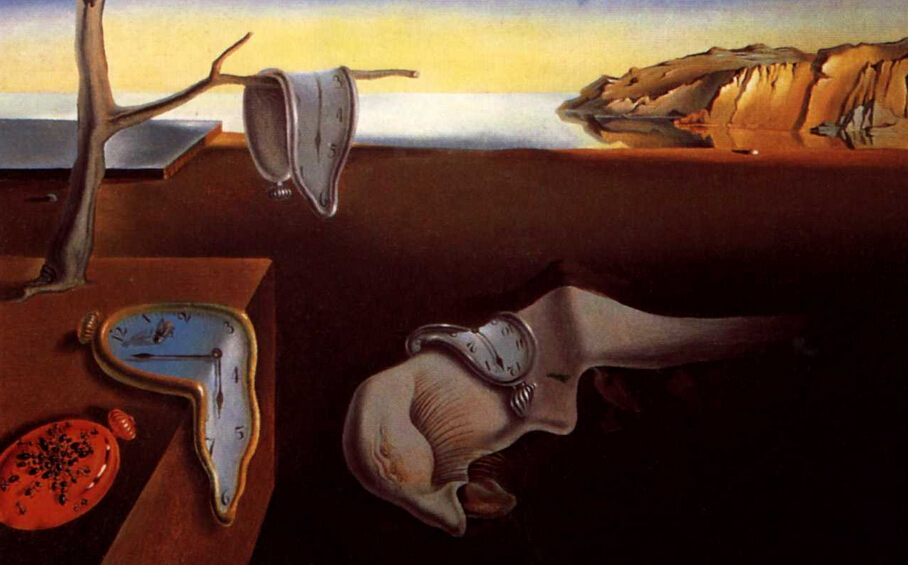
有一天,一位朋友問我:作為經濟學者,你分析了好多生命的行為和現象,包括情感與審美,可是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呢———我指的是,完完全全來自個體的,與你的教育和文化無關的生命。能不能告訴我一些你的生命體驗?
這是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難,就難在準確地捕捉住自己的生命體驗和狀態。
對我來説,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所遇所思不過像蒲公英一樣,飄然而來,飄然而去,全然不留一絲痕跡。但生命中,也有一些東西,像風雨過後的泥土,先被沖刷,漸漸沉澱,直至融入生命的最深層。多年以後,即使細節全然忘記,記憶卻更見鮮明。
它們是生命火山中的岩漿,流出後凝固成石頭,再成為我生命河床中最堅硬的底部。
年歲愈長愈清楚地知道,這些記憶就是我的生命,生命無非記憶。
母親,是記憶河床中最溫馨、摯愛的部分,牢牢佔據著我記憶的中心,卻不敢輕易碰,不敢寫一字。因母親太苦了,我是她最鍾愛的小兒卻未曾有過滴水的恩報。
滌去許多酸甜苦辣,我願記取母親在冬去春來的日子,利落地抱滿懷棉被拆洗、晾曬。那樣的日子,春日的花朵格外美麗,天空的太陽格外溫暖,漿洗的棉被上太陽的清香至今仍讓我回味無窮。日子悠長,康健的母親竟闊別我已達13年之久。
童年,是生命記憶河床中最歡快的部分。青山綠水、藍天白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上山可摘果,下河可摸魚,只道是歡歌無限,又道是夢中天堂。
多少年了,童年的一草一木卻像刻石一樣永不忘懷。就像沈從文夢中的湘西,白塔、黃狗以及翠兒。
後山是我兒時的最憶。有參天的楓樹,在風雨夜它們會呼嘯作響,讓人驚恐。但在平時,我和小夥伴們盡可縱情嬉戲、捉迷藏、奔跑,痛快地消耗和生長著童年時的力氣。
我從未上過幼兒園,但後山對我來説勝過天下所有的幼兒園。事實上,後山已入我靈魂。我,註定永遠是那個後山少年,在塵世與城市卻不過是匆匆過客而已。
所可嘆者,童年的夥伴早已不見蹤影。在那個下放的歲月,我幾乎是村裏唯一的男孩。説唯一,是因為村裏還有一個啞巴兼傻子的男孩。與我年齡相倣的女孩倒有五位之多。一起上學時,我便成了這五朵金花中唯一的綠葉。
記憶中這五位女孩都很能幹,活潑可愛。可惜,自我上高中開始,她們竟一個個早早嫁人,而我未及對任何一個道聲祝福。
上學後,不能磨滅的記憶亦有許多。奇怪的是,原來以為很重要的一些事已變得不重要,原來並不看重的一些事在記憶中卻如火星般閃爍。
讀周作人,才知道初戀原可是不經表白的青春騷動,併發現自己可能也是有過初戀經歷的。只是當時的表達方式格外奇特:明明心裏對一個女孩子有好感,卻故意找茬和她吵架,看她紅顏皓齒因生氣而格外有生氣。
某一年的一個冬天,我自外地來到縣城車站轉車回家,竟不期而遇闊別的她。彼時的她是位懷抱小兒的年輕母親。我拿出從上海買的大紅蘋果送上,她竟全然不問不顧小孩,獨自痛咬起來,眼中淚光盈盈。我無言以對,落荒而逃。
一切都已老去,包括這樣的純潔與有趣。就像一條遠帆的船,我已飄離童年和故鄉遠矣。只是,在午後、在黃昏、在子夜,如許的記憶卻會時常泛起,讓我嗓子發幹、難以動彈,惆悵莫名。
我們在人世的日子原本苦短,就如同影兒飛過。傳道者説,“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所幸有這些記憶,它們是我生命中的記憶珍寶。
我會提醒我自己,往事如風,生命真的就是殘留的記憶,除了這些真摯的東西值得收藏外,所有的一切都會不留痕跡的。
因此,不必太過看重和強求。這大概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有點遠,而與隨遇而安的尋求次優選擇的有限理性人比較接近吧!
推薦《行走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