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寫出多情的敦煌
發佈時間:2024-08-20 09:00:19 |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作者:陳繼明 | 責任編輯:孫靈萱陳繼明
2018年,我的長篇小説《七步鎮》缺一個合適的結尾,我和責編付如初進行過細緻討論,一直舉棋不定。後來我把另一部長篇小説數千字的開頭直接移植過來,做了《七步鎮》的結尾,她只留下了其中的1/5。這個結尾也就無意間牽出我和她關於“下一部寫什麼”的一次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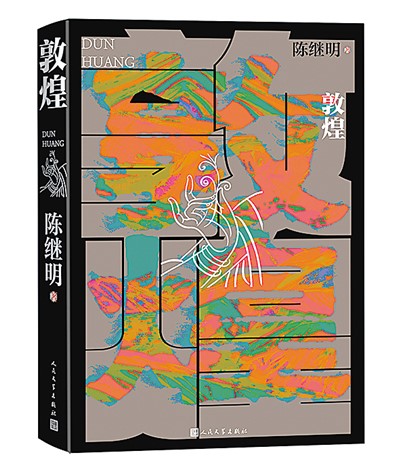
《敦煌》書影
我預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原本是另外一個故事。付如初則建議,乾脆“寫寫敦煌”。我問為什麼,她説了很多,大致有三層意思:一是,西部是一個容易寫出好長篇的地方;二是,敦煌是寫不盡的,你是甘肅人,為什麼不寫寫敦煌呢?三是,你有以小見大的能力,你是可以鑽進去的。
她的這些話打動了我。我當時就答應了她,我説,給我幾年時間。
接下來,我一邊寫別的東西,一邊在“半真半假”地準備“寫敦煌”。作家大概都有這樣的習慣,讓一部小説先在頭腦裏生根發芽、慢慢生長,給它一個長大的過程。或自覺,或不自覺;或有意,或無意,我也一樣。這個過程必不可少,沒有例外。這期間,閱讀、記憶、經歷、想像,勇氣、懶惰、頹廢、恐懼,理性、情感乃至種種偶然、一切見聞、生活本身,所有的東西都成為頭腦中那個故事的“氧氣”,供養它默默成長。也許用了半生的時間,也許只是兩年三年,它終將成為一個模糊的生命,呼之欲出,到了不寫不行的程度。
2021年,我正式開始寫“敦煌”。
開始寫的時候才知道,頭腦中的故事近似于空氣。頭腦中的一切,現在僅僅變成了一種私密的富有誘惑的寫作衝動,巨大的麻煩剛剛開始。人物、時代、節奏、結構、篇幅,都要一一考慮。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險,不能缺少精心、細緻、科學的籌備,這個階段我當然並不陌生。但是,寫敦煌,艱巨程度還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很多次,我沒信心寫下去了。付如初問過我幾次,開始了沒有?我撒謊説開始了,幾千字了。其實還沒動筆。總之,這部小説的開頭是我寫作史上付出心血最多的。好在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決心,2022年初,我終於可以寫下去了,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寫完初稿。
長篇小説《敦煌》的故事發生在唐貞觀年間,主要設計了三條線索:最主要的一條是唐王李世民的畫師祁希來到敦煌後的故事。小説中,祁希天賦過人、早慧,學藝師從閻立本等名師,曾隨李大亮的部隊征討吐谷渾。來到敦煌後,他隱姓埋名,一為體會壁畫藝術的高妙,二為了解民瘼以為朝廷決策。我想通過他這條線索,捕捉敦煌的藝術色彩,書寫唐王朝和西域的關聯。
第二條是吐谷渾人。歷史上,吐谷渾為唐所滅。小説中,吐谷渾兵敗之後,貴族慕容豆跑到敦煌,意圖隱身以“活國”。不料,他與漢族女子足娘産生深深情愫,上演了一場地老天荒的愛情。這條線,一為呈現敦煌的多民族雜居色彩,二為反映民族融合的歷史。
第三條是敦煌本地的漢人令狐一家的悲歡離合。有了這條線,敦煌的日常和風沙綠洲一起,呈現在讀者眼前。
但我不想把《敦煌》寫成常見的歷史小説。換句話説,我想讓這部寫歷史的小説,具有足夠的當代感。只是有當代感,不見得要寫成所謂的當代小説。好在,在這樣的兩難境地中,我找到了一種敘述的方法和語氣。另外,我特別加入了一個現代人,他自認為是吐谷渾的後代。我用“元小説”的技法,讓陳繼明也出現在小説裏,讓他和我成為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離世。在小説裏,我盡可能把他寫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真切的痛苦和掙扎。

陳繼明近照
人,是文學的重心。在這裡,敦煌壁畫中的眾神與人的距離如此靠近。人性,人的命運,人的尷尬,顯得比任何其他情況下更加清晰。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鏡子裏。敦煌是鏡子,千佛洞是鏡子。在鏡子面前生活的每個人,同時是自己的“終極關懷者”。他們生活在當下的一時一刻,也生活在“總體糾結”中。我希望,通過《敦煌》,每個讀者也成為自己的觀眾。看書中的人物等於看自己。實際的效果最好是,人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敦煌。
既然想讓這部小説跟所有人産生聯繫,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野心,也隱藏起我的匠心,我想讓讀者看到的樣子是,散散漫漫地寫,駁駁雜雜地寫,平平常常地寫。當然,我仍然要寫出緊張感。只不過,我想寫出一種別樣的緊張,看不見的緊張。當故事的發展遇到一些重要關口時,我可以選擇大片講故事或者商業片寫橋段的路數,但是,我不。我選擇躲開,選擇走向人心,走向生存。關於敦煌的小説,我想對故事和人都懷有足夠的敬意。
當然,讓我抱有敬意的,還有天地萬物。從一開始,我就堅定地認為這部小説裏不能缺少動物。比如狼、駱駝、羊、老鼠。它們不是點綴,它們和人的故事始終並駕齊驅。他們是敦煌的靈性,是藝術的靈感,是天地的見證。總之,從各個方面,我都想寫一部不僅僅和敦煌擦肩而過的小説。換句話説,我想以最大的勇氣直接進入敦煌的內部,寫一部觸及敦煌心魂的小説。
這個心魂,少不了女性。唐代的女性,多姿多彩。在唐代長安、洛陽等大城市,胡女是一道風景。唐代的敦煌壁畫中,女性的數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形象自然飄逸,充滿朝氣,她們在天地間自在飛翔。所以我想在這部小説裏好好塑造幾個女性形象。足娘、令狐琴、智忍花、虞月、三娘子……每一個我都用了情。
是的,寫這部小説,我在史實準備、細節儲備之外,投入最多的就是感情。我想寫出多情的敦煌,它博大、憂傷、慈悲。它被眾生塑造又俯瞰眾生,它養育眾生又被眾生養育。我只想循著自己內心對敦煌的愛。所以,寫作之前,我並沒有任何先在的結論。關於民族融合,關於文明進程,我和讀者一樣充滿好奇。我想首先還原事件的繁雜性、豐富性和在地性。在敦煌,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人,在所有複雜的事件中,人的表現是怎麼樣的,無論漢人還是吐谷渾人。
初稿完成後,我第一時間交給付如初。她提了很多建議,很有建設性。然後我又用一年時間進行修改。一年中的大半年,我棲身於廣東珠海的一座小島上。可以説,現在小説中一半的氣質來自修改。改完之後我再給付如初,她有了一些零碎的好評。然後,她開始邊提意見邊鼓勵,我於是再改。得到這位第一讀者真正的好評,是在校對的時候。實際上,直到出版前,我們仍然在討論局部的修改。
可以肯定,這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部小説,也是我迄今為止最滿意的一次寫作。作為一個西北人,我終於給敦煌畫了一幅像——我心中的像。它帶著唐朝的沸騰,也帶著今天的安寧。一定會有人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跟我的作對比,我心裏是歡迎這種對比的。我想,我的《敦煌》或許更是屬於我們的敦煌。
(作者係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