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將屬於江河、湖泊的時光溫柔挽留
發佈時間:2022-12-02 09:15:00 | 來源:文藝報 | 作者:教鶴然 | 責任編輯:教鶴然:在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之前,您的散文《大湖消息》已經引起文學界的關注。能否請您談一談這部作品的創作歷程?
沈念:《大湖消息》去年12月出版後,入選了很多新書榜單。有人問,這本書寫了多久?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從我開始寫作,就一直是在處理洞庭湖這片河汊眾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地方性格、地方經驗和地方故事,各種耽擱,遲遲未能集中精力進行系統地書寫。緣起是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長江到了我的家鄉岳陽,提出“守護一江碧水”的要求。2020年下半年,疫情稍有緩解,湖南省啟動“青山碧水新湖南”的創作活動,我把寫作提上日程,又選擇性地回訪洞庭湖和長江,多數篇章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時間裏寫完的。寫了一年左右,但感覺又是寫了很多年的湖區生活經歷。
洞庭湖是湖湘大地上的母親湖,這是一個宏觀上的認知。我對它的認知也是逐漸加深的,越了解它的過去和現在,就越加關注它的未來。我曾經有一種深深的愧疚,這種愧疚來自我對這片土地索取的多,回報的少。當我再次回去,似乎所有的積澱都發生了化學反應。這就變成了一個寫作者與故鄉的“歸去來”。每一次折返,都是一次發酵、一段情話、一種碰撞,更是很深程度上的靈感激發。
這本書的寫作凝聚了我對故鄉的深情與眷戀、憂思與憧憬。我與那些候鳥、麋鹿、植物、魚類、漁民、研究者、志願者的相遇、相識,我選擇的人物,也是我遇見的人,這都是一種緣分。我特別看重這樣的遇見。我和他們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江湖兒女。我在“打撈”他們的人生往事時,其實是將屬於江河、湖泊的時光挽留,是在感悟並學習承受艱難、困阻與死亡,是嘗試以超越單一的人類視角,去書寫對生活、生命與自然的領悟。我的初衷是還原一個真實的湖區生存、生活世界,書寫一個有情有義、有悲有喜的人世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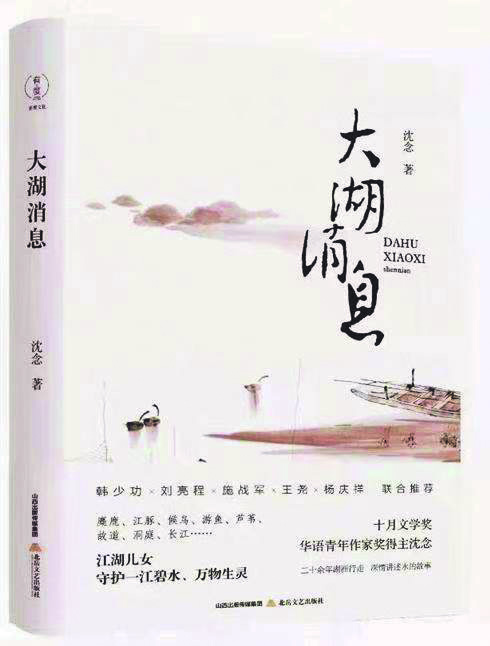
教鶴然:承接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到五四時期的雜文、小品文,再到新時期以來散文寫作的轉向,當下散文創作受到非虛構寫作的影響,也出現了美學風格的新變,據您觀察,當代散文的整體現狀如何?
沈念:我是當代散文這棵枝繁葉茂的大樹上的一片葉子。我沒法用幾句話去談論散文的當下整體狀態,只能是從我的閱讀偏好中,從我所能感受到的枝條顫動、樹木搖晃中談一點認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種文體有一種文體的漸變與豐富,當下語境裏,現代性敘事意義上的散文寫作已經越來越為人所跟隨、認定。表達現代生活的複雜經驗,説別人沒説過的言語、感受、邏輯,才會有真正意義上個人性的呈現。沒有個人性的東西,就沒法標識出你的風格特徵,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寫同一本書,這樣的創作是必須警惕的。
談到《大湖消息》,有人可能會談到非虛構或虛構的話題。任何寫作只要進入一個主觀表達時,它就會發生位移。只要是站在一個主體真實情感上的寫作,就不應該被虛構或非虛構所困囿。我反而會覺得,通過文體的開放性,小説、詩歌、戲劇這些元素加入進去,作品就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它變得不一樣,産生一個跟過去、跟很多人的寫作不一樣的新面目。不管寫什麼、怎麼寫,每位寫作者筆下的人物、命運、故事,那種現代人複雜經驗帶給他人的共鳴、共情,這才是最真實、最重要的。
教鶴然:您的《大湖消息》有很多“標簽式”的評價,比如“青山碧水新湖南”主題創作非虛構作品、比如生態寫作理念下的散文作品等,對您個人來説,這部作品應該也有著比較重要的意義,您覺得,這些評價是否貼切您的創作初衷和核心理念?
沈念:我沒有過多考慮過被貼什麼標簽,因為一次寫作完成了,需要考慮的是下一部作品。但從評論和媒體的反饋,有不同角度的解讀。山可平心,水可滌妄。《大湖消息》凝聚了我對大湖的書寫理想,折射出我對這片土地上的人與萬事萬物的態度。
任何一個地方的元素和精神內涵,歸根到底落點還是在人和物的身上呈現。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永遠是不可能均等的取與舍。從這個意義上出發,每一位投身自然生態文學書寫的寫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慾望帶來的責難,要去書寫反思與自我拯救。而我就是要從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創作”一個未來,那裏有對大地上、人世間最坦誠的信任和依賴,也是寫下獻給未來的“洞庭湖志”。
教鶴然:還記得您曾經提到過“魚腥味”與南方寫作的文化性格,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南方氣質與“島嶼”經驗是地方性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您的作品中,“水”似乎是很重要的意象,語言也充滿了潮濕、細膩的情感質地,的確與帶有北方風格的寫作者有明顯差異。那麼,您是怎麼理解地方性經驗與個人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
沈念:洞庭湖是我創作的原産地。我在洞庭湖的水邊生活了很多年。水,給了這片土地靈性、厚重、聲名,也給了人刁難、悲痛、漂泊,更是給了我寫作的靈感和源泉。長久以來,我睜眼閉眼就能看到水的波瀾四起,聽到水的濤聲起伏,水的呼吸所發出的聲音,是液態的、顫慄的、尖銳的,也是龐大的、粗糲的、莽撞的。水能把一切聲音吸入胸腔,也能把聲音擋在它鏡子般的身體之外。我原來以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沒有邊界的,飛鳥、遊魚、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區的人,都會把水帶走,帶到一個我未曾想到達的地方。還有那些曾經沒有戶籍的漁民,沿著水流四處飄零的人,他們所賴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們是本源上的江湖兒女,他們的流動性所孕育出來的地方性格,是走到哪,就傳宗接代在哪。他們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把自己交付給陌生人的勇氣,這與水的流動性天然地關聯在一起。
我在寫作地方性經驗時,是保持著“小地方人”的謹慎的。這種謹慎,是提醒自己要把記憶中最深刻的經驗和細節,融入到對世界和自然的看法之中。一個人寫作的落實過程,就是要把一個地方寫實寫透。地方性經驗于我,既是熟悉的寫作,又是有難度的。《大湖消息》于我是一次有難度的挑戰,面對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書寫視角是多維的。鳥不只是屬於天空,魚不只是屬於流水,水不只是屬於江湖,植物不只是屬於洲灘,人不只是屬於大地,它們所組成的生命有機系統,任何一個環節的塌陷和破壞,都可能導致系統的紊亂。文學要呈現的就是為這個有機的生命系統立心、立命,要把生命中難以表達的情感傳遞出來,在“所見”與“所信”之間,讓個人的寫作被生活與美學“雙重驗證”。
教鶴然:您是散文和小説的雙面手,包括在《人民文學》發表的《長鼓王》、在《十月》發表的《空山》等作品,而後又結集出版《燈火夜馳》。您選擇以“文化扶貧”“易地搬遷”等主題作為表現扶貧攻堅成果的切口,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寫作方法是否也影響著您的散文寫作?尤其是您之前的基層經驗和多年記者工作的積澱,想必也為您的文學創作打開了一扇窗。
沈念:前面提到過,為了寫《大湖消息》,我反覆地回到洞庭湖走訪,這是一種深入生活,直接影響到了寫作的成像。作家是時間裏的人,也是改變時間的人。作家在這個時代裏生活,就是在創造新的時代與生活的文學記憶。我的下鄉經歷、記者工作,不僅為我的寫作,也為我的人生打開了一扇窗。我在這個窗口盼望,看著外面的日月星辰、風霜雨雪,看著走過的足跡和擦肩而過的眾人面孔,愈加會從心底告誡自己,認真對待你筆下的文字和眼前的世界,努力寫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靈魂。
教鶴然:您曾經説過,寫作者要找到自己的根據地,並透露過想以小説的方式書寫洞庭湖,那麼,您未來的個人創作計劃是什麼?
沈念:“根據地”是寫作的底座與依託,你不斷回望它,它就會給你頓悟與創造的激情。寫作者的根據地永遠在同行,甚至在後面推動著往前奔跑。我今年在寫一部鄉土題材的長篇,散文創作停了下來。我反覆在提醒自己,洞庭湖是一塊豐富、駁雜的創作根據地,依然是要一頭扎進去。寫出與時俱進的時代之變、生活之變、文學之變,也依賴於把“根據地”扎深,寫實寫透。我不是那種有遠大抱負的人,但也正是這種“沒有”,讓我能在一條認定的路上不管不顧地往前走。
人都須為選擇而背負,好的或壞的,絕望的或倔強的努力。任何一條道路都不會是坦途,文學亦是如此,前面雖有風景搖曳,也得先穿過荊棘和叢林、沼澤與溝塹、黑暗與破碎。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肉體抑或精神,人類所面臨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糾纏不休的問題,大多是相似相通的。每一個寫作者都是圍繞著“人”進行著不同的書寫,我希望我的寫作是在創造一種新變和越來越闊大的可能性。我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洞庭湖是我生命中最有力量、最富情感、最具意義的一塊福地。未來我會寫一部關於洞庭湖的長篇和系列中短篇,這既是一個創作規劃,也是我心底的文學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