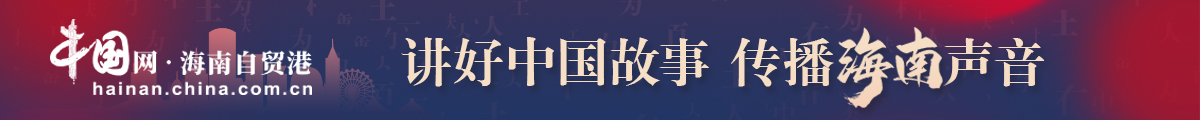
【內容提要】 融媒體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向國際社會呈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亟待從多層面增強對外翻譯和國際傳播能力,構建對外話語體系。長期從事國際傳播和外事翻譯的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總編輯王曉輝聚焦翻譯傳播這一核心議題,圍繞創新國際傳播策略、提升翻譯能力、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等熱點難點問題展開闡述,提出對外傳播需持續發力,文化翻譯須重視共情性,政治話語翻譯當體現嚴謹性,提升翻譯能力要把好語言關,對外話語體系構建是個系統工程。
【關鍵詞】國際傳播 話語體系 對外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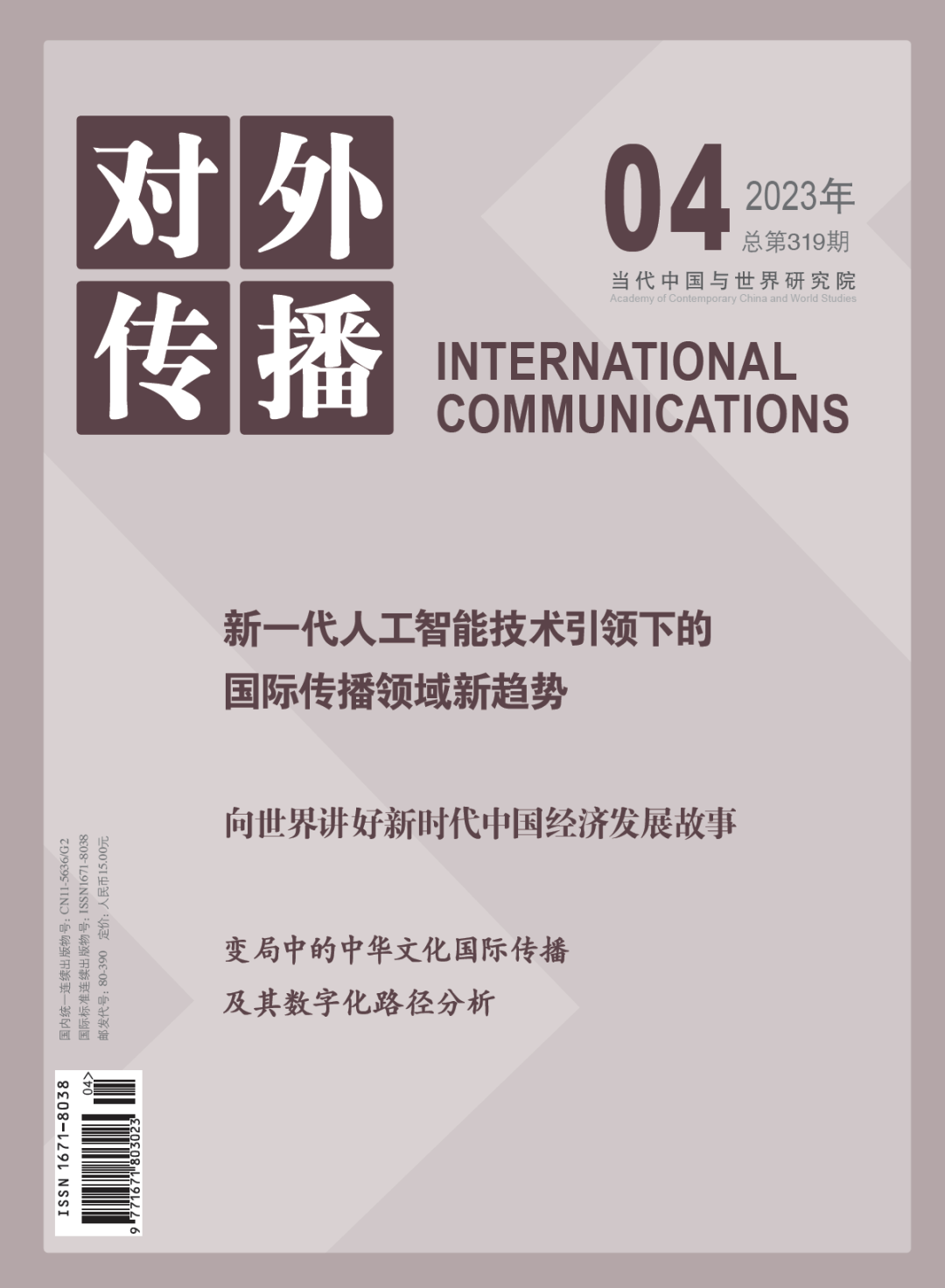
王曉輝係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黨委書記、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翻譯研究院副院長,全國翻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生導師,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王曉輝多年從事新聞報道、國際傳播、網路媒體管理和外事翻譯工作,多次擔任國際會議和論壇主持人,策劃並主持英文時事評論節目《中國三分鐘》和大型實景文化類訪談節目《似是故人來》,出版《換一種語言讀金庸》《丹青難寫是精神——〈紅樓夢〉英譯品讀》《一時多少豪傑——〈三國演義〉英譯品讀》等專著。2022年11月,王曉輝總編輯接受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副教授殷鴦專訪,將理論與實踐、親歷與案例融會貫通,多層面分析、探討了國際傳播、對外翻譯、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等熱點、難點、重點問題。
對外傳播要持續“扔小石頭”
問:您曾説過,“中國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但並不是每個故事都適合對外傳播”。您一般選擇怎樣的故事進行對外傳播?對外傳播應遵循哪些基本原則?
王曉輝:站在新時代,回望中國40多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100多年民族解放可歌可泣的奮鬥史,再上溯到中華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展望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國的故事確實太多了。怎麼選擇?不講中國共産黨的故事,中國的故事就主旨不明、主線不清;不講中國56個民族的故事,中國的故事就不完整;不講中華文化的故事,中國的故事就不生動;不講今天的中國,中國的故事就不形象、不具體。講好中國故事,以上四方面的故事必須講。很久以前,中國在世界上沒有發言權,沒有地位,或許可以不對外講中國故事。今天的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的故事就必須要講。
怎樣進行對外傳播?相關性、共情性和迫切性,是選擇對外傳播資源的原則。比如,2013年至2016年的南海爭端曾備受世界關注。當時,菲律賓當局在美國操縱下,通過臨時搭建的所謂“國際法庭”,把無效的、不合法、不合理的仲裁結論強加給中國。外國人大多不了解真實情況,以為中國以大欺小,所以講好這個故事就非常迫切,必須及時發出中國聲音。
怎麼講?要善於挖掘史料,及時講述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故事。例如,2014年,新華社《〈更路簿〉為昔日“海上絲綢之路”指點迷津》的報道稱福建、廣東沿海一帶漁民,過去家家有一本《更路經》,即航海日誌,通過畫圖、符號等來標記,從明清至今,幾百年代代相傳。後來,隨著半導體技術和導航技術的發展,《更路經》失去原有實用價值而被大量銷毀,所以呼籲大家搶救《更路經》。我當時利用這個素材錄製了四期節目,題為《天書指路,海角再遠也是家》。通過介紹《更路經》,從一個側面説明,中國人的祖先自古以來就在南海這片海域生息繁衍,相關南海諸島是中國的領土。
問:您策劃並主持的英文時事評論節目《中國三分鐘》短短幾年已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基於您的實踐經驗,該如何增強國際傳播的親和力和實效性?
王曉輝:做國際傳播是一件長久之事,要有策劃、講故事、用外語、成系列,不能指望一篇文章、一個節目就改變局勢,也不能指望用一個“爆款”打遍天下。做“爆款”就好比是搬一塊大石頭扔到湖水裏去,砸出一個巨大的水花,但幾分鐘後湖面就歸於平靜,一切都會被淡忘。但是,系列小的節目、小的評論就如同不斷地往湖水裏“扔小石頭”,漣漪不斷,節目對用戶的影響力就持續存在,有利於培養用戶閱讀、跟蹤相關節目或欄目的習慣,增強相關産品和平臺的粘性。
短視頻的對外傳播,首先需考慮播出的平臺,根據平臺匹配傳播內容。如一檔節目在臉書(Facebook)上播出,考慮到傳播對象大多為年輕人,所選擇的內容相應要輕鬆愉快、生動有趣;其次,要適合網路傳播風格,避免使用機構語言。若用機構語言跟社交媒體上的廣大人民群眾去溝通,效果一定不理想。對外傳播要瞄準目標受眾,根據受眾採用相應口吻。
文化翻譯須重視“共情性”
問:文化是對外翻譯和傳播繞不開的一個主題。您曾強調“文化是對外傳播最好的一個抓手”。在《換一種語言讀金庸》《丹青難寫是精神——〈紅樓夢〉英譯品讀》等專著中也列舉了諸多文化翻譯方面的例子,您能結合書中案例,談談對文化翻譯的心得體會嗎?
王曉輝:文化是對外傳播最好的抓手,容易引起共鳴,具有共情性和相關性。大家往往本著對自己文化的熱愛,對其他文化的好奇和欣賞這種心態而相互走近、了解彼此。不帶意識形態的隔閡,最容易被人接受。
首先,文化翻譯,如同陳寅恪當年研究歷史一樣,需“了解之同情”。譯者是“橋梁”,引導讀者去跟作者交流。前提條件是共情,譯者須深刻了解目標語文化和本族語文化,方能擔此大任。在文化翻譯中,中國外文局有來自中外的很多知名專家學者、老前輩,均作出過巨大貢獻。比如,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譯有《儒林外史》《紅旗譜》《史記》《紅樓夢》《人到中年》等諸多文學作品。就《紅樓夢》翻譯來説,另外兩位漢學家,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約翰·閔福德(John Minford)翁婿組合也堪稱典範。正因“了解之同情”,才能將經典譯成經典。
其次,文化背景決定翻譯理念,不同的翻譯家翻譯同一件作品,也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例如,《紅樓夢》第四十一回,妙玉給賈母獻茶的茶具名為“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盤”,霍克斯和楊憲益兩位翻譯大家對“雲龍獻壽”這個表達處理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作為西方人的霍克斯更注重器物形象,譯為“a cloud dragon coiled round the character for‘longevity’”,把這一形象描寫得直觀、具體,沒有中華文化背景的外國讀者一讀便知。楊憲益則更關注文化涵義,譯為“a cloud dragon offering longevity”,突出“獻壽”(offering longevity)的意思。兩人殊途同歸,不分伯仲,但是文化背景不同,翻譯時不知不覺就會把文化內涵融入到翻譯選擇裏面。
此外,文化翻譯還需考慮意境、情緒和氛圍的傳達。越是民族文化背景特別強烈的,越要仔細。否則,要麼詞不達意,要麼失去原有文化的內涵,更多情況下,兩者都失去了。特別是中國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詩詞、成語和俗語,很多一語雙關,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邏輯鏈不復存在,難以有效傳達。
政治話語翻譯當把握“四特點”
問:您在時政文獻外譯方面也頗有經驗,您對黨的二十大報告的對外翻譯和傳播,有哪些看法和體會?
王曉輝:黨的二十大報告,政治站位高、涵義深刻、邏輯嚴謹。政治話語的翻譯不同於普通的翻譯,中英文風格需一致,變通的餘地不大。
首先,政治話語具有高度敏感性。比如,“中國大陸和香港”,很多外媒譯為“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容易使人誤認為“另有別的China”。正確譯法應為“China’s mainland and Hong Kong”。諸如“中國大陸和香港”“中國共産黨和八個民主黨派”等表達,在行文上一旦並列時,翻譯需特別小心。
其次,政治話語具有權威性,很多有固定表達,翻譯時不能隨意更改和變通。其中政治話語的行文有其特殊性。第一,長句多。比如,黨的二十大報告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弘揚偉大建黨精神,自信自強、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這一長句共86字,其中有獨立的四字成語、無主句和修飾語。政治話語裏修飾語的重要性絕不亞於動詞,翻譯時既不能省略也不能降低程度,這點尤為關鍵。
第二,慣用高頻詞。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漢語越重復,越激昂、越有勁,英語則越重復,越乏味、越缺乏表現力。因此,不能將句中三個“全面”一概譯為“fully”,而應採用多樣化表達方式,變換著譯為“fully,in all respects,on all fronts”方不顯單調。
第三,新詞彙、新表達層出不窮。比如“脫貧攻堅”“藍天保衛戰”“易地搬遷”“生態補償”“五位一體”“發揚釘釘子精神”“正確的義利觀”等,都需譯者認真去體會。以“藍天保衛戰”為例,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直譯成“protect the blue sky”則容易引起誤解,應譯為“make China’s sky blue again”才符合原意。再如“發揚釘釘子精神”,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拿“釘子”作比喻,但象徵性完全不同,中國人“釘釘子”強調的是“堅持”(perseverance),而英國人“釘釘子”強調“抓住重點”(hit the nail on its head)。比喻的事情和給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翻譯時務必分清楚。
第四,常有引用詩句的情形。比如,領導人講話時一開始説“女士們、先生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4月的北京春回大地、萬物復蘇。”這是一種引用方式。第二種引用方式是把詩嵌在中間,如“一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上最恢宏的史詩。”第三種引用方式是把好幾個詩人的詩句組合在一起,置於句中,如“從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憧憬,再到孫中山‘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的夙願,都反映了中華民族對擺脫貧困、豐衣足食的深深渴望。”對譯者來説,第三種引用方式最具挑戰性,單句翻譯抑或長句分譯?若採用分譯法,邏輯脈絡如何相連?都需譯者費一番思量。
提升翻譯能力要善過“旋轉門”
問:結合您的翻譯實踐,該如何看待母語能力、外語能力和翻譯能力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王曉輝:實際上,在兩種語言的轉換中,母語和外語是相互促進的,中文好便於對原文的理解,英文好便於對譯文的呈現,反之亦然。一些大師級的翻譯,如林語堂、錢鐘書,梁實秋、梁啟超、嚴復等,哪一位不是兩種語言的高手?因此,做翻譯工作,實際上就是在兩種語言的“旋轉門”中做遊戲,兩者缺一不可。成為一名好翻譯,除精通中英文,尚需其他方面的補充。傅雷先生曾説過,譯者須以藝術修養為根本,要有敏感的心靈、高度的同情、一定的鑒賞能力、相當的社會經驗。這四者缺一不可。
問:新形勢下,掌握必要的翻譯技術也是翻譯能力的體現。新媒體是人工智慧的重要應用場景之一,據了解,中國網在這一領域也多有探索創新。請問今後人工智慧在哪些方面可以更好地協助翻譯傳播?
王曉輝:人工智慧很重要,將來“人”與“人工智慧”,即“人”與“翻譯軟體”之間必然是互補、攜手並行的關係,絕不是替代關係。“山高人為峰。”人可以駕馭人工智慧,使其成為對外傳播的手段和工具,但不能過度依賴它。對外傳播事實可以借助人工智慧,但翻譯和對外傳播的目的是與人溝通,在社交媒體上,機器人則無法與媒體受眾産生思想碰撞。所以,有限的應用很管用,但是應用的對象、場景、平臺務必謹慎。
另外,網際網路時代,從事翻譯、對外傳播的人須有理解、掌握和應用新媒體的能力。因為時代變了,媒體的形態變了,媒體的受眾也隨之改變,對外翻譯傳播工作者必須適應新形勢,擁有新媒體能力,即營造互動、培養用戶閱讀習慣、增強産品和用戶黏性的能力。
構建對外話語體系是個系統工程
問:新媒體能力是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這方面能力需培養之外,您認為目前中國對外話語體系構建還面臨哪些困境?該如何突破?
王曉輝:對外話語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長期對外交往實踐中形成的一套能夠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和認可的語言表達方式,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語言表達的規則和套路,融入了一個民族的價值觀、世界觀、話語表達和思想方法。
首先,站穩中國立場。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第二,堅定“四個自信”。若無自信,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的根基就不穩;第三,內知國情、外知世界。亟需培養講述中國故事、講述自己歷史文化、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能力;第四,建立真正屬於自己的傳播渠道。中國在大型媒體和平臺方面與西方尚存差距,借臺講述中國故事並非長久之計,有自己的舞臺才能有觀眾;第五,培養策劃能力和議題設置能力;第六,內知國情,外知世界。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前提下,將中國故事打造成世界故事的有機組成部分,在講好世界故事的視野下講好中國故事;第七,構建話語體系是一項長期複雜的系統工程,既要有頂層設計又要在實踐中摸索,需政府、高校、社會、學者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構建話語體系。
問:您如何看待翻譯在對外話語體系構建中的價值?翻譯如何助力對外傳播?
王曉輝:全世界80億人口,中國佔14億多。使用漢語的人口比例雖然很大,但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主要對象仍然是不懂漢語的66億外國人,因此翻譯工作至關重要。翻譯是一個“搭橋”的過程,很難達到“無縫對接”的程度;但對使用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來説,他們之間的交流則可以做到“無縫對接”。
《丘吉爾傳》(Churchill: A Life)一書中有一個典型的“無縫對接”的例子。二戰初期,面對強大的德國戰爭機器,英國獨木難支,首相丘吉爾希望得到美國的幫助。美國總統羅斯福派特使哈裏·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前去倫敦考察。霍普金斯在離開倫敦時,引用了《聖經》中一句話,表明瞭他的態度:“你往哪去,我也往那裏去;你在哪住宿,我也在那裏住宿;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霍普金斯的話打動了丘吉爾,讓這位首相熱淚盈眶,這就是典型的“無縫對接”。
“搭橋”與“無縫對接”之間差異巨大。中國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必須跨越語言、文化、宗教、社會發展階段等等鴻溝。對外翻譯傳播工作者要內知國情,外知世界,鍥而不捨,夯實外語基礎,厚植文化根底,培養家國情懷,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傳播。
今 日 要 聞
MORE關 注 我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