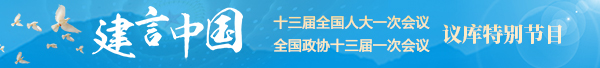艾克拜爾•米吉提:中國作家的驕傲
在許多人眼裏,作家只不過是寫寫文章罷了。其實,不然。于艾克拜爾·米吉提(以下簡稱“艾克拜爾”)來説,他不僅僅是著名作家,還是翻譯家、評論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識淵博。
提起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名字,于文壇盡人皆知。在我所讀的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二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時,由於實施抓鬮確定導師,他便成了我們這屆幾位師兄師姐的導師。關艾克拜爾的故事,非常值得學習。
那年,他從不懂漢語開始
艾克拜爾是哈薩克族,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哈薩克族有著自己的母語,在當地,他們用母語交流,而對於漢語,用他的話説,那就是一個“旱鴨子”。我們不難想像,他當初接觸漢語,是花了多少苦功的。
他的父母都是醫生。父親對哈薩克語、俄語、維吾爾語、柯爾克孜語、烏茲別克語、塔塔爾語等樣樣精通,又是醫科畢業,對拉丁文也有研究。當時,在父親看來,漢語不僅筆畫多而複雜,讀音也奇異,所以,也只能説上幾句罷了。母親則不同了,在她17歲時,作為新疆牧區代表團成員,到內地參觀了一年多時間,期間學會了漢語,還有幸受到毛主席、朱德、劉少奇、周總理等老一輩領袖們的親切接見。
艾克拜爾慢慢長大了,用父親的話説,要帶他學一種大語言,那就是父親認為的俄語。而由於他們不是前蘇聯僑民,而是中國公民,故沒有所謂的蘇僑證,於是,俄語學校就不招收他了。至此,父母帶他到第十五小學,也就是當年伊寧市僅有的幾所漢語學校之一,況且學校就在他們家所住的衛生學校後面。
到漢語學校學習,校方有所規定,首先孩子要懂漢語。當時,他對漢語一竅不通,待父母請求校方對其進行口試時,除了認得墻上挂的毛主席像,哪怕從“一”數到“十”,也是茫然。無奈之下,家長表示回去就教孩子漢語,第二天過來接受考試。最後,終得校方點頭。艾克拜爾對漢語的學習,也正從這一天開始了。那是1961年的9月初。
掌握一門語言,從聽不懂到熟練交流,一般而言,沒有個一年半載,是很難的。所以,最初的三個月裏,他除了用眼神交流,幾乎什麼也聽不懂,就這樣在班裏度過了三個月的“啞巴期”。他置身一種語境之中,之後的日子裏,用心聽,用心記,用心學,最終搞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班級(一年級乙班),更令人欣喜的是,也可以開口與同學們交流了。自此,他認識到,漢語真的是博大精深,而且非常有韻味。
直到有一日,一位班主任去家訪,通知他的父母,説六年級一畢業,就會將艾克拜爾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附中上學,讓家裏人有所準備,勉勵他要好好學習,不要辜負學校和組織的期望,同時,要求暫且保密,不透露出去此消息。
艾克拜爾還記得小學語文課《北京的秋天》,那時,他對北京秋日的藍天、飛翔的鴿群、悅耳的鴿哨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且充滿了無限遐思,再加上從母親的敘述裏,也了解了北京。自此,北京成了他心中的一個夢想。遺憾的是,時代的動蕩,讓他的夢暫時破滅了。
于1969年8月,某日他到十五小學校園去轉時,從八中招生海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之後,便由小學六年級直升初三。在艾克拜爾的記憶裏,隨著珍寶島事件和鐵列克奇事件的發生,為了落實“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學校開始組織挖防空洞,正常的教學秩序再次被打亂。
知青時期,全國要實行下鄉。在他16歲那年,來到了伊寧縣紅星公社綠洲大隊第三生産隊,開始了下鄉生活。幹各種農活,包括種、收小麥,當過木匠,放過羊,學過獸醫、當過翻譯。農活幹了大半年,他被調到“一打三反”落實政策“兵宣隊”作翻譯,也就在此時,恰遇公社書記到大隊檢查春耕生産,由於沒帶翻譯,艾克拜爾被“趕鴨子上架”,臨時做了公社書記的同期聲翻譯,巧的是書記懂維語,只不過是口語表達受限而已,他很欣賞艾克拜爾這個小夥子。不久,就指派艾克拜爾參加縣委宣傳部舉辦的通訊員的學習班,在學習班為期一個月的學習結束後,便被安排為公社黨委通迅幹事。
他從新聞寫作開始,且研究《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疆日報》《伊犁日報》的頭版,琢磨提法和報道特色,由此開始了新聞報道工作。其實,艾克拜爾小時候,受了父母和語文老師的影響,非常喜歡閱讀,幾乎每週都讀一個長篇,儘管之前不太喜歡寫作,自此時起,便與寫作結了緣。也可以説,曾經的閱讀給他的寫作帶來了益處。
1973年4月,包括王蒙先生在內的“三結合”創作組來到艾克拜爾所在的公社,創作連環畫《血淚樹》,由王蒙執筆寫腳本。艾克拜爾負責接待他們併為他們作翻譯。其他人都需要翻譯,王蒙則不需要翻譯。對此,他感到有些意外。經打聽,得知此人是一位作家,聽説還被毛主席點過名,他便覺得此人很了不起。正值青春好年華的艾克拜爾,覺得眼前這個活生生的人是作家,才感到“作家”也是一個普通的人。所以,他自己也就萌生了想當作家夢想。
在“文革”那個年代,圖書館被砸了,同學們手上拿到了不少書,大家也就互相傳著看。就在那個時期,艾克拜爾至少看了不下一百部的長篇。
1973年恢復高考,他參加了高考,有幸被蘭州大學中文系錄取。按照父親的意思,想讓他繼承家業,當一名醫生,並勸説“搞寫作容易犯錯誤”。自從艾克拜爾經歷了許多事之後,也明白很多道理。他説,“醫學院也不一定是為我開的,我選擇它,它也不一定選擇我。若是今年機會錯失,那麼來年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很難説。再説上中文系搞寫作的人,不一定都犯錯誤。”最終他説服了父親。
文學之路從‘中央文學講習所’開始
畢業後,艾克拜爾到了伊梨哈薩克自治州黨委宣傳部工作。期間,下鄉、調研、參加“普及大寨縣工作團”的工作,幾乎走了二十多個縣,一路走下來,不僅視野開闊了,也有了生活。由於粉碎“四人幫”,各種作品開始重新出版。艾克拜爾也開始買書閱讀,1978年,他創作了處女作短篇小説《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刊發于《新疆文藝》雜誌1979年第三期,且榮獲了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980年3月初,他得到赴北京領獎的通知,途經烏魯木齊時他去《新疆文藝》編輯部拜訪,在這裡獲知他已被第五期“中央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前身)錄取。“確切的説,我當時覺得一片茫然。我不知道‘文學講習所’是幹什麼的,更不知道它的歷史。”他顯得很疑惑。他説:“我不知道我被錄取,還沒跟單位請假呢。”編輯部領導説,“你是新疆唯一一個被錄取的人,機會難得,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也是我們新疆文藝界的光榮,我們會請有關部門向你單位打招乎的,你放心去吧,要珍惜這個機會。”
“文革”後第一期,也就是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艾克拜爾與蔣子龍、王安憶、張抗抗等,共同來到了這裡,開始了他們四個月的學習與交流。期間,講習所聘請的導師之中,只因先前與王蒙先生認識,打心眼裏認可他,而且對新疆生活王蒙先生很熟悉,交流起來很方便,故選了王蒙先生為導師,也算是緣分。
講習所學習結束之後,中國作協有關領導就想把他留在北京,説是要創辦《民族文學》,但是,他一心只想回到新疆伊犁州搞他的創作。最初,他是想走柳青式的道路,深入到基層,哪怕寫好一個鄉、一個村,但他發現,現實並非如此。
艾克拜爾發現,縱觀文學史,很多國家的作家成名後,都會到該國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去。比如,英國作家到倫敦,法國作家到巴黎,俄羅斯的作家,也到莫斯科。1981年,艾克拜爾來到了北京,擔任《民族文學》的編輯,一直就留在了中國作協。接下來,1985年中國作協創聯部設立民旅文學處,艾克拜爾任首任副處長、處長一職,一幹就是十年;後來在《民族文學》擔任了八年的副主編、常務副主編,接著又到了中國作家出版集團擔任黨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與大家攜手組織起了相關機構工作,其間,兼任過《作家文摘·典藏》主編,2008年又兼任《中國作家》主編。
艾克拜爾是一個比較正統、嚴肅的作家,他從不瞎寫,也不濫寫,對於學術研究,更是嚴謹。從1989年到2009年二十年間,艾克拜爾中斷了小説創作,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文學翻譯,著述頗豐,撰有《穆罕默德》、《木華黎》、《關於〈蒙古秘史〉的成書、傳播、以及哈薩克譯文版對照》、《關於木華黎歸附鐵木真年代考》、《匈奴歷史人物傳記及族群遷徙流變考》、《關於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問題》等。譯有《阿拜箴言錄》、《論維吾爾木卡姆》等譯著。
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時所引用的阿拜名言,“世界有如海洋,時代有如勁風,前浪如兄長,後浪是兄弟,風擁後浪推前浪,亙古及今皆如此。”正是出自艾克拜爾譯著《阿拜箴言錄》。另外,在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縣慶50週年之際,由艾克拜爾作詞,與著名作曲家徐沛東先生譜曲,合作了一首縣歌《阿克塞》。
迄今為止,艾克拜爾出版包括小説、傳記、學術研究、紀實文學、譯著,已達二十八本之多。
他説,“這些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事需要重新認識,若匆匆忙忙的寫,我也不願意。我當了多年主編,一年要出一千五百八十萬字的作品,為此還要閱讀幾千萬字的作品。”
然而,自從艾克拜爾當了《中國作家》主編之後,他説,“我發現,大量的作品……”
此時,我隨著他的話,扯了回來,反問,“是要去讀嗎?”
艾克拜爾遲疑了一下,説,“大量的作品……”
我又問,“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嗎?”
這一問,艾克拜爾笑了起來,他的回答,令我也覺得十分有意思。説,“我幹嗎要荒廢呢?”
他説,“小説嘛,像水銀一樣,是游離的,富有張力的,若像鋼珠一樣能拿到手,就不叫小説了。”從此,他又拿起了筆,開始了小説創作。
他的小説,涉及少數民族、大都市、小人物等。他認為,“最新的東西不一定最好,速生的東西也容易速朽。經過時間考驗,存留下來的東西才是好的。比方速食,給大家帶來的是營養缺乏。還有,網路文學和有些暢銷書,速生速滅。現在,每年出版三千多部長篇小説,一個讀者哪能讀得過來啊?”有的作品品質不一定很高。所以,他借用了高爾基的一句話,“製造語言的垃圾。”
對於語言的垃圾,他還用了個比喻,好如某些物件的豪華包裝,拆開一看,裏面的東西就那一點。那麼包裝呢,自然是被扔掉的“垃圾”。
自從艾克拜爾接手《中國作家》,便提出了一個理念,“用最優美的中文,寫最美好的中國人形象,為全世界熱愛中文的讀者服務。”艾克拜爾有著自己的價值尺度,他尊重每個作者,對於刊發的作品,首先要充滿正能量,積極向上。儘管當主編,但從沒有過排他性,也不是説喜歡誰就發誰的作品。2010年,他把半月刊《中國作家》改成了旬刊,為《中國作家·文學》、《中國作家·紀實》、《中國作家·影視》。
2012年開始,《中國作家》開始轉企,進行企業化經營和運作,自負盈虧。《中國作家》打造出了真正的文學期刊品牌。令人疑慮的是,純文學也需要經營嗎?
艾克拜爾説,文學是這樣的:當作家寫作時,它是個人藝術創作;一旦發表後,它就是社會的財富。作為期刊、圖書一旦進入市場流通領域,它就是商品。所以,文學有其商品屬性。任何一本文學書籍和刊物,都有幾重價值。當你閱讀時,它是精神食糧;從書店用人民幣購回時,它就是商品;送給別人時,它就是禮品。
據了解,2014年月10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關於《時代精神 創新意識——也談“〈中國作家〉現象”》一文,並指出《中國作家》于國際國內打造了中國作家的形象。同時,也是文壇和黨報對艾克拜爾所做貢獻的認可和稱讚。並認為,《中國作家》不僅以引領中國的純文學潮流,也引領了中國影視文學的潮流。
當然,艾克拜爾時刻關注著現實生活,期間,他跟幾個城市合作,推出一批文學獎項,比如“《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中國作家》劍門關文學獎”、“《中國作家》郭沫若詩歌獎”,“《中國作家》‘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中國作家》‘舟山群島新區杯’短篇小説獎”等。在這些獲獎項作品中,有一批作品有幸獲得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艾克拜爾一直勤於寫作,認為作家的黃金期是很短的,有的在青年、有的在中年、有的則在老年階段。那麼,對於艾克拜爾而言,他的創作高峰或許才剛剛開始。
自從他卸任《中國作家》主編之後,覺得自己輕鬆了許多,不再承擔幾十位員工的工資、以及退休人員的工資的壓力。對於他自己呢,也就有了更多的創作空間。他説,創作是安靜的,快樂的,是精神享受,而非孤獨。哪怕于他坐在飛機上,也是要打開電腦寫點東西。
“文學永遠是人學”
近幾年,關於60後、70後、80後的説法,越來越受到文學界評論家們的關注。當然,作家的同質化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對於代際關係的現象,許多時候會令人迷茫。
艾克拜爾認為,那只是年代劃分的方法,並非寫作劃分的方法。有時,甚至是一些慵懶的評論家省力的表述方法而已。文學若按這種規律劃分,豈不是太簡單了?當然,文學應該按流派、按風格區別劃分。
在他看來,現在一説到按年齡段劃分,就拿50後來説,噢,意識裏會認為這些人老去了。這一代人,曾上過山,下過鄉,插過隊,甚至當過紅衛兵、寫過大字報,屬於奮鬥型,吃苦耐勞型。而60後,眼下正是挑大梁的一代。那麼70後,開始是奮起的一代,自家裏上有老、下有小之後,也開始變得沉默了。80後呢,大多都是獨生子女。應該説,真正任性的是90後。然而,00後也在成長。如果從社會學角度去看,能講得過去,若從文學的角度去説,似乎講不過去。
是作品中關注的角度不一樣?他表示,應該是這樣。其創作經歷、創作風格方面,也各不相同。關於“魯、郭、茅,巴、老、曹”的現象,我讀魯院時,也是提得最多的。或許,每個時期的文學作品,都有它所存在的價值。
再比如,想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樣的,要讀浩然的《艷陽天》。 雖然人民公社撤銷了,但那畢竟是中國的一段歷史。1958年,三面紅旗之一就是人民公社,若説了不利於人民公社的話,那就會打成為右派或現行反革命。1982年,國家取消了“人民公社”,改為“鄉”。幾十年過去了,人民公社到底是什麼呢?想要搞明白,就要讀當時的文學作品。這時,文學作品就起了一定的作有,自身也有了文化學價值、社會學價值、歷史學價值。
談到知青文學,艾克拜爾認為,知青文學有它本身的價值所在,但是有一點,某些時候,它只知道去訴苦、訴冤。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農民依然面朝黃土背朝天生活在農村,知青文學在傾訴時,似乎忽略了同樣作為人的這些農民大眾的存在。
他説,關於尋根文學,實際上是美國黑人在尋找他們的《根》。我們的尋根文學是把根尋到農村。比如現在城裏的北京人,三代之前,多數人的祖上差不多都是農民。而今,2億農民工的根在哪兒呢?還不是在原地?我國跨入新世紀之後,那些西方的文藝理論和中國的現實之間,畢竟是有些差距的,不能照搬。
目前,關於網路文學的大肆興起,捧紅了一些人。比如腦癱詩人余秀華。我們先撇開余秀華詩的內容不説,其標題《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明顯具有爆炸性。然而,她的詩句的確很有個性和張力,有些詩寫得確實很好。他説。
艾克拜爾認為,現在是眼球經濟、注意力經濟時代,那些文商們,那些傳媒、網路、經紀人,花樣翻新想吸引消費者的眼球以獲得利潤最大化。它表明藝術的多重身份。藝術就是一個多棱鏡。作品寫出來,要放到社會上去,當讀者心一熱,就買下了,經銷商們需要的是這個。比如手機網路,你這邊點的是拇指,那邊硬幣就流到經營者的腰包了。
我們要鞏固高原,再造高峰。所以,傳統文化是決不能顛覆的,要繼承,要發揚。正如艾克拜爾説,“文學永遠是人學,寫活生生的人,寫人的情感,寫人的精神狀態,寫人的內心,寫出正能量。若把今天的‘人’寫好了,就是對這個時代的貢獻。”(作者簡介:郭香玉,山東菏澤人。魯迅文學院第二十二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當代著名紅學家林冠夫之關門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