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佈時間: 2017-05-12 | | 責任編輯: 馬雅蘭 | 來源: 劉海粟美術館
上海在中國現代攝影的發展進程中,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上海是攝影最早在中國上岸的地點之一。隨著攝影向現實生活中各方面的滲透,人們對其所具有的娛樂性與文化消遣功能也給予了同樣的關注。攝影成為了城市中産階級展開交際的媒介,而活躍于都市的民間攝影社團也鼓勵了攝影的這一社交功能的展開。中國第一個業餘攝影團體,精武體育會攝學部就是于1913年在上海成立。
等到現代印刷技術能夠將照片妥貼地、精確地轉印到紙張上去並且大批量印刷後傳播出去時,攝影更是如虎添翼。借助平面紙媒的傳播,攝影圖像成為了公眾視覺消費的重要對象。經過攝影這一民主性媒介所生産出來的攝影圖像,在傳播了資訊的同時,也時時啟示、激勵其觀看與消費者,“你們也具有創造我的可能!”在這樣的暗示與召喚下,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攝影愛好者與工作者一樣,在中國也有許多人愛上攝影並且積極探索攝影的各種可能性。上海,則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攝影圖像生産與消費場所。
在上世紀前期,促成攝影大發展的所有條件都具備了。堆積于照相器材行的等待被感光、被印相與放大的感光材料,作為中産社交圈與獎勵機制的攝影社團以及由此産生的的眾多展覽活動,充塞報攤的各種供消遣與發表照片的平面紙媒。媒介暗示與鼓勵之下悄然形成的影像消費習慣,如看畫報、上照相館拍照、購買攝影畫冊或照片,去電影院看電影等活動。更奢侈一些的,包括了尋找、加入到建立自我身份認同的攝影俱樂部這樣的社團交際活動中去。而更具精神性的探索是,本來根深蒂固卻又面臨停滯的藝術圖像的生産傳統,也在等待的新語匯與看法的再切入與激活。當然,最重要的是,對攝影感興趣的人群的形成以及逐步涌現的攝影人才。在上海這樣一個不畏新、追求新的城市,新就是為新人的出現所準備的一個時代所提供的機會與藉口。
於是,當我們今天回頭看,儘管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仍然會有這麼多當時的攝影愛好者與工作者,已經為我們存留了可供我們凝視與檢視的不少優秀作品。儘管戰爭、革命與社會動蕩,毀滅了大量的作品,但我們仍然發現,有許多攝影者的作品,在等待我們給予新的敘述與評價。
《來自上海:攝影現代性檢證》這個展覽,就是一種在歷史與時代的雙重催逼之下的産物。我們在今天探究身份認同時,我們曾經的活動與實踐,會提供切實的證據幫助我們建立、加固或破壞、否定自己有關自己的看法與認識。上海,在經歷了滄桑之後,早就面臨了自己為何的召喚。攝影,在為上海形塑了歷史形象的同時,也為上海的視覺文化傳統提供了新的材料與案例。
題目中,“來自上海”四字,主要意味是這些攝影家們的于上海出發的攝影人生。當然這當中有些人可能是中途來到上海,而有些人則是上海土著,但重要的是,他們的攝影實踐受上海的精神與物質文化的環境的鼓勵並且起步于上海。
而我們所選擇的攝影家,主要標準是看他作為一個攝影者的專業工作的持續性,以及由足夠的量所保證的質。與任何藝術一樣,攝影也是一個必須由充分的熟悉與熟練而進入到更高境地的視覺樣式。
這些攝影家的活躍時期為上世紀20到40年代。這個時期是中國現代攝影逐步形成自家面目的時期。這是攝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攝影的各種可能性經過實驗與實踐而獲得確認的時期。因此,能夠聚焦這個時期的攝影現代性探索,或許能夠更清晰地掌握到一些攝影現代性探索與追尋的線索與內在邏輯。
沙飛(1912-1950)滯留上海的歲月並不長久,但上海是他萌生以攝影為志業的重要地點。雖然從上海美專不辭而別,但與魯迅的邂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本展所展示的沙飛的作品,均是在他成為一個革命宣傳家之前拍攝創作的照片。這些照片都體現了一個青年對於社會正義的呼籲與對底層民眾的同情心。這些照片在反映其正直的品性的同時,也展示其不凡的藝術身手。沙飛的這些早期影像用光硬朗,畫面飽滿,資訊明確,這為後來其獻身宣傳攝影奠定了觀念與手法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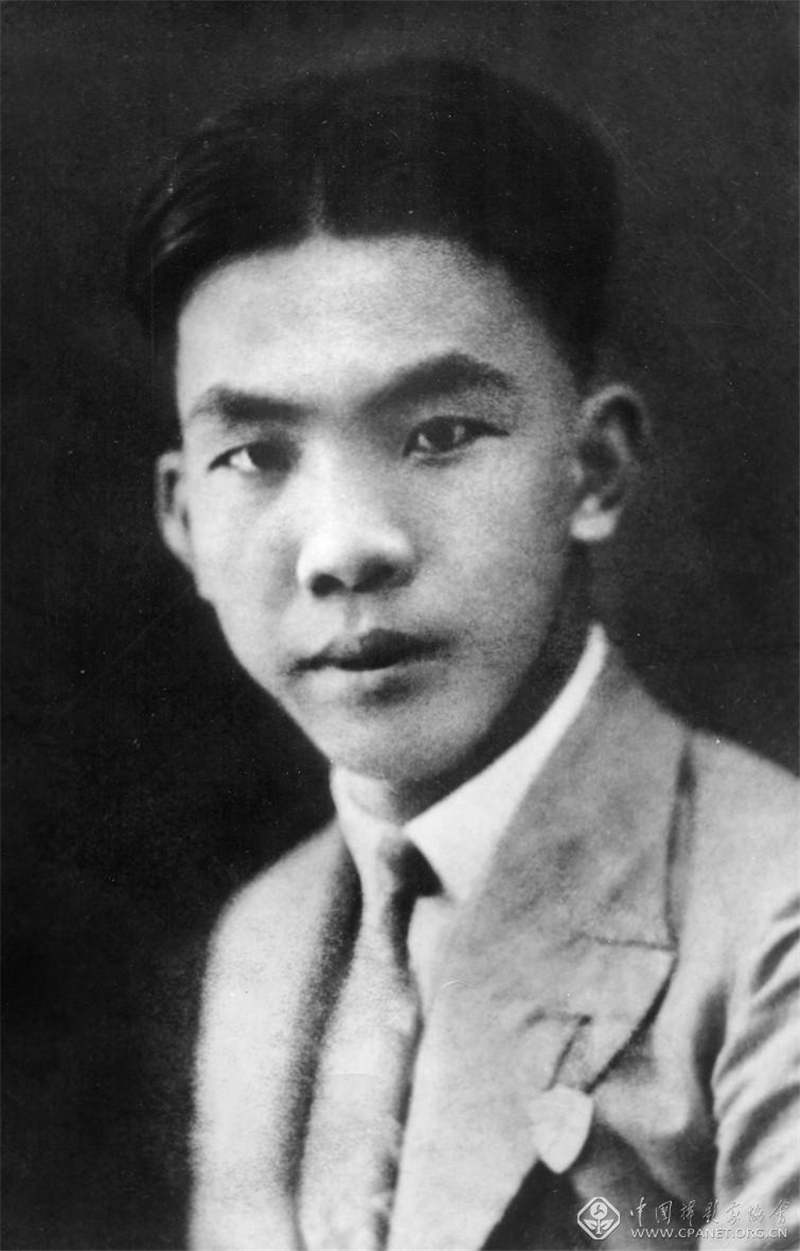
沙飛 (1912 - 1950)

沙飛,魯迅與青年木刻家,左起:黃新波、曹白、白危、陳煙橋,1936年10月8日
吳印鹹(1900-1994)在走向革命之前,在上海求學與工作。他先在上海美專研習繪畫,也在上海的照相館從事過商業攝影,後又與當時的新興視覺藝術樣式的攝影與電影結緣,拍攝了電影史上的經典名作。作為一個攝影愛好者,他在當時的攝影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深受當時流行的“美術攝影”風格的影響的作品,為時人矚目。這次展出的作品,無論是富社會性的創作還是主要以電影明星為拍攝對象的肖像攝影,其創作都富於藝術性,充分展現了其藝術家的氣質與感性。

吳印鹹(1900-1994)

吳印鹹,力,1930年
沙飛和吳印鹹的早期攝影中的社會意識代表了當時左翼思潮對於攝影的深刻影響,而本展覽中的另外一些攝影家們的創作,如駱伯年(1911-2002)與金石聲(1910-2000)等人的實踐,則顯示了他們努力將攝影提升為藝術的強烈願望。
駱伯年作為一個銀行高級職員,終其一生是以攝影為愛好。在他于1935年來到上海後,受當時的氛圍所激勵,對於自己的攝影愛好就更加投入了。或許正是一個純粹的票友,因此其觀看可以從容悠閒而不受比賽晉級或為生活掙稿費之迫,因而更有自己的一份篤定。一般認為銀行家的這種身份相對會在各方面趨於保守,但駱伯年的探索表明,這樣的身份並不影響他展開大膽的甚至是激進的攝影語言探索。

駱伯年(1911-2002)

駱伯年,構圖,1933年
金石聲當時在上海就讀于同濟大學。其身份雖是大學生,但他與其他兩人創辦的攝影雜誌《飛鷹》,被公認為是一份體現了當時中國攝影的標準與水準的重要攝影媒介。這是他于攝影史的最重要貢獻。《飛鷹》提供了一個寬容的平臺,基本上包攬了當時所有活躍于攝影界的攝影家。而他自身的創作,則體現了在傳統畫意攝影與現代主義攝影之間尋找平衡點與突破口的努力。而其實,他的這份努力,不正是本展覽中所有其他攝影家們都在努力嘗試的嗎?

金石聲 (1910 - 2000)

金石聲,百老彙大廈(現為上海大廈),1935年
我們很榮幸得到金石聲先生後人金華的幫助,為本展覽複製其父親編輯的《飛鷹》所有各期封面,以及發表在《飛鷹》上的各類攝影作品。我們企圖以這些畫面為展覽提供一個更大的背景,以便觀眾可以更深切地了解到當時上海的攝影氛圍以及愛好者們的攝影探索的真切面目。
在所有這些從上海開始其攝影人生的攝影家中,只有莊學本(1909-1984)是真正的上海土著。但是,與本展覽中的其他攝影家不同,莊學本樹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攝影家形象。他掌握了攝影的觀念與手法後,沒有在繁華的上海過多逗留或者説被其都會性所吸引,而是赴邊地八年,風餐露宿,為的是以民族志方式對於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結構等有個深入的攝影觀照。風花雪月在他的照片裏絕跡,十足的志“異”顯示了這個上海人對於非都市性的強烈興趣。而且,他或許是當時唯一一個從邊地這個都會的對極為都會現代性提供了最鮮明的視覺參照、也為理解攝影現代性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的攝影家。而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性質與內涵,他更以自己的民族志攝影將其具體化、可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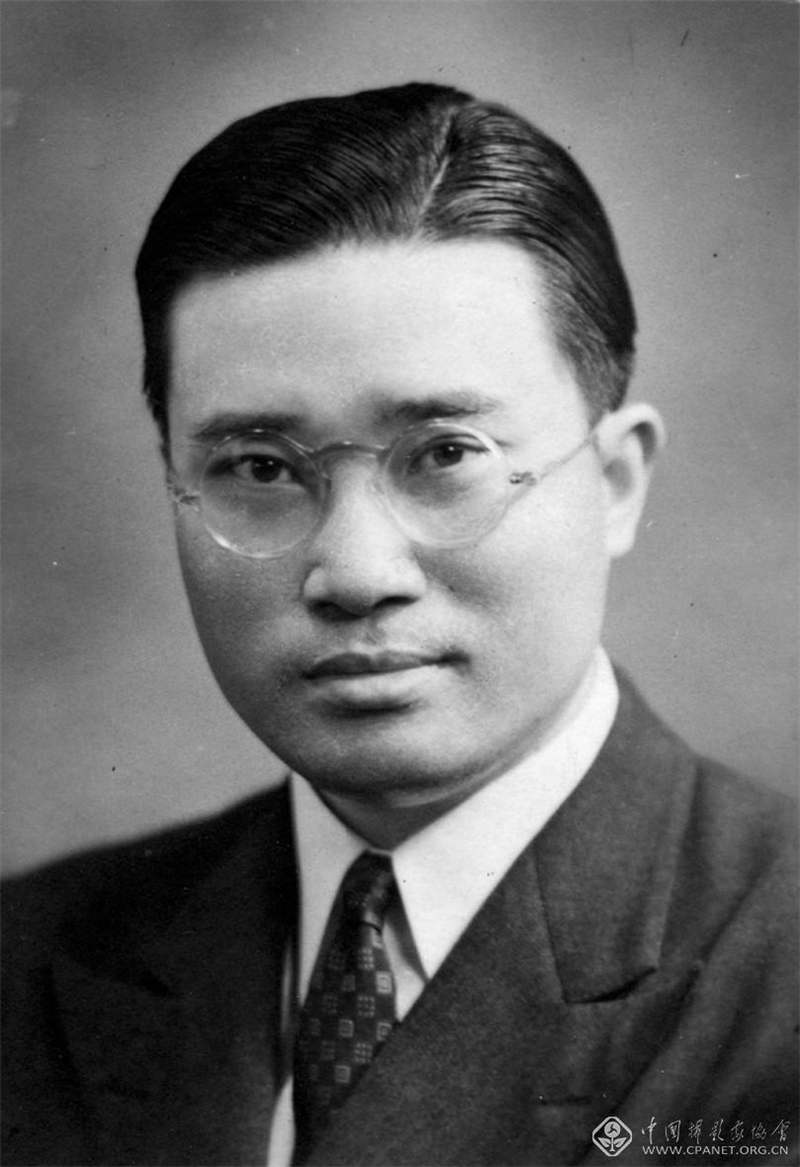
莊學本(1909-1984)

莊學本,嘉絨少女,四川理縣,1938年
在檢視了職業攝影家或者説是高級業餘愛好者(具創作志向)的工作後,我們很高興能夠再提供兩個案例供討論探尋攝影現代性之用。陶冷月(1895-1985)與夏盈德(1907-不詳)兩人,都並非以攝影為志向或最終以此為職業,但他們由於經濟收入較高或生活較為優裕,因此得以從不同的動機出發與攝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並且以存世照片的足夠的數量,向我們展示了他們對於攝影的熱衷與把握,同時也豐富了攝影現代性的內容,也拓展了我們對於攝影現代性的理解。
陶冷月是當時享譽中外的中國畫家。因為為繪畫取材的原因,他置備了高檔照相器材,在出遊時經常攜帶照相機並大量拍攝素材照片。由於繪畫原理與攝影的相通之處,從他保留下來的照片看,他的攝影水準很高,也充分把握到與繪畫仍有根本區別的攝影的特質。他的攝影作品因此也顯得成熟,既有繪畫的意趣也有攝影的品格。他的這些照片,既為山水風景以及都會景觀保存了當初面目,也展示了其對於攝影這一媒介的理解與把握,殊為難得。

陶冷月(1895-1985)

陶冷月,南川金佛山古佛洞, 1932年
在劉海粟美術館的資料中,我們欣喜地發現並最終確認是由夏盈德精心手制的多本照相冊。他是畫家劉海粟的夫人夏伊喬女士的哥哥。除此之外,我們對他的個人生平經歷所知甚少。雖然為此做了一些努力,但我們仍然對其包括如何愛好攝影的人生經歷一無所知。但夏盈德的這些照片,充分説明瞭一個中産一員或者是正要成為中産一員的年輕都會人夏盈德對於攝影的熱情與熱衷。而這些照片正好為上述許多以藝術創作為己任的攝影者們的“群眾基礎”提供了一個充分的證明與説明。我們從他拍攝的這麼多的照片可以發現的是,當時生活優裕的城市中産階級與攝影與影像消費的可稱水乳交融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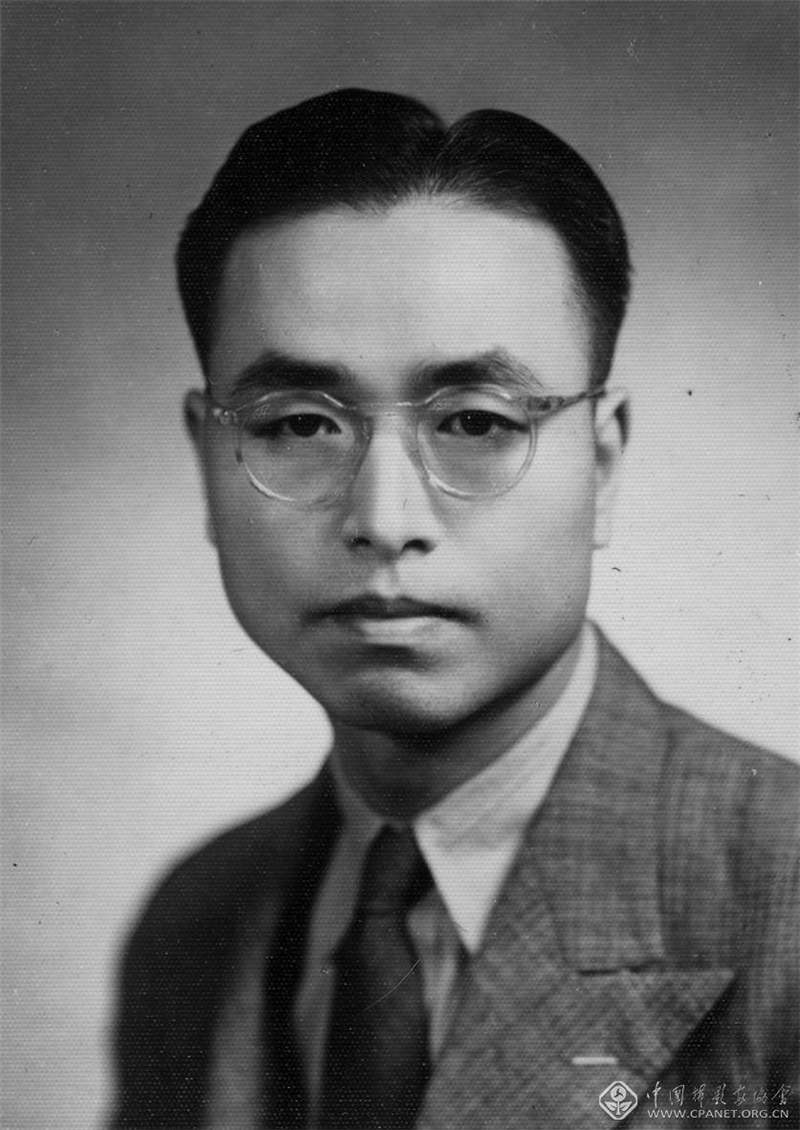
夏盈德(1907-不詳)

夏盈德,無題
需要指出的是,這七位同時代的攝影家,雖然在上海有著時間空間上的各種可能的交集,但總的來説,他們缺乏相互間的聯繫。可以説,他們各自的探索都是處於一種都會整體氛圍下的、但相對來説屬於個體的孤獨的但卻是目標明確而堅定的探索。他們的創作,在題材上、在語言上、在思想上,有著某種相互呼應,相互聲援,因此具有一種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品格在。這可能要歸功於上海整體的物質與文化的氛圍、尤其是大量的平面媒體所提供的資訊以及攝影社團的存在,使得他們的探索有可能無形中形成了相互間的促進與鼓勵,並且最終在整體上推動了中國現代攝影的發展。
由於一些具體的原因,在當時上海的攝影現場曾經發揮過重要影響的攝影家,如郎靜山、丁悚、潘思同、胡伯翔,以及在上海錘鍊了攝影身手的攝影家,如張才等人的作品沒有機會在此次展覽中展出。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在此對他們之於攝影現代性的貢獻表達高度的敬意。
行文至此,或許到了討論一下什麼是攝影現代性的時候了。現代性的審美實踐,既是意義的生産,也是語言的實驗,兩者一起構成了現代性的內在與外表。攝影現代性,又因為其媒介特性所帶來的觀看的特長與片斷性的限制,而具有了驗證現代性的特殊方式與邏輯。
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重要著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將攝影以及電影視為破除盤旋于藝術品上方的“靈氛”(Aura)的手段。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攝影既將包裹在藝術品原作上的“靈氛”驅除殆盡,但在追求其本身的現代性進程中,在促進了藝術民主化的同時,又因為種種原因而步入了自我神聖化、自我神秘化的過程中,想要成為一種與繪畫等並駕齊驅的“高藝術”。而美術館與博物館在此進程中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加劇了攝影自身的神聖化與神秘化、以至經典化的進程。時過境遷,懸挂在博物館與美術館墻壁上的攝影作品,與繪畫作品相類,同樣開始散發一種異樣的“靈氛”。這個吊詭,發生於攝影,發生於攝影追尋現代性的過程中,這也是我們這個展覽想要呈現並引發關注的,這同時又成為我們檢視攝影現代性為何的動機。
作為一個在民國時期國際化程度最高、産業與商業最發達、對外來文化敏感度最高、都市文化最繁盛與都會意識最強的現代口岸城市,上海必然會承擔起輸入、吸納、消化外來文化並嘗試轉化為本土文化與物質消費的責任。
攝影,作為體現了充足的現代性的視覺手段之一,它非但在歷史記錄方面一直大顯身手,而且也逐漸成為了一種從其他視覺藝術樣式挪用、吸收並改篡觀念、靈感與手法的新興藝術樣式。攝影的現代主義實踐,最終使其獲得了可以説是最充分地説明瞭20世紀視覺感知如何演進與開花結果的最主要的觀看手段之一的資格。
同時,攝影也從多個方面深入到了都會市民的生活中,溶化于他們的日常之中,塑造現代生活,培養現代感性。攝影,從它與現代生活發生方方面面的接觸始,在其本身體現了、傳播了現代性的同時,也成為了檢測都會現代性的指標之一。
與同時期國外的攝影探索相比較,這些從上海開始他們的工作的攝影家們的實踐其實絕無遜色。這也可能與他們的攝影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與上海處於世界主義大都會前列有關。由豐沛的人流、充足的物資與橫溢的資訊所佔據覆蓋的都會上海,攝影的用武之地得以確保。沒有充分的、發達的在物資器材、資訊以及人才等方面的保證,尤其是像攝影這樣的需要技術手段與物質水準來保證的現代觀看媒介手段,其現代性的探索與獲得恐怕無法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説,攝影現代性與都會性的關係無法分離開來考慮。都會現代性保障了攝影現代性探尋的充分可能,而攝影現代性的獲得則進一步具體化都會現代性。
從這些活躍于20世紀早期的中國攝影家們的作品,我們相信,攝影現代性在中國的獲得有充足的證據可以提示。什麼是現代性,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一種現代品質的育成與成熟,也是一種對於通過媒介的探索而得到的自我發現的可能,以及由此而來的自我質疑並修正的不斷過程。他們的作品以及通過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現代志趣、探索意識以及認同標準,都是在充分把握到了攝影的特性並進而探索其本質的具體結果。
在討論種種現代性的過程中,出現了中華現代性的説法。但是本展覽並不想為這個説法張目。輕易地把中國人與某種現代媒介、尤其是觀視媒介之間的關係作為論證某種“我也有的”或者是“我已經有了”的説法,或許無助於對於現代性的切實把握,也不是我所感興趣的。作為展覽策劃者,我更感興趣的是通過攝影這個為地球各個角落的人們所共用的媒介被探索與實現了的攝影現代性的駁雜光譜中的中國攝影家所提供的別具特色的內容。我們相信,通過這些攝影家們的作品,人們能夠從這個展覽發現並確認,攝影現代性在生活在上海的中國攝影家手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而這正是這個展覽所想要呈現給廣大觀眾的。
(《來自上海:攝影現代性檢證》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