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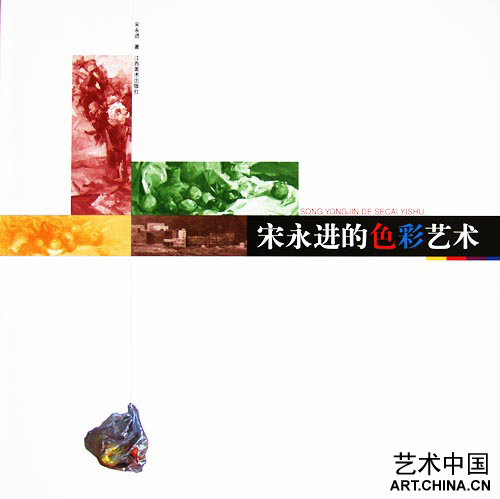 《宋永進的色彩藝術》封面
《宋永進的色彩藝術》封面
《宋永進的色彩藝術》序文
宋永進
當代畫家對色彩語言的橫向拓展已進行了許多有益的探索,色彩語言的陳述範式前所未有地豐富,這種探索的勇氣和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色彩文化高度和深度的拓展上,畫家們所作的努力卻仍然不夠。
精神的傳達需要借助語言的形式。“繪畫中的色彩”是傳達藝術精神的重要形式之一,但它有別於“日常語言中的顏色”,它是視覺藝術的一種形式語言。色彩指的是畫面中顏色與顏色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僅反映出畫家對藝術規律(主要指顏色之間的對比與協調和補色的關係)的認識和駕馭情況,還傳遞著畫家的智慧、氣質、修養及生活閱歷等精神層面的資訊。色彩不僅具有物質屬性,還承載著精神因素,具有文化性。因而,對色彩的審美,就不僅僅是對美的顏色的發現和創造,更是畫家的心與對象的色之間的碰撞與融合。觀者品味色彩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目賞”的層面,而應該“心悟”色彩的涵養及其背後所隱含著的畫家的思維狀態、藝術修養和精神境界。
然而,當代畫家藝術心態的浮燥和藝術行為的急功近利,把色彩自身的巨大魅力導向了物質化的發展方向,色彩語言中的精神因素在不斷地削弱或消失。
一方面,從“剃頭”、“理髮”到“美容”、“美發”,再到改頭換面的“藝術造型”,當代生活日趨藝術化;另一方面,許多畫家對色彩文化性的認識卻呈現了一些倒退的趨勢,從追求高雅的“色彩”品位到熱衷於營造漂亮的“彩色”效果,乃至尋求高純度的“顏色”刺激。畫面上顏色的種類和花樣愈來愈多,色彩的純度愈來愈高。其實,顏色的種類越多,並不等於色彩越豐富;而顏色的純度越高,也不等於色彩的品位越高。眾所週知,“顏色”是物質的一種自然屬性,“彩色”也一樣,不過是多種顏色聚集在一起的一個統稱,是僅僅相對於黑白而言的。兩者都不是文化範疇的概念。顏色原本並無優劣等級之分,但在某個特定的時期或區域內,由於人們共同的某些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響,造成了大多數人對一些顏色産生偏愛或忌諱,久而久之形成了群體的欣賞習慣,美的顏色和醜的顏色也就産生了。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各種習慣在改變,美的標準發生了變化,美的對象也就發生了轉移。因此,人類對物質自然屬性的喜好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時裝流行色就是典型的例子。色彩則是永恒的。這種永恒性就來之於色彩的文化精神。而一旦失去了文化精神,“色彩”就要褪色了,畫面上留下的只是那些漂亮的“顏色”。眼睛觀賞漂亮的顏色,就如同挑選華麗的服飾或者享用美味的佳肴一樣,是人的物質享受,而非精神享受。當前的繪畫界,也存在著多種樣板的流行色現象——甜蜜抒情的、苦澀深奧的、西部特色的、歐美洋味的、追求刺激的……種種色彩套路,既缺乏文化的深度,也不是藝術家精神的自然流露,而是為討得某些人歡心而精心設計的物質誘惑。面對這些形形色色的畫面,看似五彩斑斕,熱熱鬧鬧,其實空洞無物,只能令人眼花繚亂、心情煩躁。正如老子所言:“五音使人耳聾,五色使人目眩”。相反,古今中外許多大師的作品,其色彩或許並無甜蜜誘人之處,也無驚世駭俗之舉,卻吐露了藝術家的心聲和美的氣息。在莫蘭迪的作品中,僅僅是幾組簡單的顏色聚在一起,灰白、草綠和赭石,或者是淡黃、暖白、灰綠和灰紫,在相互交融中相輔相成,相互襯托,其中每一組顏色之間的層次都極其微妙而豐富,並蘊涵著次序和節奏,因而構成了和諧而神秘的美的意境。從寧靜而幽雅的畫面中,人們看不到絲毫物質的誘惑,卻接受了一次崇高的精神洗禮。
倘若色彩的精神因素消失了,那麼顏色本身無論如何漂亮、高貴或者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色彩語言也同樣會顯得十分貧乏和毫無意義。色彩語言的文化高度和深度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就能達到的。這就更需要藝術家對色彩文化的執著和潛心地研究,而不應該急於求成和投機取巧。常言道“欲速則不達”。一些農場主所謂的“科學”養雞就是一個例子。當家養的土雞滿足不了市場的需求時,如果用幾個早熟的洋雞品種充數,甚至利用激素催長,那麼雞的數量和重量很快就“過量”了,人們的溫飽問題也可以解決了,可是雞的品質呢?當下流行的那些色彩樣板不正是早熟的洋雞品種麼?這樣的藝術充其量也就是“溫飽型藝術”。正當物質生活不斷地加快了小康的步伐時,我們也期待著藝術能早日從“溫飽型”中走出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