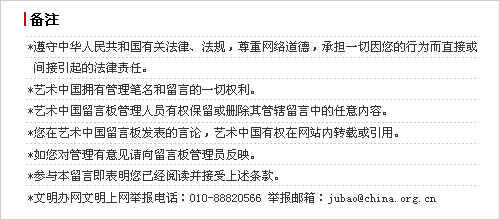“做俗比做雅更危險,難度高,挑戰性也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沒有創造力?自己有沒有激情?有沒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不用急著當下一定要説什麼,或者擔憂是否被理解。”
蔡國強常説影響他創作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奶奶,一個是毛澤東。現在説毛澤東。
蔡國強在紐約古根漢美術館舉辦的回顧展,創下古根漢美術家個展歷來參觀人數最多的紀錄。這位不説英文,無法當面跟外國人溝通的中國藝術家,卻讓如此多的群眾著迷。
蔡國強作品中明顯的儀式意味以及如同西方評論説的“對群眾的掌握”,主要根自蔡國強從小受到毛澤東思想訓練裏頭談的“民眾參與”。從小浸淫在這樣的思考養成之中,蔡國強的藝術也特別在意參與,而毛澤東理論教會他思考“如何讓群眾參與藝術的方法論”。
“學校中受的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一直到現在都還深深影響我。現在還在用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做作品。”譬如説“不破不立”、“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等,都是極為有幫助的理論。
如何讓民眾參與呢?
“首先,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我必須做我自己想看到的東西,觀眾才可能會想看。”
“我的作品往往是帶有童心,有種浪漫氣息的,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是擁有童心,就是渴望追求童心,要不然就是懷念童心的。這點會使得大眾比較容易接受我的作品。”他説。有童心的人看了會感到好玩,沒有童心的人看的會想起自己曾經也有過的童心。
他大膽地用“雅俗共賞”這四個“危險”的字來形容自己的特質。
“基本上, 雅 俗 共賞在現代藝術中並不被當作好事,好的現代藝術通常都被視為追求 雅 的層次,因為喜歡講的是精英,談的是小眾。”
但是蔡國強的社會主義背景,讓他特別在意藝術的責任,相信藝術與社會應該是有關係的。
蔡國強談到他在上海APEC製作閉幕焰火的經驗,由於要跟官方密切打交道,他想這樣做也不行,想那樣做也不行,因為他的政治人文主張與官方思考的有所不同,就藝術創造面的溝通也難以達成。他一度沮喪到不知道該用什麼法子了。
但是他最終想到,他用的公家機關預算其實來自人民的稅金,並不容易;畢竟人民不是生下來就應該要給他錢的。在這樣的念頭下,他最後還是設計出來一場令人歡欣鼓舞的燦爛焰火盛會。
但是,“俗”要怎麼做呢?要不要有底線呢?如果“俗”沒有策略,沒有掌控,很可能連一點點“雅”都留不住了。
“對一位有自信的藝術家來説,我覺得做 俗 比做 雅 更危險,難度高,挑戰性也高。”他説,“也因此我每一次做 俗 都悄悄抱著高一些的期待,因為其中的冒險性高,讓我更興奮。”
“我的性格中有一種 明知故犯 ,像是做這種盛典活動,或是大量運用東方的東西,不管是選材或是藝術呈現,都有一種危險的傾向,會讓人家感到很危險。”
將蔡國強對於“俗”這項挑戰推展到最極致危險的,莫過於他接下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的視覺總監與焰火演出了。
“做奧運,首先要面臨到的是一位藝術家竟然成為政府的御用工具,但更危險的是,你很容易在京奧搞了兩年,最終卻做不出任何一點點具備藝術價值的成果。”他嘲諷了起來:“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 當代藝術的特點就是什麼都可以幹,幹什麼大家都不覺得危險了,但是做奧運是危險的。”
大家包括自己都覺得危險,蔡國強就覺得有意思了。
“我想做,並且想要撐久一點,不能做到一半撒手不幹。”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俗”與“雅”又要怎麼分呢?
蔡國強以他做京奧的二十九個大腳印為例。“雅”版本的説法是,北京這座古老城市,一串大腳印沿著中軸線走過,這是看不見的世界的力量延伸,這也是“與外星人對話”的行為。“但是你用這種説法,那幾千個警察與消防隊員為什麼要來幫忙?”
明明是同樣一件事情,“俗”的説法便是:“這些大腳印象徵世界正向中國走來,中國向世界走去。二十九個大腳印也代表二十九次奧運的軌跡。”他説,“官員、警察、消防員都很感動於這種説法,願意用千軍萬馬幫我把這個計劃做到最好。”
雅跟俗,兩種説法,究竟哪一邊是真的,哪一邊是假的?
也許兩邊都是真的,也都不是真的。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奧運可能都被淡忘了,要是美術史會討論二十九個大腳印走過北京中軸線的藝術行為,也許奧運只是個『托』,幫助我實現藝術這件事。”
蔡國強對藝術界和對警員、消防員講不同的語言。然而今天很多藝術家喜歡站在精英的尖角,就算面對一般大眾,也不願意或也不懂去説群眾的語言。
蔡國強毋寧是對説群眾語言有高度天分的一位藝術家。
對藝術家,或是當代藝術家,或是人家常用的爆破藝術家等稱呼,蔡國強也不是一開始就接受的。他小時候連自己名字裏的“國強”兩個字都很討厭的,但是稱呼、名銜這些東西現在對他來説已經沒那樣值得在意了。
“以前我要做一個展覽,會跟主辦者花很多時間説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跟主辦者較勁自己的觀念。”比如説,蔡國強最近到日本,在廣島做了一個黑色焰火的爆破。“如果強調這個計劃的對抗性與前衛色彩,主辦者很可能因為你的説法就不給你市政府的支援。但是,如果你改變一種説法,説這是鎮魂,是對過去災難的悼念,就很容易被人們接受。”
“其實,兩種不同的説法,而我做的事情卻是一樣的。我做的就是在中午過後,在原子彈投過的廢墟裏頭,放了三分鐘的黑色焰火。在同樣的時間與空間,在此時此地,你做了這件事情,什麼説法其實都不能改變你所做的。”
“年紀輕點的時候,會用自己的態度和力量去堅持前衛藝術的説法,相信我們是在對時代提出創造性的資訊,其實這就是現代主義的基本價值。現代主義因為理念的存在,作品才有價值,若是沒有理念,作品就失去了價值。”
“可是我現在慢慢發現,我可以説他們容易接受的,但要做的時候我就照我要的做了,這樣可以省去很多麻煩。”
但是他也很不願意美術界的藝評家、策展人,對他作品的理解,僅止于他自己説出口的言語,他希望他們面對他的作品,而不是聽他的話語。
“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無創造力?自己有沒有激情?有沒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不能要求觀者理解很多,也不能要求自己一項做到很多目的,只能一個一個做。以後,人們也許會在混亂中理一下,沒有理清也沒關係,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很多自己覺得很好玩的東西,經過很多年後,還會有激情衝勁創作。”
“一件件作品宛如膠捲般記錄了每個場景,我要不要解釋廣島黑煙的意義並不重要,人們是透過作品與藝術家對話,而不是透過創作者嘴巴説出來的語言來與藝術家對話。”
“就像我因九一一事件的觸發,在大都會博物館的晴天空中放黑雲,又在西班牙那邊做了黑色彩虹,現在又做了一個三分鐘的黑色焰火給廣島。我想,這些事情的本身就構成了文本。”
“我相信,關於藝術的説明與任何語言,最後都會慢慢淡掉。很久很久後,人們不會記得我當時是怎麼説廣島黑煙的,但是就是只有一張卡片留下來,人們會看得到就是一張黑色焰火的照片,後面寫著 蔡國強,廣島2008年 。”
“未來就只剩下這些。因此我不用急,不用急著當下一定要説什麼,或者我是否被理解。”
“藝術跟語言的關係,總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什麼都説不清楚。什麼都説了,卻又像什麼都沒説。感到説多了,便減少一些,感到説少了,又加多一點。”感到説多了,便減少一些,感到説少了,又加多一點。”蔡國強説:“總是自己在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