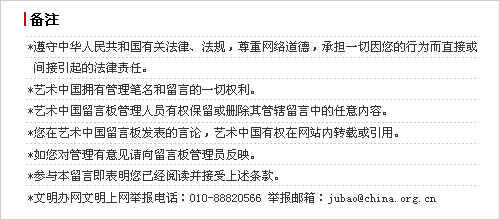蔡國強的每一項思考中,總帶有一點幽默與疏離的哲學意味。比較可惜的是,在那陽剛、龐大、與歷史對話的藝術計劃中,那份幽默與輕鬆的理解,也就是在嚴肅之中出現輕快以為節奏的美妙,卻常被藝術評論家忽視。
蔡國強在大陸有一句名言:“藝術可以亂搞。”有人稱讚這句話,也有人特別針對這句話批判他。
“亂搞”到底是什麼?蔡國強針對每件作品都仔細規劃,找盡資料,企圖與歷史文化對話,企圖與群眾溝通,為什麼卻又説:“藝術可以亂搞”?
“中國民族一百多年來的苦難,使藝術成為救國救亡改造社會的工具,主流藝術被當成清除舊社會黑暗、展示社會主義理想的工具。而反主流的前衛藝術,則把藝術當成改革開放,促進國家民主化的武器。在這個背景底下,藝術在中國就顯得特別痛苦。”
蔡國強認為,中國有很多令人感動的題材,如一九四九年逃亡的顛沛流離,那個時期勞動下鄉的荒謬辛酸,每一個故事説出來都會讓人熱淚盈眶。但當這些故事成為了小説,似乎都無法成為世界名著。因為作家在寫作本身下的工夫還不夠。畫家也是啊,把中國每個時代的歷史事件都畫出來了,但是這些東西畫了幾十年,藝術成就似乎不及抗戰時期木刻家的作品。
“簡單地説,就是 幹活 的 活 還沒幹夠!”
他拿中國人與日本人作比較,日本人在這方面很客氣,不會直接點破中國人的這問題,但心裏頭清楚,日本人覺得中國有深厚的漫長博大歷史傳統,中國人長的漂亮,畫畫模特兒又多,各種故事題材取之不絕。但是中國藝術家、建築家、小説家的作品,日本人看來就覺得這個“活”比較粗。中國人有這麼多好東西,還無法好好利用。
所謂“藝術可以亂搞”,其實是看到太多當代藝術家與策展人,談了太多太多藝術的理念以及創作的企圖動機,但説的是一套個,做出來的東西卻無法與説的那偉大的道理相映。“我想説的是,藝術不要光談這麼多偉大的理想,藝術要回到『活』的本身,要把藝術的『活』幹好,你要衷心認為藝術是好玩的,才會認真做好。”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蔡國強的每一項思考中,又總帶有一點幽默與疏離的哲學意味。比較可惜的是,在那陽剛、龐大、與歷史對話的藝術計劃中,那份幽默與輕鬆的理解,也就是在嚴肅之中出現輕快節奏的美妙,卻常被藝術評論家忽視。
“我不知不覺地也養成了説教的習慣,於是我要用我另一個幽默、好玩的天性消化,破壞我傳統古板的思路。藝術不好玩是不好的,但是要好好去玩。”
“很多時候,作品需要藝評家或策展人搭一座橋,把民眾帶進來,這樣我會很高興。但當民眾把那座橋當作我的作品的時候,我就很不高興。有橋可以方便彼此溝通理念,但當橋更被視為真實的作品的時候,不是很好。”
他也坦言其實這種問題不斷地再發生,是藝術領域中一個常見的問題。
“所以永遠都要相信,最終都會回到作品本身。因為藝術家會死,解釋作品的人也會死。就像我在MoMA(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展出《草船借箭》的那艘船,經常有人會從文化衝突、中國典故、新殖民主義等角度議論這些作品,但這些最後會被忘掉。幾十年後這件作品還持續存在,人們又會從另外的角度來解釋這件作品。”
蔡國強剛到美國的時候,正好是文化藝術領域理論最為迸發的時候,學院與藝術領域裏頭的人整天都談理論,這些學者會用這些理論來套他的作品。
“藝術家的魅力常常在創造出一個短時間內無法被説準、卻幾百年後都可以持續被討論的作品,而且甚至幾百年都無法被討論清楚,如果藝術家無法提供作品被持續討論的可能,這位藝術家就稍微有點可憐了。”
“現代主義以前的藝術與當代藝術很大的差別在於,當代藝術家是要創造出值得保留下來的理由,他的任務更大、難度更高,藝術家要去説服民眾,雖然整個世界都在變動,但這件作品是值得留下來的。”
可是,究竟作品值得留下來的理由會是什麼?人們會把眼睛留在什麼樣的藝術上頭,並且那麼多人會連同這一位藝術家一起相信,他們眼裏所見到的這一切,這胡思亂想、這無中生有的一切,是值得留下來,是該被選擇不要遺忘的?
“很多跟我一起成長、在國際上闖蕩的藝術家都是這樣。我們一起做展覽,晚上一起喝酒,並且互相刺激,會很關心對方正在做什麼。”
“有時候我看雜誌可看到對方的作品,一看就知道他在做什麼,而且知道這個作品的上下文脈絡,甚至知道他往下繼續做的會事什麼。好比下棋,有時候我可以感受到他下不下去,因此換了一盤棋,但這新的棋局與棋法,我可以看到有些還是一樣的。”
到底什麼作品是值得留下來的?
“作品值得留下來的理由,我經常一時説不清楚。藝術家也是啊,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位藝術家就像動物身上發光的毛,這是指動物的精神性很好,毛色漂亮光澤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