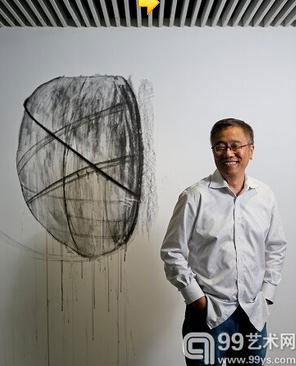
以華裔人口為主的新加坡處東南亞最具戰略價值的位置,亦相容並包中華、馬來、印度與西方諸文化,其當代藝術的創作與批評更是輕盈舞動於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木上。作為新加坡重要的美術史學家、策展人,新加坡美術館前館長郭建超前不久在上海證大喜瑪拉雅美術館舉行的文化論壇期間,接受了記者專訪,談到中國水墨傳統與當代藝術創作時,他表示:“水墨是很重要的文化資源,而這個資源必須找一種方式跟世界分享。其中微妙的難處在於:在新加坡,如果把水墨過度民族化,就會由於這種強烈的民族性讓其他文化難以認同;如果把水墨的民族性削弱,它又會回到西方思想方式中藝術課題的主流裏去,水墨本身就被淡化了。”談新加坡藝術:
“多元性是我們珍貴的文化寶庫”
記者:您作為一個新加坡策展人,怎麼看後現代和中國水墨的問題?
郭建超:我覺得水墨課題必須是一個國際課題。對任何文化而言很重要的課題都必須是一個全球課題。尤其是中國的水墨有這麼源遠流長的歷史,它從商朝末期就開始了,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千年,世界上有多少藝術的傳統是那麼久的?所以水墨肯定是一個國際的課題,因為它也是人類的課題。
記者:因為它是人類文明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新加坡有很多華人,水墨肯定也是新加坡藝術的一部分。能不能談談新加坡藝術這方面的源流?
郭建超:你講到水墨畫在新加坡是不是一個重要的美術課題,它的確是的。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興起美術教育的時候。中國南方像廣東、福建,尤其是潮汕地區有一些藝術家就來到上海受教育,變成上海現代化新美術的重要部分。他們中有一些回到了中國南方,另外有一些到了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美術也是有這樣一部分背景的。
在這其中,廈門美術學院非常特殊,他們創校的時候是到菲律賓去學畫的。上海這邊要出國學習美術,要麼就去東京,要麼就到巴黎。但是菲律賓有西班牙統治的歷史,經過很長一段時間,那裏也建立了歐式的繪畫學院。再加上廈門地區和馬尼拉地區特殊的關係,所以這些廈門的藝術家就到菲律賓學西畫。
那是一種雙面的關係。首先有上海和其他中國南部地區的區域性差異,再加上廈門本來就跟菲律賓有著聯繫,所以這批畫家跟東南亞畫家是一種相互的雙邊的關係。
記者:彼此影響的關係嗎?
郭建超:也不能説彼此影響。五四運動之後,這一批中國南方的藝術家來到上海,接受了上海的一些新思潮;但是他們又有在馬尼拉受教育的遺澤,所以也有一定西方藝術的基礎;後來又到南洋去,接受新加坡的文化的影響熏陶。這樣(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也産生了一些新的畫派,這些新畫派你可以看成是水墨畫在南洋經歷文化碰撞所産生的新的流派,也可以看成是一些支流。但是我們現在在一個多元的藝術框架下看問題,就不太用這樣的字眼來説,什麼是“支流”,什麼是“主流”。我們對任何不同的潮流都感到興趣,覺得重視。
比如説雲南地區的苗族,這裡(中國大陸)叫少數民族文化,其實它跟整個湄公河流域的文化是很接近的,有著一些湄公河流域的審美價值觀。所以這是中國的衍生嗎?還是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從泰國來看?當然這都是一種多元化的發展,也很慶倖能看到中國本身的多元化。
我們説回來,新加坡的畫家也跑到巴厘島去。作為一個畫家,以畫面去思考圖像的問題,當你到一個地方看到當地的音樂舞蹈宗教儀式,跟繪畫是不能分割的,你的基礎可以是水墨畫,但是整個審美的價值都被改變了。新加坡有個著名藝術家叫鐘泗賓,他就走向了裝飾的風格。這種裝飾風格不僅僅在於把一個平面圖像做得更漂亮一些,而是跟生活的節拍不可分割的,包括舞蹈和宗教藝術等。所以鐘泗賓雖然是水墨畫的底子,但是同時又有很多元的背景。他出自一個廈門的少數民族村落,進入廈門美術院校學習,這個美術院校又受到清末和五四新美術思潮的影響和熏陶,而這種新美術思想也是現代化和西化的基礎。
那個時候海派畫家講究金石趣味,在書法上特別重視碑文。在文人畫傳統裏,對“古樸”的推崇一直是很強烈的。鐘泗賓在東南亞地區又跑到東馬來西亞半島,那邊有很多本土的少數民族原住民,對於他而言,本身所帶有的中國文人繪畫“古樸”的審美價值和當地原住民的文化有了溝通,通過原住民的文化他又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再來理解中國的文人畫傳統本身的價值,再加上他本人就是在東南亞生活的,這其中是非常微妙的。當我們現在講到後現代問題的時候,這種多元性的確是我們珍貴的文化寶庫。
記者:所以我們不再用邊緣和中心這樣的詞彙,更加會看到其中多元化的差異性。新加坡藝術的源流,除了水墨畫之外還有別的,比如馬來西亞當地的藝術形式。
郭建超:當然是有的,這個説來就話長了,是整個馬來西亞藝術史了。
記者:新加坡的藝術家在處理後現代的問題時,和中國大陸的藝術家有什麼異同嗎?
郭建超:當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國籍的問題。
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們也是從很多西方的論述出發來做一些思考。甚至因為新加坡教育制度的關係,就會更直接地去接觸西方文化。但是本地的文化意識也是很強烈的。對一個藝術家來説,對這些會更加敏感,但他也不可能完全把自己脫離出整個群體而站在另一個角度去面對這些問題。就好像我本人對中國藝術很感興趣,但我也不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和長大的,那我所形成的中國藝術史的觀感和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是不一樣的,同樣,西方的藝術理論,新加坡的藝術家可能通過教育的渠道對之也十分熟悉,但是由於客觀的“身份”,就不會認為這是自己(文化)的藝術理論。
我們今天所談的,很難從很大的角度去劃分什麼是民族的,什麼是國家的,或者是把世界分成中西兩部分這樣二元論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我們最後能做出的總結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通過解構去深入了解這些藝術。所以我要講的“全球性”並不是全球歸一趨同化的全球性,而是真正全球對話的一個論壇。
後現代單從西方的角度是不可能把國際上的多元性都涵蓋的,所以上世紀90年代起他們積極地去了解世界上不同地方的藝術發展。他們有這樣的走向。站在西方之外的角度,我們也不可能説:“謝謝你們,終於接受我們了。”
藝術的好處就在於我們可以慢慢地去對話、體會和了解,而不是為了給自己挂上某一國家、某一文化的標簽,説我是法國的,或者我是新加坡的。這個都沒有什麼意思。
記者:在喜瑪拉雅美術館的展覽“跨地域的水墨經驗”中,我們也看到兩件新加坡藝術家的作品,您覺得這兩件作品中有什麼“新加坡性”嗎?
郭劍超:郭捷忻畫的是一個新加坡的景象,有著一種新加坡民間的味道。它是描繪社區裏的一些活動,日常生活的味道。從這個看,它是一件寫實的作品,直接描繪新加坡的。
陳玲娜用的素材是木炭。木炭的元素和水墨的元素其實是一樣的。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水墨進行解構的一件作品。我們説水墨畫的多元化,藝術家用的就不一定是傳統的墨、筆。從中也能看到對於當下的生活、當下的環境以及水墨畫本身做出的一些思考。陳玲娜選擇對水墨畫解構的方式來創作,採用與水墨同元素的木炭來進行創作,你可以説它是水墨畫,也可以説它不是水墨畫。
談水墨藝術:“找到一種方式將水墨與世界分享”
記者:現在關於水墨的討論還蠻多的,大家都比較關心這個話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之前也做了一檔水墨的展覽。從國際視野來看,一些人可能只是把它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媒介。您覺得當代水墨還有沒有包涵一些文人性在其中?
郭建超:在文化史上,水墨畫是一種特殊的東西。中國的科舉制度和朝廷官制起源很早,所以水墨畫本來就帶有雙重的身份特徵。首先朝廷裏本來就有畫院的畫家,但是朝中大臣的文化趣味卻在於朝堂之外的山林之間,尤其在明朝董其昌之後,也就是十六世紀中期之後,整個文人畫的脈絡就被制度化了,文人畫就被納入了中國繪畫的正統,而其實它的背景卻恰恰是不在於朝廷或者制度之內的,卻被朝廷所瞻仰,這是個很特殊的現象。
這個特殊的現象對當下的中國文化環境有怎麼樣的意義?中國官員喜歡文人畫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不接受社會寫實主義嗎?我對此不是很了解,但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這些官員在找尋一種文化標誌和符號。
然而,畢竟水墨、山水或者文人畫並不是那麼容易在國際上獲得廣泛的接受。很多人中文都不懂,更不要提書法,這對於華語文化圈以外的人是非常難的。這也不能去怪別人沒有能力去理解,因為他學習中文語言可能需要十年,學書法又是十年,是很難的。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在國際上非常強勢地崛起,有一些人把水墨或者文人畫看作是中國文化的標誌。國外的藝術界就會對此有一種情緒,一方面是出於不了解,一方面是出於抵觸,他們會覺得:水墨是你們國家非常陳舊的東西,我們可沒有興趣,我們現在做的是當代藝術。這樣的問題是存在的,越是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個人覺得,中國藝術界越有責任去向國際上説明解釋水墨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面對的就是這類多層次、多視角的對話,如果我們又站回自己的身份,只關注某一種傳統,文人畫傳統也好,別的也好,就會變成只有我們自己了解自己的傳統是有價值的,但是這樣一來,我們是否有必要跟別的文化圈分享我們的傳統?
所以水墨的課題是很重要的。之前談到的兩個課題,首先是“文人”的概念在當下社會有什麼樣當代的意義?另一個就是在全球的範圍裏面,這些古老的價值觀如何跟國際藝術界溝通?
記者:這兩個也是我們現在在處理現代與後現代問題中比較重要的,需要面對的問題。
郭建超:是。水墨是很重要的文化資源,而這個資源必須找一種方式跟世界分享。
記者:上世紀上半葉,在西方,亞洲的藝術文化——比如佛教與禪——有一陣是很流行的。
郭建超:是的,這又跟日本有關,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尤其是美國,他們對禪宗佛學非常感興趣,進而對水墨也開始感興趣。印度在二十世紀初期對水墨畫也産生過興趣。是一個比較小的文化圈子,那時候都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我們回過頭看二十世紀初期,就會覺得我們又走回了一百年前的路。甚至在美國二戰之前的一個階段,他們很多學校把水墨編進學科設置裏,因為他們覺得水墨不僅僅是新穎的藝術,更是覺得,如果要讓學生具有全球化視野,就必須把其他文化中很重要的東西放到課程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