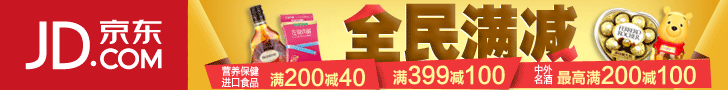羅本島記錄曼德拉的鐵窗生涯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3-12-06 內容來源: 央視新聞頻道

自從1944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後,曼德拉花了大約10年的時間使自己成為非國大事實上的領導者。最初白人政府沒有意識到他的力量,而非國大也只是一個黨派組織,所以他們只是因為權威遭受挑戰而遷怒于他。但當曼德拉在1961年6月創建了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並出任總司令後,白人政府知道,如果想使種族隔離制度在南非延續下去,他們就只能把曼德拉投進監獄。第二年8月,43歲的曼德拉入獄,罪名是“政治煽動和非法越境罪”,兩年後政府又給他增加了“陰謀顛覆罪”,刑期從5年變成了終身監禁。
從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島”之稱的羅本島上熬過了漫漫18載。
年近八旬之時,曼德拉對進島當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他在自傳中這樣描寫道:
“我們下飛機踏上羅本島的那天,天氣陰暗,凜冽的冬風透過單薄的囚衣,打在我們身上。迎接我們這群被判處終生監禁的幾名非國大成員的,是一幫荷槍實彈的獄警。我們旋即被押上囚車,送到一幢獨立的石造舊建築物前。獄警命令我們脫光衣服,然後他給我們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種族隔離的條例甚至體現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凱西拿到長褲之外,我們每人都是給的短褲。在非洲傳統中,短褲意味著我們是‘小孩子’,這顯然是一種污辱。”
“那天,我穿上短褲,但我發誓:我穿著它的日子不會很長。”
四天后,曼德拉等人又被押送到羅本島的“獄中之獄”——一座特別為關押政治犯而營造的新監獄。當局這麼做是為防止“危險”的政治犯將其政治觀點傳染給普通犯人。這座長方形的石頭堡壘,中間是一個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墻,墻中間是一條狹窄的過道,有牽著德國狼狗的哨兵晝夜巡邏把守,可謂“插翅難逃”。
曼德拉拿著剛發的三條薄得幾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後面,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盡頭的單間牢房。牢房門口挂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N·曼德拉,466/64,表示他是這個島上1964年以來接受的第466名囚犯。牢房裏霉濕氣味撲鼻,且十分狹小,只有三步長、兩米寬,躺下時雙腳會碰到墻壁,頭則緊挨著另一面墻,是名副其實的“牢籠”。
監獄有一套不成文的獄規,每位犯人必須嚴格遵守,否則將受到重懲。獄規要求犯人上衣的三粒鈕扣必須扣上,在獄警經過時必須脫帽致意。如果鈕扣沒扣好,帽子沒來得及脫,或沒有把牢房打掃乾淨,受到的懲罰是關禁閉和不準吃飯。曼德拉上島後不久,就嘗到了這個苦頭。
一天,曼德拉在長凳上發現一張報紙。沒有多思忖,他迅速撿起報紙,趁無人之際塞進襯衫裏。作為政治犯,曼德拉不準獲得外界的任何消息。這張意外得來的報紙對與世隔絕數月的曼德拉來説,無異於一頓“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根本沒聽到那漸漸逼近的腳步聲。等他意識到一位看守出現在自己面前時,已來不及藏報紙了。結果,他因私自擁有違禁品,被罰禁閉三天、禁食三天。以後,類似的懲罰成了他的家常便飯。
島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規律,近乎機械化。由於不允許攜帶任何計時器,囚犯們根本無法知道準確時間,吃飯、勞動和睡覺都由看守們通知。久而久之,他們連記憶月份和日子也困難了。這正是當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種手段。不過,這一招在曼德拉身上沒有靈驗。他來羅本島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墻壁上自製一個日曆,使自己生活得像個正常人。
如此封閉、孤獨、嚴厲而刻板的羅本島,不只是一座監獄,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獄。南非當局要在這裡撲滅任何尊嚴和人性的火花,把像曼德拉這樣剛強的政治犯熬煉成灰燼。
政治犯都穿上了長褲
入獄伊始,曼德拉就開始同監獄當局展開不懈而艱苦的抗爭。這是他在極其沉悶的鐵窗生涯中保持清醒頭腦,並逐步樹立其在難友中的領導地位的一種方法。很快,他便成為政治犯們的代言人。每當外界來訪或視察時,他都代表獄友們説話,力爭改善獄中惡劣的生活環境。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關押在隔離監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長。在這份請願書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裏卡人在“一戰”和“二戰”時均因叛國罪而判刑,但他們都未服滿刑期即被釋放,曼德拉與他的21名單人牢房的戰友要求享受同樣待遇;在被釋放之前,他們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較合適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應有閱讀一切未遭禁止的書籍報刊、聽廣播和看電影的權利;應有選擇專業學習的機會。他們指出,政府將政治犯不是作為有價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計去懲罰他們;政府未能將監獄作為恢復政治犯名譽的場所,而是將其作為處罰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權利,政治犯則被剝奪。當時,這封請願書在南非議會引起了震動。
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對黨——進步黨的議員蘇茲曼夫人到羅本島會見了曼德拉。曼德拉在與蘇茲曼夫人會談時,重申了自己在請願書中提出的無條件釋放的要求。蘇茲曼夫人認為曼德拉的理由論據不足,“你們是否準備放棄暴力和武裝鬥爭?你們與那些白人的不同之處是你們的鬥爭尚在繼續進行。不錯,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釋放了,但他們的鬥爭已被挫敗。這一點削弱了你們的論點。我不能要求釋放你們。”曼德拉的答覆明確無誤:在南非人民贏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戰友們是不會放棄武裝鬥爭的。
雖然與蘇茲曼夫人的會談失敗了,但曼德拉在監獄期間對暴力和武裝鬥爭的考慮更加週密,認識更加完善。他認為,光口頭上談論武裝鬥爭不行,必須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去貫徹執行這一方針。同時,曼德拉把提高獄中生活條件的鬥爭看作是反對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鬥爭的一部分。
從到羅本島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議穿短褲,並要求見獄方負責人,提出申訴。起先,獄方對他的抗議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驚喜地發現自己的牢房裏多了三條長褲。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獄友並沒有獲得與他一樣的待遇。
仔細斟酌後,曼德拉恍然大悟:獄方是想用幾條長褲來堵他的嘴,以便儘快平息不滿。他責令看守把三條長褲收回,除非每一位非洲囚犯都穿上長褲。看守不敢擅自取回長褲,最後監獄長韋斯爾上校氣惱地把三條長褲拿走了,但留下一句話:“即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們穿一樣的短褲吧!”
曼德拉沒有屈服,更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1965年夏天,國際紅十字會來羅本島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況。曼德拉抓住當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國際紅十字會詳實地介紹了他們所遭受的各種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訴,要求獄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條件,並真正聽取犯人們的申訴。這一招果真靈驗,國際紅十字會成員離開後,犯人的獄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長褲。
在羅本島,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這種生活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要在這樣極端孤獨無聊的環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過學習充實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讓重復不變的監獄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鬥爭意志。
曼德拉曾向獄方提出學習的要求,並獲允通過函授攻讀倫敦大學法學碩士學位的課程。同時,他為其他獄友也爭取到了學習的權利。
不僅如此,曼德拉又帶頭提出配備桌椅等學習用具的要求。這次,獄方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壓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們給每間牢房添制了一張帶有三條腿板凳的簡易書桌。
正是在這樣的書桌上,借著走廊上長明燈的昏暗光線,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時間自學了阿非利卡語(即南非荷蘭語)和經濟學,並偷偷完成了幾十萬字的回憶錄。
在凱西和西蘇魯等難友的建議下,曼德拉從1974年起開始寫回憶錄。“不要把這看作是個人的事”,被人們稱為“非國大的歷史學家”的西蘇魯表示:“這是我們鬥爭的歷史。”曼德拉的寫作進度很快,在短短4個月時間裏,即完成了初稿,從自己的出世一直寫到入獄前的審判,以羅本島的一些記錄結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壓縮成幾乎放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紙片上,然後將這些紙片藏在自己的筆電中,計劃讓提前出獄的難友帶出去發表。
為安全起見,他們將長達500頁的手稿分三處埋在監獄的花園裏。1975年,獄方為了加強對不同集中營的政治犯的隔離,決定在花園裏建立一排欄杆,以加固已有的圍墻。儘管曼德拉等人及時轉移了兩捆手稿,第三捆還是被獄方發現了,曼德拉等人被剝奪學習權利整整四年。
監獄裏組建的“高層機構”
在羅本島服役三年後,經過不懈的抗爭,監獄的條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犯們在勞動時可以自由談話而不會被看守打斷。在這種情況下,曼德拉、西蘇魯等非國大執行委員商討後決定,在獄中秘密建立一個非國大機構,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國大的反種族主義鬥爭。
這個組織的正式名稱是“高層機構”,其成員都是關押在羅本島的非國大成員。曼德拉擔任該機構的最高負責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國大全國執行委員組成常務委員會。其他成員按照牢房所在的區域,劃分成若干小組,每組指定一名成員為組長,負責聯絡和召集工作。
高層機構”作出的第一個決定是:獄內的組織不去影響獄外的非國大組織的決策。曼德拉認為,他們在獄中對外界的形勢知之甚少,若對自己不了解的事進行指導,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層機構”只對獄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訴、鬥爭、通信、食物等,作出應該作出的決定。
由於在獄中不可能召開經常性的大會,“高層機構”的活動便先由四位常委作出決定,然後分頭傳達給各小組長,再由組長傳達給每一位組員。為了把消息和決定從常委們所在的B區傳遞到與之隔離的普通區G區和F區,“高層機構”特設了一個秘密的通信委員會,專門負責傳遞資訊。
曼德拉和非國大成員通過各種方式互相鼓勵,始終保持高昂的鬥志。
“比親兄弟還親”的白人看守
對於監獄的看守和警官來説,他們從未見過曼德拉這種自信而有尊嚴的囚犯,並且,他還是一個黑人。
曼德拉的行為成功地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他會在早上試著同監獄長握手,會説早上好,還問他們妻子和孩子的情況。曼德拉總是以禮相待,特別是對有些年輕的看守,他就像父親一樣。有些看守還幫助曼德拉等人傳遞資訊,有的甚至還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裏的深厚情誼即是一例。
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裏起初認為,曼德拉是一個“恐怖分子”。漸漸地,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種東西觸動了。後來他回憶説:“我那時對他們那些黑人領袖仍持有偏見,認為像政府宣傳的那樣,他們要殺害我們的家人,奪走我們的家園,實行多數黑人統治。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發現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領袖人物,我開始尊敬他。”
曼德拉被列為羅本島的“頭號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終都很溫和。在格列高裏記憶中,20年裏,他只見曼德拉發過一次火。一次,一個白人看守譏笑曼德拉是個“白白浪費時間的黑種”,那時曼德拉正在獄中攻讀法律碩士學位課程。當時,曼德拉的聲音都發抖了,他對那個白人看守説:“你身上只有這一件制服讓我尊重,別以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膚會救你。”
在曼德拉周圍的15個白人看守中,格列高裏是唯一能和他談心的。他倆經常在獄中花園內安靜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膠樹下交談。他們從不為政治問題爭執,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見。他們兩人的兒子均死於車禍,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們的心理距離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裏傾訴內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時間裏,格列高裏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當曼德拉因小兒子馬克加索不肯上學而焦急不安時,是格列高裏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學校,以後,又送他上了大學。而曼德拉這位黑人領袖也成了格列高裏兒子的教父。在他倆之間,膚色的障礙已不存在了,正如他倆所説:“我們比親兄弟還親”。
然而,這種不尋常的友誼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種種議論。一些人説:“格列高裏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裏開始承受種族主義者的侮辱。他們中有的稱他為“黑人們的情人”,有的則往格列高裏家裏打匿名電話,甚至有人揚言要在街上打死他。種種威脅使監獄當局十分緊張,他們甚至不得不為格列高裏配備保鏢。
格列高裏至今還保存著曼德拉臨出獄前與他的合影,以及一張曼德拉親筆寫給他的卡片:
軍士長格列高裏:
20年來我們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今天結束了。但是我會永遠記住你,謹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誠摯的問候,並請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 責任編輯: 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