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中國 >
袁鵬院長談“政治博弈下的美國亂象”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 作者:袁鵬 | 時間:2020-07-31 | 責編:李曉曼
文丨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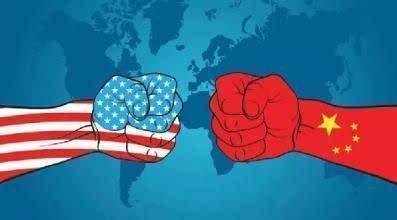
【編者按】最近,世界各地的民眾正難以置信地見證著發生在美國的一切——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致非洲裔男子死亡,“我無法呼吸”的乞求傳遍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創下悲劇性的記錄,超過美國自朝鮮戰爭以來所有衝突中因軍事戰鬥而死亡的人數;在最需要合作抗疫的關鍵時刻,美國宣佈終止與世衛組織的關係……美國媒體刊文稱,這些事件呈現了一個處於危機中的國家的嚴峻局面。
如何看待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系列事件?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專訪,進行深層次解讀。
問:日前,46歲的非洲裔美國人George Floyd在街頭被白人警察用膝蓋壓住頸部達七分鐘之久,Floyd一直乞求“我無法呼吸”,直至不省人事。此後美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答:在美國,警察暴力執法事件屢見不鮮。這次之所以引發如此大規模抗議,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警察暴力的視頻畫面在網上傳播,擊中了弱勢群體心中最脆弱的神經。Floyd瀕死前不斷乞求“我無法呼吸”,成為美國少數族裔在種族偏見和歧視陰霾下喘息掙扎的真實寫照;第二,10萬多生命死於疫情,民眾飽受痛苦、倍感壓抑,借此事件表達情緒。紐約州州長科莫稱,此次抗議浪潮同民眾對政府應對疫情不力難以分開。
挑起這次抗議的深層原因,還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問題。美國沒有令許多國家頭疼的“民族問題”,但“種族問題”則伴隨著美國歷史。從美國內戰到民權運動,黑人問題始終是美國最突出的種族問題,也是最大的政治問題。民權運動後,看似黑人的政治地位問題得到解決,但並沒有解決社會地位的平等問題,各種歧視依然嚴重存在。2008年奧巴馬勝選,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令美國黑人歡欣鼓舞。但奧巴馬在解決種族問題上作為有限,令美國黑人多少有些失望。特朗普上臺被視為“白人藍領”的勝利,在種族問題上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通過廢除奧巴馬醫保、美墨邊境修墻等舉措激化了種族矛盾,非洲裔、拉美裔美國人活得比較壓抑。
這次疫情,黑人死亡比例明顯高於白人,窮人死亡比例明顯高於富人。疫情期間美國沒有爆發大規模抗議,不等於人們不憤怒,非洲裔男子在白人警察膝下動彈不得、無法呼吸的現場畫面,讓積蓄已久的社會情緒迎來一次大爆發。雖然特朗普極力淡化,把它説成是一個地方性事件,諉過於民主黨州政府,但其影響已輻射全美。
問:最近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破10萬,感染確診人數突破170萬,數字之高遠超他國。作為世界上科學發達、醫療技術先進、醫療設施完備的國家,美國的防疫效果為何是這樣?
答:面對疫情大考,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不僅不能領導世界應對危機,還辜負了自己的人民”。超過10萬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這是一波令人震驚的死亡浪潮。其慘象超過“9•11事件”,死亡人數超過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之和。更加令人揪心的是,這場危機迄今為止仍沒有緩和的跡象。
美國抗疫不力,值得檢討的地方很多。此次疫情暴發恰好趕上美國大選年,兩黨明顯把疫情與選情掛鉤。對於特朗普來説,他上任以來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好的,失業率減半,股市翻番,這一切成為他謀求連任的最大籌碼。如果採取嚴厲的防疫舉措,勢必重創美國經濟,衝擊華爾街股市,這是特朗普政府不願樂見的,所以疫情初期一直在救人和救市之間猶疑,甚至一度把救市擺在救人前面。後來疫情發展遠超其想像,這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進一步措施。然而他的措施要麼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要麼隨意性太強,完全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應有的章法。更要命的是,他指揮不了各州,民主黨也要玩政治。雙方都把選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次要位置。國內政治因素是導致美國抗疫不力的罪魁禍首。疫情會對接下來的總統選舉造成多大影響,現在還不好説。但如果疫情導致經濟衰退、股市下跌、失業率上升,勢必對特朗普的選情造成衝擊。所以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他們迫不及待地要復工復産,實際上又是為了選舉。
問:從“斷供”到揚言退出,疫情發生以來,特朗普政府針對世衛組織動作不斷,不斷抹黑別國。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答: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追求單邊主義、漠視多邊主義,追求自私自保、弱化全球責任,此前已經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巴黎協定》、伊核協議等等。宣佈退出世衛組織,再次凸顯了其極端狹隘的自私自保,應該説不令人奇怪。但這次“退群”還有一個明顯的政治考慮:對於抗疫不力的責任,光打中國不行,必須連上世衛組織一起打,才能成功“甩鍋”。
疫情在全球氾濫,好比病毒這個“無形的敵人”在以特別的方式警醒各國:理順全球化的內在邏輯和發展方向,重新認識全球治理的極端重要性。但迄今為止的結果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政要,不是積極推進全球化加強全球治理,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遠太深;不是尋求國際合作解決醫用物資短缺等問題,而是狹隘地推動所謂“脫鉤”“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強國際組織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從世衛組織撤資、退出,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這只能讓美國在國際上繼續失分,包括德、法等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也看不下去,很多歐洲國家都是多邊主義的堅決捍衛者。
美國對華戰略近年來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即美國已經十分明確地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對手,並動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對華進行全方位遏制。而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止為因應中國崛起帶來的力量轉移,更意在遏制中國發展模式對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衝擊。一些美國政客耿耿於懷的,也正是中國制度對美國制度的深刻挑戰。此次疫情應對過程中,中美兩國表現的巨大反差進一步刺激美國一些政客打壓中國的制度。
問:如何看待美國國內目前的政治形勢?背後反映出美國社會哪些深層次矛盾?
答:近20來尤其是近5年來,美國已經變了,變得不僅外國人不認識了,而且美國人自己也覺得陌生。比如曾經高呼“歷史的終結”的知名學者福山,開始不斷批評美國已經進入制度的“衰敗”。究其根本,美國社會已經出現很深的結構性問題,集中表現為五大社會矛盾。
一是族裔矛盾。過去主要體現在黑人和白人之間,現在主線還是黑人和白人,但也延伸出白人和拉美裔、白人和非洲裔、白人和亞裔、以及少數族裔之間的矛盾。近些年來,由於少數族裔人口的上升速度超過白人人口,傳統的美國白人愈發覺得這對自己是一大挑戰。美國保守派學者塞繆爾•亨廷頓2004年出版《我們是誰?》,論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種種“挑戰”: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將使美國的核心價值和文化不斷萎縮,最終成為一個“擁有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和兩個民族的國家”。族裔矛盾不解決,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的精神之根必然萎縮。
二是階層矛盾。“佔領華爾街”運動喊出“99%對1%”的口號,就是美國階層矛盾激化的真實寫照。不少美國人憂心忡忡,自己生活在一個社會流動性降低的時代。據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切蒂(Raj Chetty)的最新研究:美國社會的“絕對流動性”,即下一代比其上一代父輩們收入高的幾率,從幾乎可以肯定的90%的水準,降到了拋硬幣一樣的50%的水準;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擴大;在美國幾乎所有地方,黑人孩子向上爬的通道都更為艱難。過去那種靠白手起家也能當官發財的説教在美國越來越沒人信了,教科書上講的那一條美國社會流動性似乎不管用了。
三是代際矛盾。不同年齡段的人之間因利益訴求、成長經歷、人生追求不同,也産生深刻的矛盾。青年人希望學費減免,中年人需要工作,老年人關注醫保。青年人喜歡桑德斯,老年人喜歡拜登,中年人尤其是藍領白人中年人傾向特朗普。
四是地域矛盾。“陽光帶”“鐵銹帶”“凍土帶”,不同地域之間也日漸隔閡。東西海岸各州擁抱全球化,內陸各州則多主張“美國優先”。美國50個州,大約40個州恒定支援共和黨或民主黨。總統競選的結果,最終由八九個搖擺州決定,“紅州”“藍州”日益固化、形成對峙。這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最鮮明體現。
五是性別矛盾。既體現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美國婦女受到長期的、系統的、廣泛的、制度性的歧視,各種公開的、隱蔽的性別歧視現象觸目驚心,也體現在對於所謂的“彩虹族群”(LGBT)上的態度不一,民主黨、共和黨對此就分野明顯。
五大社會矛盾不是平行存在,而往往是交織疊加的,在政治上集中體現為兩黨惡鬥,以及聯邦和州之間的不協調,進而導致美國政治極化“處在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時期”。蘭德公司研究人員蒂莫西•希斯撰文稱,“兩黨在很多議題上無法形成共識,每個政黨內約三分之一的選民認為另一黨對國家的未來構成威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則表示,目前兩黨已“視同仇人”,美國政治已“超級極化”。此次疫情期間很多措施不能落地,跟這種極化政治有極大的關係,任誰也不好解決。
問:有美國媒體評論稱:“曾經,美國帶來的是希望的故事;但是近30年後,美國的故事陷入了困境。”對此你怎麼看?
答:對於美國的政治極化和政治惡鬥,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痛心疾首,呼籲進行改革。但這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選舉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團的角力等等,一時間難以推進。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精英希望通過向外部轉移矛盾、樹立敵人來迫使兩黨緩和對立情緒。但“美國生病,別國吃藥”的策略,顯然無助於其自身問題的解決。
縱觀美國歷史,獨立戰爭後,美國國父們以憲法為基礎的改革,奠定了美國的基本制度框架;內戰之後,形成了進步主義運動的改革,完成了美國的初步崛起,並且經由一戰,確立其世界強國的地位;1929-1933年經濟危機後,羅斯福新政確立現代福利資本主義的模式,此後經由二戰,實現了從強國到西方霸主的轉換;通過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不斷強化其軍事工業複合體,最終贏得冷戰。美國的發展壯大乃至成為超級大國,一方面靠週期性的對外戰爭,一方面則靠階段性的體制性改革。
冷戰後,美國從“兩極”變成“一超”,加之全球化、資訊化時代的來臨,其內外環境再次發生革命性變化,本應再一次推進深層次改革以順應潮流。但遺憾的是,這場原本應該開啟的改革要麼被克林頓時期表面的經濟繁榮所掩蓋,要麼被小布希時期的反恐所耽誤,遲遲沒有展開,導致種種矛盾不斷累積。其結果,一個呼喚改革的年輕人奧巴馬被美國人民推上歷史舞臺。但奧巴馬空有改革的理想,缺乏改革的基礎,僅僅進行了一些技術性的改革,深層次的改革依然沒有展開。在這種背景下,終於迎來一個要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特朗普。特朗普真的是在“改革”,但他是以一種顛覆性的方式打亂美國的既有體制,打亂美國跟世界的關係,打亂傳統價值。“治大國如烹小鮮”,特朗普則在“翻燒餅”。美國看似經濟繁榮,股市高漲,失業率降低。然而這不是靠結構性改革實現的,而是靠美國霸權的老本支撐起來的,結果可能是坐吃山空、飲鴆止渴。美國的經濟結構、選舉制度、社會結構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美國要實現真正的轉型,還必須經歷一段時間的陣痛,對內要對兩黨制度、政治極化的現象進行深層次改革,對外要勇於擁抱全球化、資訊化的潮流,而不是背道而馳,這恐怕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應有路徑。
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