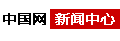李彥談文學中的親情困擾
李彥 (加拿大):親情困擾可能疏解于筆端?
幾年前,我應邀去多倫多,為一個讀書會做講演。那個讀書會的成員,清一色都是白種人職業女性。她們對我的英文小説《雪百合》中的母親這個人物形象,展開了意見相左的熱烈討論。
有的學者不解,為什麼在我的幾部中英文小説中,會反覆出現圍繞著母親發生的故事。母愛是個永恒的話題。千百年來,歌頌母愛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在我讀過的作品中,印象較深的,有高爾基的《母親》,張潔的《世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還有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
在我成為母親之前,我對母愛的理解是單純的。在我成為母親之後,我對母愛的理解,卻陷入了深深的惶惑。
長久以來,伴著歲月的流逝,我一直未能從對親情的困擾中解脫。也許在潛意識裏,正是這種惶惑,促使了我提筆創作。我抑制不住地試圖通過筆尖,梳理出對親情的反覆思索,層層深化,以求徹悟。
我等待了十五年,才把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説《紅浮萍》全部譯寫成中文版,呈現給祖國讀者。儘管時光的沉澱,已使中文譯本更趨成熟、客觀,但仍然引起了母親的憤懣。她揚言永遠不能饒恕我。
我反覆向母親解釋文學創作和回憶錄之間的不同,她實在不應當對號入座。即便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親人的一些傷心往事,我也希望她能有心胸,為記敘歷史的真實而做出奉獻與犧牲。
“媽媽,用不了多少年,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不完美的世界的,”我對她説,“而歷史應當存活在後輩人們的記憶中,才能使這個世界漸趨完美。”
母親不能釋懷,迫我反覆向她檢討道歉。中國文化強調“為尊者諱”。父母面前,錯的,永遠是孩子,這與西方文化格格不入。我雖在加拿大生活了27年,但我血管裏流淌著的東西,至死無法擺脫。和母親解釋文藝規律,已無濟於事,便只能無奈地任憑早該擯棄的文化糟粕一遍遍重復。
正如我在《雪百合》中所感嘆的:真實,是十分醜惡的。
倘若我們如實地描寫親情,該有多麼恐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曾寫信給我,論及我的小説《雪百合》與李南央所著《我有這樣一位母親》二者中存在的同樣一種現象,納罕是何種因素造就了這種特殊類型的女性。
這個問題很復雜,令我陷入了更多的思索。説真話很難。但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作者,應當堅持獨立思考、客觀地反映生活,而非趨炎附勢、投機討巧,隨意歪曲或美化歷史與人性。
不少人傾向於把一切不幸都簡單地歸咎于政治運動。然而,曹七巧的生活圈子裏,政治運動是零。 即便是在政治運動繁花似錦的歲月裏,眾所週知,磨難與衝擊也並未使所有的女性都喪失理性和母性,採用對敵鬥爭的手段來折磨自己的親生骨肉。虎毒不食子。那是為人的底線。
不可否認,性格造成了命運。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通過對一個又一個熟識女性的觀察與分析,探索人性缺陷所引發的問題,由此造成了她們命運的坎坷。不回避這樣的因素,我們才會對歷史和歷史中的人物獲得更加清醒的認識。
劉再復老師在《紅浮萍》的前言中曾有一針見血、力透紙背的分析:小説女主人公雯對于“父親”(組織)的絕對的愛與忠誠,使她喪失了其他一切的愛,並經受了貫穿一生的身心折磨。
他的話,令我想起了多年前偶然讀過的一篇英語論文,那是關於中世紀歐洲一個修道院裏發生的故事。該文描述了曾經生活在修道院裏的幾名年輕的修女。她們都在暗地裏把自己“嫁”給了耶穌·基督,通過對這位“戀人”的忠貞不渝,來維持信念,碧海青天夜夜心,渡過修道院裏悽清孤寂的漫長歲月。也許,女性是依賴于“愛”與“被愛”來生存的。修女們為自己“愛”的本能找到了寄託之所,成功地實現了情感的轉移。
愛,或者説親情,是我的小説主人公對她母親所寄予的悲憫情懷,同時也是小説中的母親希冀獲得組織認可時所孜孜追求的一種情感。
在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代,家庭和親情這些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在新的文化震蕩之下被扭曲和破化。作為驟然投身於變革洪流中的知識女性,雯們無可避免地掙扎于新舊兩種價值觀中,一方面,她們渴望以獨立自主平等的新女性形象自立於世,一方面,她們在潛意識裏卻依舊擺脫不了女性在傳統上對男性的心理依附。當這種依附無法通過美滿幸福的婚姻得以完善時,雯們身不由己地將這種情感寄託到了男權的替代物—“組織”的身上。
這個強有力的男權替代物所倡導的鬥爭哲學,需要雯們在革命的蛹化過程中勇敢地割斷一層層親情的絲線,並使她們象在追求一個完美無缺、高不可攀的戀人一樣,屢屢被拒之門外。她們的才華和努力都付諸東流,而從她們身邊奪走這一切的,恰恰是她們最渴望擁抱的戀人。
造物主是仁慈的,樂於看顧不幸的人們。他早已為普天下的女性都準備了一劑醫治心靈的良藥。無論貴賤貧富,能夠體驗為人之母的過程,實乃人生之大幸。
可嘆造物主的神情厚意,並非人人都能領悟。女性或者母性的情感無以寄託時,人性中惡的一面便會凸顯。女性往往會逃避面對強勢的男權,而選擇相對軟弱可欺的其他女性,作為報復的手段。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道,此時也成為方便的工具,使得失意的女性能夠名正言順地把滿腔怨憤都發泄到女兒的身上。當她們把女兒,而非兒子,看作一切不幸的根源之時,恰恰證明瞭她們遠未擺脫開傳統文化的桎梏,成為擁有獨立自主平等觀念的新女性。
雯們不懂得,博愛,才是治療一切疾病的良藥。悲憫和寬容,不摻雜任何目的的純粹的愛,才是真正至高無上的道德準則。和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她們只能接受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而把一切不幸都歸咎于時代和他人,從不反省自身的缺陷。
時代翻過了一頁又一頁,僵化的口號消失了,代之以物質的誘惑。今天的人們,陷入了另一種困境。除了錢,已經貧窮得一無所有。面臨著新的潮流,雯們的失落,使得她們的人生悖論愈加明顯。可悲的是,這代人已入耄耋之年,大多衍化成性格古怪的偏執老者,已無能力站在時代的背景下,冷靜地審視自己人生的得失,尋找到心靈的寧靜。
剛剛過去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北京,探望年邁的母親。一個落日將歸的傍晚,她突然悠悠地問我,“基督教如今在中國很盛行。據説,大多數中國人是為了祈禱錢財而信教的。焉知基督教的精髓,卻是教導人們學會懺悔的。是嗎?”
從母親已經昏花的眸子裏,我捕捉到一線微弱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