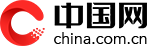近日,甘孜州公安局政治部組織知名作家媒體赴成都,對88歲的甘孜州公安局經文保處原處長馮雲富老人進行了深度訪問,有幸聆聽了有著67年黨齡老人獨屬於他們作為康巴高原第一代人民警察非同尋常般的傳奇生涯。

10個人的公安局
馮雲富,今年88歲——1951年從警,1994年退休,全程都在雪域高原聖潔甘孜。
1933年,他出生在甘孜縣——父母系從四川內地鄰水逃難到甘孜落戶,做小生意謀生。
老人回憶,從小就喝酥油茶,吃糌粑,與當地藏族孩子一起,在雅礱江邊、草原上、寺廟旁、野地裏摸爬滾打長大,除了衣著與當地孩子有區別,其他都沒有兩樣——他不僅能説漢話,藏語與當地孩子一個腔調,若穿上藏裝,就是一個藏家小子。
15歲那年,父母忍嘴從口裏挪出錢糧,送他到遠在康定的中學讀書。“暑假從康定回家,與同學合租牛幫一條牛,要走上20多天,路上哪黑那裏宿,草地山洞都棲過身。”所以,他對沿途的山高水長都瞭如指掌。
1950年,18軍進藏,在甘孜縣擴軍。他與幾個夥伴踴躍從軍。52師保衛科知道他熟悉當地情況,又會藏漢雙語,便讓他當通司(翻譯)。

1951年,甘孜縣籌備人民政府成立事項,部隊抽調他和5位外省籍戰友協助地方開展籌建工作。這一去就沒能脫身——新政府成立後,地方上強烈要求他們留下來,6個人就與當地抽調的四個同志一起,組成了甘孜縣首個公安局——當時叫公安組。
“10個人就在縣政府一間辦公室辦公,晚上集體滾大鋪。沒有明確分工,大家都抓治安。我因為會雙語,審訊的工作要幹,人口登記要做。由於文化又相對多些,文字材料自然歸我。其實,凡需要做的,都必須上手。忙得一天到晚幾乎沒有睡覺的時間。”老人説道。
槍林彈雨
1954年4月,已有3年警齡的他擔任了甘孜縣絨壩岔區工作隊副隊長。任務是開展當地各階層社會狀況調查,開展宣傳教育,組織並幫助當地藏族群眾發展生産。作為公安,他另有重任——調查土匪活動情況,配合部隊剿匪。
當年要剿的匪不是傳統意義上聚嘯山林的綠林草莽,而是國民黨軍隊殘部、反動土司頭人糾合的武裝、被他們裹挾的寺廟勢力、袍哥會組織。這樣的土匪有數十股,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數十人,甚至有跨越幾個縣聯動作亂,人數上千的匪幫並有台灣國民黨空投武器、電臺、人員支援。這些匪幫不滿足於佔山為王,而是四處出擊,攻擊區鄉甚至縣級人民政府。
“同他們的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搏鬥。曾經有一個工作隊懷孕的藏族女隊員,被土匪抓到後殺害,並殘忍地將她破肚。”老人如是説——那一段經歷,就是刻骨銘心的槍林彈雨!
工作隊就是剿匪先頭部隊——既是為大部隊提供情報的偵察兵,又是與土匪面對面作戰的第一梯隊。
作為“偵察兵”,現場偵察與蹲點守候是家常便飯。剛去工作隊那年冬天,他們偵查到了一股土匪竄進一座寺廟。在派人向縣上和部隊報信的同時,他們就地潛伏在在零下10多度的雪原上觀察土匪動向。餓了吃乾糧,渴了吃雪,凍得僵硬就僵硬,眼睛不敢眨眼——這個已經成了他們“偵察”時的常態。最長的一次,是在一個偏遠的雪山下潛伏了三天。糾纏他一生的胃病就是那時蹲點守候“潛伏”下來的。而正是因為有了他們卓有成效的“潛伏”,才有剿匪平叛的摧枯拉朽,捷報頻傳!

作為“第一梯隊”,真刀真槍是必須的!一次他們接到群眾舉報,有10多個土匪在一個草原上活動。他與工作隊同志合計,自己有30多條槍,拿下這股土匪小事一樁,不必花時間找大部隊錯失戰機。一行人縱馬出動。趕到現場才發現對方也是30多人,旗鼓相當。狹路相逢勇者勝,他們喊聲“打”就衝了上去。土匪見他們人少,散開隊形反包圍迎戰。他們邊射擊邊向土匪衝過去,打破土匪隊形,回身又以反包圍隊形壓向土匪。土匪再變隊形接招。幾番來回中,子彈在他耳邊“乒乒乓乓”亂飛。他回憶説,當時容不得瞻前顧後,就只有不顧不管拼殺!幾個小時後,土匪最終被他們氣勢壓倒,丟下10多名死傷者,在夜色中向山上逃竄。工作隊雖然無人犧牲,但也受傷了五六人。一個藏族小夥子就在他身邊中彈摔下馬。他清楚記得,當時那小夥子突然縱馬就衝在他了前面一米,否則中彈的就應該是他。在和戰友抬著擔架下山時,受傷的小夥子痛得不斷吼叫。他這才感到一身都是冷汗。
還有一次,他們通過情報獲悉,有100多名土匪聚集在一座雪山下。於是就出發追蹤打探情況。兩個多小時後,發現了土匪蹤跡,至少有300人。憑他們10多人衝上去,那就是送入虎口。大家一商量,派一人火速趕回向上級報告,然後撤回。回撤時,他靈機一動説,不走原路,而是從近道上公路返回,順便為進剿部隊尋找更好更多的進攻路線。正是這一決定救了他們——駐軍接報後,派出一個營按他們提供的情報第二天分兩路出擊,將這夥土匪圍剿。被俘土匪頭目供述,土匪當時也發現了工作隊的行蹤,並在工作隊返回的原路的山口派了60多人埋伏,準備一口將他們吃乾淨……
他扳著指頭算,與死神擦肩而過的驚心動魄,至少不下5次。
最讓他得意的是昌臺剿匪之戰。根據自己建立的情報網得知,昌臺聚集了來自理塘、義敦、新龍、白玉等縣的幾股叛匪,圖謀作亂。他當即安排人貼近查明具體情況,掌握叛匪動向。自己又親赴154團共同研討剿匪作戰方案,並與團參謀長帶領該團一個營緊急出動,在義敦、白玉、理塘呷瓦、新龍甲拉山等處設卡守候,將叛匪外逃通道都全部堵死。主力部隊在工作隊引領下,泰山壓頂出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土匪打得落花流水,完勝——擊斃叛匪36人,輕傷重傷13人,俘虜15人,自動投降28人,並連帶剿滅與之相聯的土匪上百人……慶功會時,團長、政委、參謀長輪流向他敬酒,醉得他人仰馬翻——他説,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喝醉,也是唯一一次大醉。
縱馬高原
夏天的草原,遠處雪山冰峰,眼前遍地野花,那時的馮雲富二十齣頭,可謂是羽扇綸巾,雄姿英發,隨時都在草原上縱馬賓士。老人談笑風生回憶,興致來了,就拍馬追趕路上吉普車,有幾次居然就追上了,得意地對著吉普車伸舌頭——因為那時甘孜的公路是土石路,吉普車許多時候跑不過烈馬。
只是雪域高原並非一年四季都是藍天白雲。深秋一開始,雪就來了,冰天雪地的日子幾乎有半年。路難行,人難行,連馬也難行。一次他下鄉回來,就遇到了一個手腳凍傷,饑寒交迫躺在雪地上孩子——這是一個10來歲的藏族小孩,進城與家人走散。他當即將孩子帶回工作隊駐地,帶到衛生隊請醫生救治,又根據孩子的敘説,親自將孩子送回了家。10多天后的一個下午,孩子的父親又來到工作隊找到馮雲富,“我上午親自看見有10多個帶槍的人騎著馬進了一個寺廟”。當天晚上,他們就在這夥土匪走出寺廟時,將其一網打盡。

馮雲富雪地救助孩子的事,當然不是個案。他説,1964年從甘孜縣調到州公安局時,當地群眾感謝他送的哈達就有一大堆——在工作組開展工作的方圓幾百公里兩個區,説“馮雲富”可能沒人知道,但説“有痣的漢娃娃”,當地群眾都知道。他們用藏語親切地稱呼他“甲珠勉切”(意為“有痣的漢娃娃”)——他臉上長著一顆大痣。
“有痣的漢娃娃”光榮稱號,來自於他與藏族同胞親如一家。下鄉就吃住在藏家,與他們一起喝酥油茶,喝酒,用地道的藏話嘮家常……村寨裏老人小孩與寺廟裏活佛喇嘛生病,他馬上到衛生隊請醫生到府救治。藏民牛馬被偷盜,他當成自己的事——他就曾10多次及時破獲偷牛盜馬案。當時的甘孜,許多藏族群眾對新政府不理解,而且還抵觸。但這些不理解與抵觸,在馮雲富的説一家話,喝一家酒,吃一家飯,睡一家床,辦一家事面前,便都冰雪消融。
除了“有痣的漢娃娃”,他還有另一個光榮稱號“大娘阿布(意為大娘的兒子)”——這個要拜他母親包實友所賜。父母當年雖是逃荒來到甘孜,靠著勤勞在甘孜縣城開了一間小小的雜貨舖辛苦度日,但為人卻極仁愛心善,每看到街角來進貨的馬幫坐在門口喝涼水吃乾糧,母親總要從店裏端點藏茶,舀一碗豆瓣醬給老鄉們下糌粑。因此遠近老鄉與母親都很親近,稱她“大娘”。所以,説到“大娘”,甘孜人都曉得是包實友,又因馮雲富小時候機靈可愛,討人喜歡,眾人就喊他“大娘阿布”。剿匪工作中,他獲得的許多情報線索,就是一些喊他“大娘阿布”的老鄉悄悄告訴他的。
舊時甘孜地處偏遠,農業生産落後,群眾生活艱難。為了讓藏族同胞過上安康生活,工作隊下鄉發農具組織群眾開荒生産。起初,老鄉們處於觀望狀態。工作隊於是讓事實説話,半天工作半天種地,幾個月後就收穫了青稞、蘿蔔、蓮花白,不僅改善工作隊生活,還送給群眾分嘗。群眾嘖嘖稱奇,紛紛找工作隊要種子要農具,積極開荒擴大耕地面積。生産一發展,群眾生活自然改善,心便都向著新政府,願意和工作隊打交道。
正是有了這樣的群眾基礎,許多老鄉就成了工作隊剿匪中的“編外隊員”,工作開展自然如魚得水。比如,在他主導破獲的台灣空投特務案、空投偽鈔案與販賣6800多兩鴉片大案時,自然就不缺情報線索。再比如,在甘孜遠近聞名的大金寺所涉重大叛亂一案中,他才敢在危急關頭挺身而出,領頭到寺廟與活佛談判——活佛與許多喇嘛他都熟。動之以情,曉以大義,活佛積極配合,交出土匪藏匿于寺廟內準備用於叛亂的槍支與迫擊炮。
在工作隊期間,他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在縣團委工作的藏族姑娘易慧敏——藏族名“益西拉姆”。恰好姑娘的哥哥益西居敏是他小學同學,其時在駐軍騎兵團任參謀長。彼此知根知底,益西居敏熱情地為他倆牽線搭橋,因此喜結連理。
何以家為
益西拉姆也是一個傳奇。奴隸娃子出身,才12歲就給進藏的18軍當翻譯。因為年齡太小,實在不能跟隨大部隊行動,到川藏交界處,部隊又派人將她們這些年齡小的送回了甘孜,參加地方工作。新政府成立,她進了團縣委,被派到區鄉工作,在這期間初識了馮雲富。之後,組織上為了培養少數民族女幹部,送她到中央團校學習,後分配到重慶的四川省委第二團校工作,還擔任班主任。但她的心卻在故鄉的土地上,主動要求回甘孜,這才有與馮雲富組成一個家。
可是這個家的前二十年,基本就是處於“四分五裂”中。他們的幾個孩子是這樣介紹自己小時的家——
老大馮曉萍:1964年,父母從甘孜縣調到州府康定工作,就把我和弟妹三人先後寄養在甘孜大嬢家。後來雖把我們接回康定,但因常出差,也沒時間管我們,許多時候,生活就由我帶著幾個弟妹自己解決。
老二馮曉冬:我生在康定,但父母工作在甘孜縣,我從小就寄養在康定劉婆婆家。劉婆婆見我長得可愛又聽話,兩歲時提出抱養我。半年後,媽媽實在捨不得,又把我要了回來。
老三馮曉紅:小時最盼的是爸爸回家。平時難得與我們見上一面的爸爸,回來就下廚房,做新學到的菜品青椒炒肉、木耳炒肉片、燉豬蹄子為我們改善生活。還陪我們下棋。我的象棋就是他手把手教的。那時爸爸常和我們玩“失蹤”,三月兩月不回家是常事,最長一次是調到新龍縣當公安局長,一年半後才見到他。

老四馮傑:我三歲時才被接到康定,但説不來漢話,只能説藏語。
1976年,馮雲富被調到新龍縣公安局任局長、政法黨組書記。他再度煥發青春,縱馬亮劍,全身心撲在工作上。當時新龍治安秩序異常混亂,發案多,但破案率僅為28.6%。他到任立即組織破案戰役,破案率上升到86.5%,重特大案件全破,當年發生的48起案件全破。
“我們家應該是公安世家。父親在公安43年,大姐是37年,如今,弟弟也在高原子承父業——貢獻了自己又貢獻兒孫”——馮曉冬如是説。
“十多年前,媽媽患病逝世,父親一夜之間頓然蒼老”。馮曉紅説時,聲音哽咽,眼圈發紅……
歲月留金
英雄也會暮年,但英雄必有讓自己熱血沸騰,情不能已的精彩畫面——
“我得到過十世班禪回贈的哈達。”——那是1986年7月,藏傳佛教格魯派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到甘孜州視察。這期間,馮雲富一直是班禪近身警衛——那時,他是甘孜州公安局經文保衛處處長。班禪的整個行程活動、行程路線、生活住宿等安全保衛工作方案,是他一手一腳做的,並得到了州公安局、省公安廳及更高層的審批認可。迎班禪時,他向班禪敬獻了哈達。沒想到班禪離開甘孜時,竟向他回贈了哈達,還送給他兩隻鋼筆。
“胡耀邦總書記給了我兩盒煙”——1985年9月,胡耀邦重走長征路,親臨甘孜。安全保衛工作方案,同樣也是他一手一腳做,也是近身警衛。一天,胡耀邦在駐地休息時,看到馮雲富經過門外,就主動招呼他進去,親切地同他聊天。當胡耀邦知道他在甘孜幾十年,藏語説得非常好時,欣慰地握住他的手説,“涉藏地區就需要你這樣的同志!”之後,拿出兩包特製的雙喜牌煙,塞到他手中。馮雲富不抽煙,但心裏卻想著將煙帶回家,給抽煙的老二分享。不曾想剛回駐地,就被參加保衛工作的弟兄們一搶而光。“耀邦總書記沒一點架子和派頭,我......我,就像見到了分別多年的老上級,老上級!”老人激動得竟然有些結巴。
“鄧小平同志我也見過”——那是1964年,四川省人代會需要懂藏語的公安人員參與大會安保工作。馮雲富被抽調到成都,進了大會安保組同時兼翻譯組。人代會後,來川視察指導的鄧小平總書記接見了大會工作人員。他清楚記得,小平握住他的手,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對他説,“你們在高原涉藏地區工作很辛苦,黨和人民會記得你們。好好幹!”
往事歷歷如燦爛的星辰閃亮太空。説到這些榮耀時刻,老人從沙發上騰躍而起,雙眼放光,眉飛色舞,手足比劃——這叫戎馬一生,歸來仍是少年!

退休後,老人以自己名字為根,取了筆名“水雨田”,寫下了10多本涉藏地區工作回憶錄。老人自豪地説,在工作隊時,他做情報工作,就為民主改革初期甘孜政教的局勢寫了12本情況報告,為土司頭人、寺廟喇嘛,尤其是西藏直接管轄的大金寺活佛、堪布、格西等人寫了120余篇人物小傳,在民主改革時期,為上級黨委政府和公安部門決策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陳大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