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時世與遠大前程:戲劇才子們 走出校園之後
發佈時間:2021-11-12 10:37:40 丨 來源:北京青年報 丨 責任編輯:高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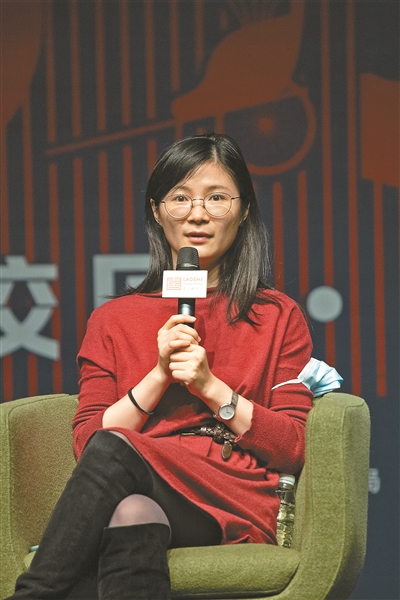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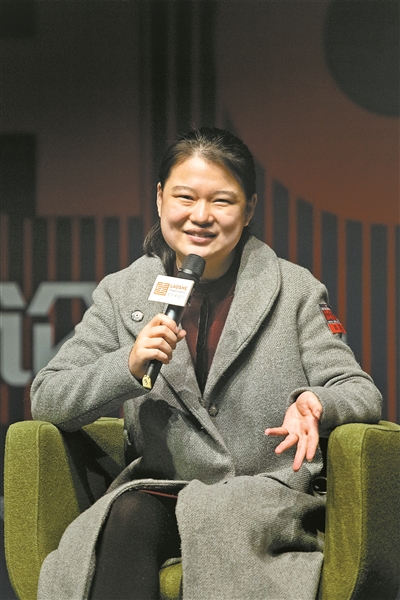


◎天真
2021第五屆老舍戲劇節近日舉辦以“校園·戲劇·人生”為主題的論壇,分享觀點的嘉賓包括從事戲劇教育和校園戲劇實踐的專家、教師,以及多位從校園戲劇中成長起來的青年戲劇人。
溫方伊、朱虹璇等近年活躍在戲劇界、具有創作影響力的新生力量,帶著“戲劇才子”的光環走出校門,以戲劇這個小眾行業為職業,適應環境、開啟創作、尋找機會、推廣作品。
戲劇創作和戲劇觀眾的源頭活水都在校園,年輕創作者的成長經歷是整體行業生態的個案寫照,解讀他們的生存狀態,也許是回應戲劇人才不足、創作衰弱等戲劇困境更為具體而有效的辦法。
朱虹璇:
辭職做全職戲劇人
一個月後疫情暴發了
朱虹璇,編劇、導演,代表作《四張機》《春逝》《雙枰記》
2012年,我參加北京大學巨星風采大賽初賽,改編《十二怒漢》。因為比賽時間比較短,就砍掉了幾個角色變成了《九怒漢》,這就是我們劇團名字的由來,“九人”。
我們前幾年做戲,既不是因為要靠這個吃飯,也不是因為對戲劇有多大的熱情,什麼也不懂。2014年我們在蓬蒿劇場做了離開學校以後的第一次商業演出,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我的職務,我的工作包括紙糊道具、劇場保潔,還包括挨個給劇場打電話問我們有一個戲你們願不願意接受我們去演,大家都是“你誰呀”這種態度,最後去蓬蒿劇場演了一場,總成本6000塊錢,虧了3000塊錢,聽上去也沒有很慘。
有一場演出演到一半紙糊的窗戶掉下來了,當時完全就沒有演出事故這個概念,大家在下面説好刺激,就覺得做戲真是太好玩了。還有一場演出,有一個時鐘吊得不太好,一邊演它一邊旋轉,還有觀眾問,你們這是暗示了什麼?黑暗的力量佔據上風的時候,鐘就轉到了背面。其實全都是意外。
後來我們就去了繁星戲劇村西區,一年一年繼續往下演,陸續演到天橋藝術中心、國家大劇院等等,每年都會做一部原創的作品。
2018年我開始自己做導演。我做導演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找不到導演,我原先只做編劇,想像中舞臺實現就是一個黑洞,不知道最後做出來是什麼樣,開始做導演以後明白有很多事情是可以一步一步做起來的。第一次做導演不會做減法,讓女演員上去舞劍、撒雪花,還有打戲,還有皮影戲,花裏胡哨都往上堆。我們這些年的成長就是虧的錢越來越多,那年我們就虧了十幾萬。製作人説如果還想繼續做,那就當作戰略投入吧。
我們沒有投資人,也沒有官方背景、企業背景,製作人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幾個人從自己這麼多年掙的工資裏掏一點出來,所以就會做得很省。有些戲學校撥一點錢、基金撥一點錢,或者有一個出品機構,會有百十萬的資金,我們直到現在還在10萬以內的規模做戲。我有一個例子,看過《四張機》的觀眾可能記得舞臺上亮起一首詩的燈箱,那個燈箱第一版是淘寶上60塊錢買的鞋架,再拿紙殼糊上去,手工貼LED燈條。燈光師老范有一天很著急地給我打電話,説原先我買的燈條做出來效果不能達到預期。我説那你有別的解決方案嗎?他説有,那就得換另外一種更貴的燈條,但是那個要貴不少錢。我説你説吧,貴多少,我去跟製作組申請預算。他説要貴10塊錢。對,這是原話。當時我也覺得有點那個,真的嗎?貴10塊錢你覺得是這麼大的問題嗎?他説你只看單一組燈條貴10塊錢,加起來要貴50塊錢呢。我説是不少。就是窮到這個程度。直到現在,道具老師給演員配眼鏡去潘家園都是10塊錢、10塊錢地砍價。
從2019年做《四張機》開始,我們的票房就開始好起來了。那一年好像有《聲入人心》的影響,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走進劇場,可能一開始想去看音樂劇,後來拓展到看話劇。音樂劇才是真正的風口,帶著我們一起飛了起來。
這些年我們確實做了不少的動作,我以前特別不會寫劇本,我主題先行,以觀點為主,不會寫活人。到《春逝》開始把更多的筆觸放到人身上,慢慢地找方法進步,宣發、製作各方面都在成長。2019年我們就能夠做到一個戲可以自負盈虧,也是受到了這個鼓勵,我辭職出來全職做戲,那時候我們好不容易做到第八年,覺得可以繼續試一下。但就是在我辭職一個月後疫情暴發,演出場所關閉。
2020年我們本來已經做好了所有的戲都不能上演、所有排練都停掉的準備,正好有一個“培源·青年戲劇人才培養及劇目孵化平臺”,《春逝》這個戲我們當時想投了試試看,結果拿到了比較好的成績,所以當年就把《春逝》這個戲做出來了。然後《四張機》和《春逝》就不斷打磨,口碑一點一點好起來,所以到2021年就做了《雙枰記》。
邵斯凡:
無論多困難先把作品做出來
帶著瑕疵讓觀眾看見
邵斯凡,編劇、導演,代表作《北緯66.5度的夜》《生日快樂》《卡埃羅!那一個心醉神迷的夜晚》
我2005年做第一個導演作品,是在法國讀大學的畢業作品,選的是我師父編劇、導演的作品叫《約翰和瑪麗》,在學校得了最佳作品獎。當時非常自信,覺得從今以後就可以進入戲劇行業,讓我的作品走進正式的劇場。
但其實後來走出校園遇到的困難非常多。我剛才聽大家説在學校排戲要爭排練廳,我們學校排練廳還是蠻多的,總能找到一個排戲的地方,雖然有時候要在走廊,而且有演出作品的空間。這些好像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直到走出校園才發現是這麼的困難。雖然導師能夠幫助我們和外面的戲劇空間建立聯繫,但是對於一個非常年輕、完全沒有經驗的導演來説,走出校園在一個正式的劇場和空間找到真正的觀眾,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有的劇場需要我們再等兩年,這是不可能的,兩年以後我的同學有可能都改行了。還有一些劇院需要付場租,最好的條件是分票房,我們的經濟能力完全無法實現。所以走出校園對於我來説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繼續創作,繼續保持創作熱情。
我現在會和剛剛開始創作的年輕導演説,做作品這件事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保持,不能把自己的想法構思停留在家裏、臥室裏,而是要盡一切的可能性,無論用多少錢,無論有多困難,讓這個東西做出來,帶著它的瑕疵,帶著它的缺陷遺憾讓觀眾看見。當時我和我們班一半的同學創立了一個劇團,大家用工作收入來維持這個小劇團的正常運營。回國以後也一樣,我還是想辦法儘量保持正常的製作環境,能夠給演員找到一個好的排練廳,能夠讓大家在有一點點經濟保障的前提下去創作。
我能説什麼給大家一點信心?當我們還什麼都不是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很多作品的時候,當沒有很多人知道你的戲劇風格、你想做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怎麼去找到製作人、出品人,怎麼找到錢?我的經驗是,開始真的就是刷臉,就是儘量不用錢,燈光也好、舞美也好,讓所有的朋友、夥伴在沒有錢的情況下工作一個月、兩個月,做出一個作品,慢慢地有些人會來聊後面的合作,因為他們看到之前的作品,看到裏面的瑕疵,又看到裏面有點意思的東西。
總結一句話就是,對戲劇滿懷熱情的年輕人,有一天走出校園,困難是永遠會有的,錢是永遠不夠的,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在操場、停車場等等任何地方去排你的作品,讓你腦海裏的東西,通過和演員、舞美、燈光的溝通來實現,讓其他人能夠看到,慢慢地就有可能找到越來越多的夥伴。
溫方伊:
萬一處女作即巔峰
之後怎麼辦
溫方伊,編劇,代表作《蔣公的面子》《繁花》《活動變人形》
每次人家一講到曹禺23歲寫出《雷雨》,溫方伊21歲寫出《蔣公的面子》這種話的時候,我真的很慚愧,我是一個90後天才編劇嗎?並不是,是因為很多天才的人都選擇了其他的職業。在我本科的時候,有幾個同班同學比我更有才華,只不過他們後來轉行了。他們轉行的理由是感覺戲劇是不怎麼正經的行業,尤其綜合性大學的學生特別容易有這種想法。我的一位學姐是很成功的編劇,她總想要一個正經職業,於是就去銀行實習,直到有一次參加了銀行的年會,見識到了燈紅酒綠背後的空虛,就覺得其實銀行業也不怎麼正經。
我自己並不是一個很主動的人,以我的性子,如果沒有寫出《蔣公的面子》,或者寫出來沒有演出那麼多場、沒有去外地演出,可能畢業之後就找一個坐辦公室的職業,從此作為一個戲劇愛好者生活著。
我之所以走上這條路是因為我有一個特別愛折騰的導師呂效平。他當時開著他那輛破桑塔納,我坐在後面,他説如果這個戲演到30場、50場會怎麼樣?我想,天方夜譚,在南京這個地方一個戲能演到10場嗎?我要感謝他的愛折騰——對於綜合性大學而言,一個老師去做戲劇實踐對於他評職稱沒有任何的幫助,當然那個時候呂老師也不需要評職稱了——呂老師所幹的這些事情在他的同行眼中都屬於不務正業。
我也很有幸正好處在一個大家的觀念在轉變的時期,環境是在慢慢變好的,我是這種環境變好的受益者。我本科畢業去面試藝術碩士,老師笑瞇瞇地跟我説很好很好,我們不需要那麼多寫論文的學生。但是我聽説過,可能往前倒幾年,我們自己培養的本科生怎麼能讀藝術碩士不讀學術碩士?
後來我們有了自己的劇場,一個頂多坐150人的黑匣子,自從有了這麼一個場地,感覺到如魚得水。南京大學現在有週末劇場,每週都有戲演,而且不僅我們專業受益,還能供別的社團排一些小戲。我很崇拜外文系的同學,他們讀到沒有翻譯成中文的劇本,自己跟編劇聊版權,沒有舞臺範本可以模倣,他們自己做導演,非常有創造性,在我看來是可以拿出去商演的程度。
如果要説我自己的人生有什麼改變的話,就是因為有這麼多助力,讓我有信心將來繼續做這一行。我父母都在電力部門,當初我高中選文科的時候,他們就説,你選文科,將來找工作我們就不可能給你提供任何幫助了。如果你讀理工科,哪怕讀一個很差的學校,我們都可以幫你安排個工作。但是我就是走上了這條路。這兩年我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趨勢,一到每年填大學志願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説,女孩兒不要學文藝,不要以為女孩兒只能學文藝,你們要學理工科。我就只能説,沒關係,學文藝也不丟人。
我是一個很懶的作者,人家説我八年只有兩部戲,到底在幹什麼。一個是害怕,另一個是懶。《蔣公的面子》實在是起點過高,大家都希望我能推出更好的作品,我覺得這是不大可能出現的事情,之前廣州大劇院的工作人員問我是如何保持高品質産出的,我説只有兩部作品叫保持高品質産出嗎?對於藝術家來説,保持高品質産出的唯一方法就是産出了高品質作品之後再也不産出。哪怕是最頂尖做藝術的人也無法保證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是完全不合格的都有可能。
為了不失敗,我就選擇不産出。直到出現了一個計劃外的事情,就是我懷孕了,而且懷的是雙胞胎。那時候覺得不行了,我一定要為我的職業想想未來,所以一下子就接了《活動變人形》和《繁花(第二季)》,付出的代價就是孕期和月子裏一直在寫劇本,對身體摧殘比較大,但這個很正常,所有的編劇都有職業病,所有的職業都有職業病。
祖紀姸:
在上海看戲的是觀眾
在北京看戲的是老師
祖紀姸,編劇、導演,代表作《晚安,媽媽》《嘿,是我》《最完美的婚姻》
我讀的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影視編導專業的本科,然後是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的碩士,我是學術碩士,學的不是電影實踐的研究,是電影理論研究,其實是就電影哲學的研究。
我可能是先成為一個“戲劇導演”,後成為一個戲劇愛好者。“戲劇導演”其實是要加引號的,在我大四的時候抱著完整自己大學生活的心態去報名參加北大巨星風采大賽,在那之前,我看過的戲一隻手絕對可以數得過來。那時候做戲完全出於一種本能,以及來自讀過的文學和一些中小學課本劇的經驗,不懂任何的專業手段和藝術技巧,沒有指導老師,完全是一個野生的狀態。我們是把這件事當作豐富人生來進行的,而不是想要做一個多完整的作品,藝術的初心是為了自己。
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戲劇市場其實既不缺優秀的編劇,也不缺優秀的導演,最需要的是優秀的觀眾。我這麼多年做的就是純商業戲劇,因為我是做小劇場戲劇的,很少能夠拿到真正的政府扶持,必須一張票、一張票賣出去養活自己、養活團隊。我特別能理解貧困戲劇的貧困。有一個玩笑説,在上海看戲的是觀眾,在北京看戲的都是老師。我們的校園劇社和校園活動能讓所謂的“無知”同學走進劇場排戲,通過排戲知道戲劇這門藝術很有魅力,開始願意走進劇場,願意把自己的閒暇時間、富餘出來的一點錢花在戲票上,這就是中國大學戲劇普及對戲劇行業非常重要的支援和支撐。
現在真正的戲劇觀眾太少了,戲劇人才流失,所以戲劇可能會讓大家擔憂,會不會消亡?會不會衰落?但用市場化的方式來思考,培養出足夠優秀、足夠多的戲劇觀眾,這個行業就有未來。
供圖/老舍戲劇節
原文連結:
http://epaper.ynet.com/html/2021-11/12/content_386765.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