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年輕人要敢做“不怕失敗的堂吉訶德”
發佈時間: 2017-09-14 10:29:35 | 來源: 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 責任編輯: 王子楓

不久前,一篇演講視頻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單身的黃金時代,我們如何面對愛情》。演講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開場甩出的六個問題,個個戳中當代青年心肺,立馬成了網上熱鬧的論辯話題:
“未來愛情會面臨的六大難關:我們敢不敢和A女比翼齊飛?能不能克服愛情中的肌無力?還相不相信一見鍾情?你會不會殺死回家的浪子?墮落是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別處?”他用真實而單純的語言,去描述現代社會最為複雜且多樣化的愛情認定——
“愛情最根本的,是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梁永安演講截圖
稍稍做了些功課,發現梁永安專攻比較文學和現當代文學,著作、譯作不少,且在復旦學生中人氣相當高,被稱為“復旦中文系的智慧”。對他,學生的評價是,“孩子般的純潔、乾淨,機智、博愛、謙遜,尊嚴而不顯疏離,深刻卻不犀利,抱著深切的關懷,洞察著現實與人的深刻本質”。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課給師兄發短信,“過於激動,復旦滿足並且超出了我對大學的所有期待”,梁教授開的“當代中國小説選讀”,場面向來極震撼,提早半小時到場都沒有空位,後排黑壓壓站了一片,然後是“一個半小時的思想衝擊”,“梁師魅力無敵”。
一個年逾花甲的文學教授,何以會對青年最關切的問題情有獨鍾?一位50後大叔,何以總能戳中90後小屁孩的痛點?
這顯然是一位不僅僅囿于書齋的有趣學者。於是,在上海最熱的那天,我帶著筆電坐到了梁教授對面。梁永安教授問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談方式,自帶樂觀的光芒。兩小時談下來,深知學生之嘆不虛,而筆者所能擷錄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説説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嗎?您是怎樣與文學結緣的?
梁永安:小時候,我在軍隊院校里長大,看書條件不錯。讀了很多紅色經典,蘇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鐵流》,中國的《紅日》、《紅岩》、《紅旗譜》。那個時代的文學,貫穿著一種紅色美學,核心部分和革命、階級、國家民族這些關鍵詞相聯。當時也能閱讀到一些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狄更斯、巴爾扎克、左拉、托爾斯泰等,它們則從個體價值、人道主義出發,構成與革命文學不一樣的精神空間,對我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初中時,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隨手投給《雲南日報》。沒想到,幾天后校長帶著報社的人找到我,原來人家要審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襲,以準備刊登。從此老師開始覺得我是可以寫東西的。老師不讓學生上課看閒書,卻指著我説,“梁永安例外”,當時非常自豪。
後來,我在雲南高黎貢山做了整整兩年的插隊知青,大長見識。我發現老鄉做飯,有個秘密原料。當地樹上的螞蟻窩很多,老鄉把一窩螞蟻整個割下來,再把螞蟻敲出來,用大紗布裹住使勁擠,螞蟻肚裏酸水就出來了,這就是當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這東西了。但後來得知,這種蟻酸營養高,能抗瘴氣、濕毒,防止生病——你看,這就是長期形成的鄉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邊的芒合——一個傣族村寨,剛到那天,老鄉們趕了六頭牛來幫我們搬行李。寨子裏大多是文盲。但我們從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貧下中農學習,所以我們精神上的姿態特別低。我們四個男生住在一戶農家院兒的偏房,茅草頂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覺得苦,拿幾個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勞動就是割稻,彎著腰,很吃力。然後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繩把稻穀壘高,捆起來,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塊,一層層垛上去。垛子越來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勞動雖然辛苦,但對人的鍛鍊很大。

高黎貢山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復後第一批錄取的大學生,為什麼會選擇現當代文學為專業?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傳來的全國新聞聯播中,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很興奮。我自信一定能考上,畢竟一直沒斷過讀書的習慣。當時我已經在工廠幹了兩年多電工。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就讀了中文系,至於選擇當代文學為專業,説起來也很偶然。本科時我很喜歡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準備考王運熙先生的研究生。但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研究生招生也要聽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學批評史專業研究生的學校很少,於是我畢業的那一級停招,只好轉考中國現當代文學了。
復旦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們
人物工作室:當時的復旦大學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梁永安:復旦的文化與學術分量非常重。當時,中文系的朱東潤、郭紹虞、張世祿等老先生都在,他們從小受國學熏陶,學養厚重,很有文化氣勢,人又謙虛,真是儒風拂面。有次請北大的王力先生來講課,在第一教學樓三樓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話:“你們復旦門檻很高啊,進來很不容易啊!來這裡呢,要特別感謝我的語言學啟蒙老師,就是張世祿先生,看了他的書,我才走上語言研究的道路。”那麼著名的學者卻這麼謙遜,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結束不久,老先生的價值一下子都釋放出來,到第一線上課,把終生積累全都拿出來,傾囊相授,給我們這些本科生極大的精神恩惠。
比如朱東潤先生。他那時已經八十歲了,身體還很厚實,説話沉穩大氣。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去英國留過學,歷經滄桑。我當時在中文系學生會,負責宣傳,有一些活動要請朱先生,他都很熱情。還有郭紹虞先生,學術大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請他給中文系書法展寫題頭,師母説郭先生身體不好,沒力氣。但郭先生説這個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寫。我過了四五天去取字,師母説,郭先生握那麼大的筆寫不動,後來在筆尾裝了一個環,用線挂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寫出來的。我聽了特別震撼。我去拜訪王運熙先生時,看到他的書房挂著一幅字“飲河軒”,我一看就很敬佩,這取自《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意思是自己學問很少,非常謙虛。
外係的一些老先生也讓人印象深刻。像哲學系的嚴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籃橋監獄關了好幾年。但他到了監獄也不閒著,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學、古代哲學。嚴先生上課不帶講義,肚子裏裝著 2600 多首和禪宗有關的古詩,上課講到哪兒就寫一首,一個字也不會錯。我特別佩服這些老先生,一輩子價值就在求知和治學,人很純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學統,我們復旦才有“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種世俗誘惑的“無用”之心。我大約就屬於比較“無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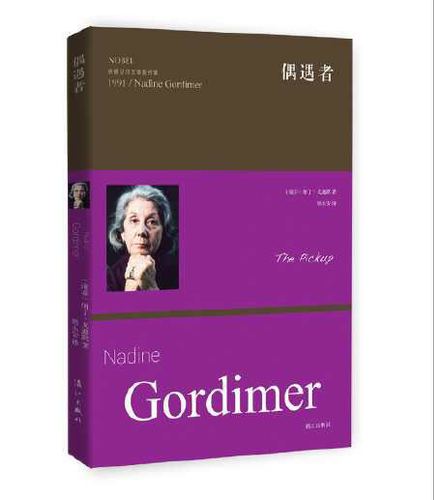
梁永安的專著

筆者與梁教授
未來30年,將是人的現代化的30年
人物工作室:您一直從事比較文化研究,這對您看待中國和世界有什麼啟發?
梁永安:我以前深受王元化、施蟄存那一代學者影響,他們覺得中國最重要的任務是原原本本地把西方原典翻譯過來,強調多吸收外來的東西、減少摸索的過程。這固然很重要,但長期以來,一些中國學者有些走偏了,過於重視歐美、尤其是美國。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容易形成“單向思維”。
我們關於“現代”的概念,就囿于美國。為什麼中國的那麼多城市都一個樣?這絕不只是規劃部門的事,也是因為中國人心中所能想像的“城市”,只是倫敦紐約那樣的,想像不出充滿生態文明的那種城市。我對中國的現代化抱有信心,關鍵是如何對待將來的30年?未來30年,我們還有3億農民工要進城。此前2、8億農民工進城,都是在城市工地上搬磚頭、拌沙子,做體力勞動,從經濟學角度看,是被“資源化”了——進城的只是勞動力,鄉土文化、家族文化、傳統文化沒有融進城市,某種意義上是被切掉了。文化是有脈絡的,柬埔寨修一條20公里的路,都想著要考慮雨蛙遷徙的路線,否則寧願不要效率和高樓大廈,他們重視的是“生命的整體感”。一個文明體系,就像一片山水樹林一樣,有自己的生命力。城市化不能把周邊的文化生態鏈切斷。
人物工作室:您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非常關注,在您看來,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哪個方面是關鍵點?
梁永安:現代化過程中,中國人的“現代性”發育為什麼會這麼難?這是我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有多種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比如,我們不接受荒誕。現在的世界不是農業社會中“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經驗主義總結,有時候出發點和落點完全不一樣。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變革的時代,不是形式邏輯所能左右的,否則就會陷入巨大的痛苦。世界的邏輯已經充滿了悖論,不像一個農民挖地,只要不偷懶就能收穫。現在的世界,可以説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時代。中國人要能夠接受荒誕。一旦我們能接受荒誕,在這個世界上就真正自由了。
還有,中國人在感受方式上不太接受悲劇。中國社會一直都稱讚成功者,缺乏悲劇意識,不敢接受一個失敗的人。如尼采所言,希臘藝術的繁榮不是源於希臘人內心的和諧,而是源於他們內心的痛苦和衝突。其實,悲劇的意義可能更深刻,可以證明生命的複雜和生存意志。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悲劇,再看歷史、看時代,我們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2000年,諾貝爾文學院曾經邀請54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位作家,推選“1000年”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品,結果《堂?吉訶德》以絕對優勢榮登榜首,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直至卡夫卡等文學大師的鴻篇巨制黯然失色。這個結果乍聽讓人驚詫,仔細想來,很有道理。那個瘦骨嶙峋的遊俠騎士,以十分荒誕甚至悲劇的行為,挑戰了人類精神層面的第一大難題: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一個老人,已經沒有多少力量的老人,一輩子讀騎士書,面對世界還敢飛蛾撲火地衝上去。我們身邊有多少人一輩子嚮往一個東西,但一輩子都不敢付諸行動?我們的時代太需要勇敢的探索者和挑戰者。美國3億人口中大學生超過半數 ,中國有13億7千萬,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僅12%,基本上還是初中生為主體的國家。但我們的青年有近5億,一千個年輕人中有一個敢於挑戰的堂?吉訶德,就不得了。頭雁出來後就會形成陣勢,就會有人跟隨。
面對現代化,中國還需要向前進發30年,這將是“人的建設”的30年,需要特別廣的實驗性。希望中國的青年一代不要過於現實和世俗,要敢於探索、不怕失敗。
“行萬里路”比“讀萬卷書”更重要
人物工作室:您是不一個不滿足於書齋的人,經常在國內外遊走,有的人覺得您“喜歡玩兒”。在您看來,在當代,“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的關係有什麼新變化嗎?
梁永安:我有一個理念:今天這個時代是一個文明變遷的時代。一個人既然生活在這個時代,就要多去深入歷史現場,行萬里路比讀萬卷書重要。過去的人把四書五經讀好,再輔以行萬里路,像顧炎武那樣,就能形成一個非常好的思想體系。今天這個時代完全不同,一方面有全球化的背景,另一方面還有我們國家從鄉村到城市的全面改變。
一個人一定要有時代感,要關注當下處在什麼歷史階段,社會處於什麼精神狀態,所做的事情應該跟這個時代有所呼應。如果想做一個文化健全的人,你就要與社會生活有盡可能多的連接,多到文化變化的現場去,才能看到這個時代的細節。所以我很重視文化人要“走出去”,國內國外都要去。生活的土地是一本更大的書,要傾盡全力去讀。讀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要把積累的一切生産化,把它寫出來,通過圖文甚至視頻表達出來。
因為有這份心願,這些年,我不大去名山大川,總是到文化變遷比較大的地方去攝影和寫作,新疆、雲南跑了很多次。在日本的三年教學工作中,我跑了很多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歷史現場,想理一理日本近代以來的變化過程。今年夏天,我又到當年知青時代去過的村寨,走訪了十多個村落,與傣族、傈僳族、回族、漢族、德昂族鄉民聊天拉家常,説實話,有種很吃驚的感覺,這裡生活水準的提高超乎想像。因此,我打算做一個項目,“多民族農村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從三代人的不同生活看我們四十年來的變遷,從老百姓的生存細微中看時代巨變。
這些年遊歷中,我形成了一個觀點:中國四十年以來的變化不能僅僅用“文化變革”來概括,而是一次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文明變遷”。文明變遷包含著多種文化內質,而不是用一種“先進文化”去同化其他文化。這是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大國的特點,而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是當下精神意識中最大的盲區。
人物工作室的話:
訪談之後,忽覺梁教授身上,有三點或是他的魅力之源——赤子之心、博學之士以及“自由而無用的靈魂”。
赤子之心——他仿佛就是一個用最為真摯的眼神打量世界的孩子。在很多文章與演講中,他都提倡“用自身的熱度讓世界更加豐富”、“用一顆真誠的心愛這個世界。”很多學生就是喜歡他孩子般的純潔、乾淨。一個作家,常常遊走在最冷漠的旁觀和最熱情的參與之間,在過程中,依舊保持著赤子之心,十分可貴。
博學之士——那些站在聽完他幾個小時課程的學生,原以為站著聽課很苦,但是,“他一開口,竟仿佛時間從此不再存在,宇宙就是一個講臺,每個人的思維都凝聚于一點”。在兩個小時採訪中,我也領略到他的博學。我個人對於東羅馬帝國較感興趣,教授得知,立即侃侃而談,他對東羅馬的了解十分深入,談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文藝復興的重大影響,以及由此引申到伊斯蘭文化對中西方交流的影響,都很有見地。難怪有學生説,“每聽一次梁老師講座,就更加覺得完全無法摸到這個人的深度和廣度”。
自由而無用的靈魂——這是復旦大學的民間校訓。何為“無用”?莊子點破了這層意思: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為之為,是為大為。梁教授向我們演繹了什麼是“自由而無用”,思想自由,淡泊名利,敢於抒發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小王子》有一句名言:這個世界上漂亮的臉蛋太多,有趣的靈魂太少。如此有著“有趣的靈魂”的梁教授,自然讓學生欲罷不能。(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宮梓銘,本文編輯:楊雪梅 周飛亞)
(責編:湯詩瑤、陳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