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代巨變中追尋中國科幻的“原力”

劉慈欣與他的《三體》資料圖片
回顧中國科幻的發展歷史可見,20世紀初在時代的巨變中,中國科幻從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類進步的夢想中汲取了“原力”,並融合了民族的英雄氣概和國際主義精神;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劉慈欣將之發揚光大,寫出了中國氣派的“星空浪漫主義”,激勵我們奮勇前行,也使中國科幻走向世界。在當前,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又將如何引發科幻藝術的新變?
那種不斷向上、追求進步的精神在哪出現,科幻的種子就會在哪生長
2020年即將結束之際,全球科幻迷聽到了一個悲傷的消息:美國時間12月23日,著名科幻作家、學者詹姆斯·岡恩去世了,享年97歲。岡恩編選的讀本《科幻之路》啟蒙了無以計數的讀者。早在1997年,該書就被譯介成中文,成為許多中國讀者了解世界科幻的重要指南。他的另一本著作《交錯的世界:世界科幻圖史》則系統地述説了科幻文學的由來與演變。該書初版于1975年,直到2020年才推出中譯本。儘管時隔45年,仍然令人激動。
岡恩出生於1923年,比世界上第一份專門性的科幻雜誌——雨果·根斯巴克創辦的《驚奇故事》還早了3年。他親歷了20世紀美國科幻文化的繁榮昌盛和起伏變遷,對那些重要的作品、雜誌、人物都十分熟悉,與不少聲名顯赫的作家、編輯更是交往深厚,因此能夠在講述歷史時如數家珍。另一方面,岡恩從1970年開始在大學講授科幻課程。《交錯的世界》正是以他的講稿為基礎修訂完成的,這使得他的敘述在確保學術水準的同時又能做到明白曉暢,與之相比,此前被譯介到國內的科幻史類著作多少都帶有一點學院派的深奧晦澀。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以中譯本的出版為契機,已經九十歲高齡的岡恩,又在原書的基礎上重寫了第一章、補寫了最後一章,並特別提到了《三體》英文版獲獎等近期事件,不但讓這本經典科幻史著作在結構上更為完整,也讓我們能夠透過科幻黃金時代親歷者的雙眼去審視近四十年來世界科幻的潮流。這樣的視角尤為寶貴,畢竟,與岡恩同代的不少科幻大師早已謝世(為本書第一版撰寫了序言的阿西莫夫早在1992年就已故去),可以説,近一個世紀的科幻風景,在岡恩這裡被整合成連貫而深厚的生命體驗。
在中文版序言中,岡恩開宗明義地指出:“科幻小説是變化的文學,其本身正是變化的最好例證。”圍繞“變化”這一核心概念,岡恩生動地描述了科幻的歷史:儘管古希臘時就已經有了對理想國的描繪、通過虛構旅行抵達奇異世界的故事,但在漫長的時期裏,人類的生産方式、生活態度、戰爭模式等都未發生實質性變化,直到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整個世界開始發生根本性的、加速式的變化,一種新的信念確立了——人類不需要依靠超自然力量,而是可以憑藉自己的理性,去探索未知,認識宇宙、自然和自我,通過自己的發明創造改變命運,以獲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在這種信念下,科技發明日新月異,極大地提高了生産力,不但取得了驚人的物質成就,也重塑了社會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面貌,“未來”取代了已然失落的“過去”,成為“黃金時代”的新坐標。這個極為重要的歷史變化,為科幻小説的誕生提供了基礎:
也許界定科幻小説的唯一標準是它的態度:科幻小説包含了這樣一種基本觀念,即宇宙是可知的,而人類的使命就是去了解宇宙,發現宇宙和人類從何而來,如何進化到今天的情形,宇宙和人類又將往何處去,是什麼法則在制約它們,最終一切的結局將會怎樣,又將如何結束。
換言之,不是先有了一批新穎的故事,世人才懂得了“科學幻想”,而是在一種渴望真理、勇於探索、推陳出新、朝向未來的整體氛圍中,科幻小説應時而生,這種因果關係被概括為一句話:“科幻小説理應被視為科幻世界的文學。”正因此,岡恩在勾勒不同階段的科幻發展時,尤其注重説明當時的科學成就及其社會影響。對於廣大科幻迷來説,這是理解科幻的關鍵入口,正是通過展示現代科技帶來的神奇變化和未來的無限可能,科幻為讀者提供了最主要的樂趣。這種樂趣被劉慈欣喻為“科幻的原力”,它能夠將一切幼稚、粗糙的故事催化成魅力無窮的精神食糧。可以説,岡恩的科幻史,正是一部“原力”的消長史。讀完這部歷史,讀者或許無法記住許多有趣的細節,但一定會留下一個強烈的印象:那種不斷向上、追求進步的精神在哪出現,科幻的種子就會在哪生長。
例如,19世紀層出不窮的新發明,讓凡爾納在歐洲登場。這位法國天才感受到了時代精神的召喚,成功地將科技成就變成小説的主題。他筆下那些令人憧憬的新發明,往往以前人已有的技術構想為基礎,能夠讓讀者相信未來確實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故事。儘管當時還沒有“科學幻想”這個概念,但凡爾納回應了歐洲人面對科學奇跡時的狂喜,也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成功。到了20世紀,永不滿足於現狀的科幻精神,在美國這塊新殖民地獲得了蓬勃的發展。隨著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崛起,隨著世界各地優秀人才向這裡的聚集和大眾對通俗讀物的需求增長,熱衷在科技時代探索未來奇景的出版人順應時勢,通過圖書和雜誌將有著共同愛好的作者與讀者聚集起來,由此促成了科幻的“黃金時代”。岡恩不無驕傲地寫道:“科幻小説誕生於法國和英國,卻在美國找到了自我。”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發源於英國、在美國得到響應的“新浪潮”運動,開始革新科幻的美學面貌,新一代作家廣泛借鑒了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敘事技巧,大膽開拓新的題材,包括對人的身體及其他私密領域的探索。在許多人看來,這些作品為了贏得“主流”文化界的認可而犧牲了故事的可讀性。岡恩卻指出,老派的科幻迷之所以抵制“新浪潮”科幻,根本原因不在於其晦澀艱深的文學技巧,而在於其視角的轉變:“新浪潮”作家放棄了此前的科幻文學那種從廣袤的時空尺度上審視人類命運、相信理性與科學能夠引領我們前進的態度,而將目光重新聚焦于當下的社會和個體的煩惱,並採取了主觀主義的、非科學的、“感覺比思考更重要”的視角。不論讀者對此抱持何種態度,時代精神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讓岡恩在初版的結尾總結歷史、展望未來時不無深情地指出,科幻的動人之處在於“一種既高傲又謙卑的哲學”。
可以説,岡恩對數百年科幻史的描述與把握,採用了完全純正的科幻迷立場,對科幻風尚的變化作出了頗有説服力的解釋,所以劉慈欣才稱許這本書是“目前國內翻譯出版的唯一一部從科幻的視角寫出的科幻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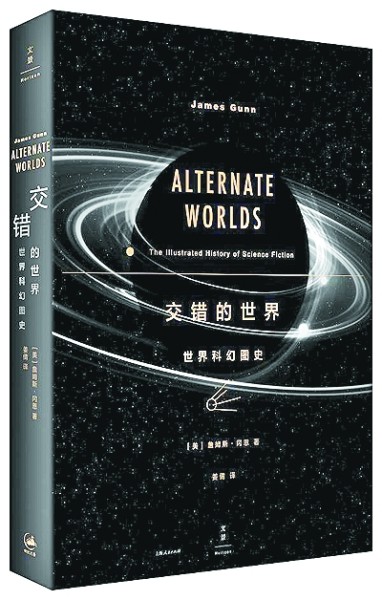
《交錯的世界》詹姆斯·岡恩著資料圖片
在時代的巨變中,中國科幻從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類進步的夢想中汲取了“原力”
當然,作為一本完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著作,《交錯的世界》也有其局限:它所涉及的基本上以英美科幻為主體。這或許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但也給今天的中國讀者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問題。書中的一段話令人感慨頗深:
到了1840年代,美國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們都已見證了工業革命的考驗和勝利,並接受了這樣一種社會理念,即科學會帶領人類走向嶄新的、更加美好的生存狀況。
在美國學者筆下,這是閃爍著金色輝光的歷史時刻:科技帶來的社會變化正在加速,整個世界都為科幻小説的到來做好了準備。但是,1840這個年份卻不可能不召喚起中國人的苦澀記憶。對我們來説,“渴望真理”“勇於探索”“推陳出新”“朝向未來”“理性精神的發展”,只是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的一層面向,而在故事的另一層面,探索未知疆域與殖民者的暴力征服緊密相連。也正是殖民主義為近代中國帶來的劇烈“變化”,促成了科幻在中國的生根發芽。
任何文明要持續發展,必然要不斷經歷自我肯定、自我保存與自我質疑、自我革新的往復,以實現延續與發展的統一。新舊文明的激烈碰撞也會帶來文學藝術的重要變化。當西方文明對科學技術帶來的巨變進行肯定與質疑時,科幻的“原力”也激蕩成兩個方向:對於“進步力”的讚揚(如凡爾納)和對於“毀滅力”的憂懼(如《弗蘭肯斯坦》),兩者的交織貫穿了科幻的歷史。
同理,中國科幻誕生於本土文明遭遇空前危機的時刻。19世紀,曾經的天朝上國顛倒角色,淪為落後國度,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西洋文明”中的“進步力”在落後國度面前變成了“毀滅力”,這勢不可擋的歷史動能向落伍者們拋出了自我保存與自我變革的平衡難題。一方面,否定傳統和激進變革的意志由此而來。在這場變革中,以現代科學為基礎改造國民的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成為重要的文化工作,同時“小説”的功用被拔高,於是“小説界革命”中自然出現了科幻小説的身影。在1902年的《新小説》創刊號上,主編梁啟超翻譯了法國天文學家弗拉馬利翁的《世界末日記》,講述了幾百萬年後人類文明逐漸凋零的故事。結合梁氏當時的宗教思想,可知他翻譯這篇科幻小説的目的是要展示天文學尺度上的末日圖景,讓國人能夠改變好生惡死的心態,放下對紅塵的貪戀,變得勇猛、剛毅,投身到舍生取義的大無畏事業之中,為拯救蒼生而獻身,肉身雖會隕滅,地球雖會滅亡,但靈魂和愛會在星空中永生。這種看法,呼應了以身殉道的好友譚嗣同,在後者看來,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隔膜造成了世間的不幸,通過“乙太”這個物理學家假定的無所不在、遍佈宇宙的介質,個人的至誠就能夠感動他人,衝破彼此的隔膜。英勇就義之時,他一定在期許自己的死亡可以激起更多人的熱血。他甚至還曾設想,既然人類進化不止,總有一天會擺脫肉體的束縛,變成純精神性的存在,在宇宙中遨遊。換言之,正是現代科學促成的三觀革命,賦予仁人志士舍生取義的勇氣。
另一方面,這種英雄氣概又和一種國際主義精神融合在一起:先覺者們不僅要挽救自己的民族,更要為人類的和平共存謀劃出路。24歲的梁啟超曾這樣表白:“我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這意味著,不但要以西方文明為鑒革新自我,也以自我的困境為切入點去思考西方文明的弊端,在東西互鑒中為人類文明尋求新的價值與方向。正因此,中國科幻從一開始就深受西方科幻的影響與啟發,同時也在模倣與改寫的嘗試中探索自己的道路。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被梁啟超改造成了聞名後世的“睡獅”,飽含“毀滅力”的文學形象竟演變為富於“進步力”的民族寓言,實屬陰差陽錯(學界早有考證)。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則讓賈寶玉重生在20世紀初的中國,曆盡社會黑暗之後進入科技發達、道德至善的“文明境地”,其中乘坐飛車、駕駛潛艇的部分明顯模倣、戲謔了凡爾納的故事,全景式的烏托邦描寫也有著愛德華·貝拉米《百年一覺》的影子,但作者的意圖絕不在於拙劣的模倣,而是要通過科幻小説這一新的文學方法,探討一個“真文明”世界應有的技術與道德水準,以此映襯和揭露列強在“文明”的假面背後恃強淩弱的本質。對此,曾翻譯過凡爾納的青年魯迅也深有感觸,後來的他雖然不再熱衷科幻小説,但在《破惡聲論》中對“黃禍論”的看法,也與同時代中國科幻小説裏不時出現的黃種人大敗白種人的復仇幻想構成了對比:如果未來中國能夠強大起來,不應重走列強的老路,而應去扶助弱小,使他們擺脫奴役、獲得自由。
簡言之,近代中國雖然飽受欺淩,但在頑強的求生意志下,産生了奮發圖強的精神和英雄主義氣質,這種精神和氣質又受到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的激勵,化作對美好未來的信念和為信念犧牲的勇氣。20世紀初的中國科幻也正是在時代的巨變中,從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類進步的夢想中汲取了“原力”。當然,科幻文藝的繁榮終究要以綜合國力作為堅實基礎,法、英、美、蘇、日等國的科幻發展中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直到20世紀末,才出現了通過《鯨歌》登上歷史舞臺的劉慈欣。2006年,《三體》開始連載。2010年,《三體》第三部《死神永生》出版,開始在科幻圈外引發轟動。從1999年到2010年,這是劉慈欣個人成長的階段,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階段,是中國高校開始擴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基數逐年增長的階段,也是城市化進程持續推進並最終在2011年首次實現城鎮人口比重過半的階段。正是這樣的歷史變化為中國科幻的蓄力提供了能量,為《三體》的成功奠定了文化土壤和群眾基礎。在“變化”與“原力”的視角下,我們能夠發現劉慈欣的故事裏蘊藏著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苦悶與追求,它們挑動著一個民族內心深處的焦灼與渴望。
首先是強烈的進化壓力與生存焦慮。多年來,這位長期居住在山西娘子關的工程師小説家一再表達對於科學探索尤其是基礎科學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期待,對於人類不能永遠停留在地球而必須進入太空以獲得更廣闊生存空間的信念,對於在極端條件下為保全整個文明而必須採取諸多反道德直覺之舉的擁護。在《鄉村教師》裏,罹患絕症的老師在臨終之際仍在要求懵懂的孩子們背下他們不能理解的牛頓力學三大定律,出人意料的是,神一般的外星文明在清掃戰場時鑒定著沿途行星的文明等級,被隨機抽作地球樣本的孩子們面對一系列測試題時無動於衷,直到正確答出了牛頓定律,才證明了地球值得保存。以奇異的方式,作家再次道出了文明降級後失去生存資格這一久遠的憂慮。有趣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商務印書館翻譯的凡爾納小説《環遊月球》中,就已提到日、地、月的運動屬於“三體問題”。在原著的另一個譯本《月界旅行》中,譯者周樹人在序言裏曾推測人類如果能夠殖民外星,恐怕“雖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戰禍又起”。從魯迅到劉慈欣,對生存與滅亡的思考始終位於百年中國科幻的核心。
其次是通過超感官衝擊促成三觀改造,完成文化的革新。年輕時第一次讀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遊》後,劉慈欣感到一種“對宇宙的宏大神秘的深深的敬畏感”。在他看來,科學描繪的宇宙圖景遠比科幻小説震撼,科幻作家只是通過小説把這種震撼“翻譯”出來,傳遞給讀者。在隨筆中,他説希望通過科幻讓忙忙碌碌的眾生能停下匆忙的腳步,仰望星空,感受宇宙的浩渺。在小説中,他試圖用現代漢語展示宇觀尺度的事件,讓我們有限的個體經驗和喜怒哀愁在超感官的衝擊中得到洗禮。在最極端的《朝聞道》中,科學家甚至願意以生命為代價,換取認識科學真理的十分鐘。在歷史的參照系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位經常描寫地球末日、太陽系末日乃至宇宙末日的當代作家,和20世紀初翻譯《世界末日記》的梁啟超一樣,也試圖通過文學的工作來推動民族精神的更生。
不過,儘管劉慈欣的故事看起來很黑暗,人類在宇宙面前看來微不足道,但又因為能夠認識到“真理”而偉大,因進取而崇高,因失敗而悲壯。這種悲壯,正是人類生存意志和種族尊嚴的表達,因此營造了一種英雄主義氣氛。這在《流浪地球》中體現得尤為鮮明。太陽系演變為紅巨星的災難,本應幾十億年之後才發生,小説家卻讓其極速降臨,於是在危機和解決危機的手段之間造成了極大的不匹配:人類在地下世界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只為能夠驅動地球離開太陽系,以如此笨拙的方式來逃亡。茫茫冰雪覆蓋的地表上,巨大的工業體系艱難維持運轉,標示著人類的國際合作精神與頑強抗爭意志。
總之,劉慈欣小説對生存的焦慮、對進化的執著、對科學的崇拜以及對人類團結合作謀求文明延續的憧憬,正是近現代中國核心命題在星際尺度上的再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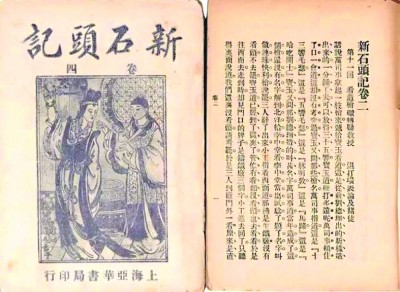
清代吳趼人的科幻小説《新石頭記》資料圖片
劉慈欣把民族的英雄風骨投射到未來的時空裏,寫出了中國氣派的“星空浪漫主義”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了不起的人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跡,通過歷史記載和文學藝術的演義,成為代代相傳的集體記憶,塑造了人們對於中華民族的理解和情感。比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是壯士悲歌;比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是盛唐氣象中的文人風骨;比如義薄雲天、不畏豪強的關雲長,是普通人對於忠義的寄託;比如“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是為了保衛家鄉而不惜流血犧牲的勇氣,是為了建設家鄉而改天換地的氣魄,也是敞開家門迎接四方來賓的氣度,更是對世界和平的美好期待。所有這些故事澆灌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培育著民族自豪感,在困難的時代激勵我們奮勇前行。劉慈欣小説的魅力之一,就在於把這樣一種英雄風骨投射到了未來的時空裏。
如果説,在20世紀的中國大眾文藝譜系裏,金庸塑造了一系列古代中國的英雄,是一種“歷史浪漫主義”,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塑造了一系列現代中國的英雄,是一種“革命浪漫主義”,那麼劉慈欣就是塑造了一系列未來中國的英雄,是一種“星空浪漫主義”。有一段時期,好萊塢電影讓我們習慣了美利堅的黑白英雄拯救世界的敘述,直到《三體》的出現。通過恢弘的設定、龐大的骨架、複雜的情節,劉慈欣摹畫了一組未來人物群像,其中有史強這樣強悍粗魯、狡黠命硬的警察,有章北海這樣冷酷果決、縝密隱忍的太空軍政委,也有觸發危機的葉文潔和力挽狂瀾的羅輯。這些人物在命運攸關之際的抉擇,讓讀者津津樂道、爭論不已,像談論赤壁之戰一樣談論地球的太空艦隊如何被三體人的“水滴”探測器輕易摧毀,像談論荊軻刺秦一樣談論章北海為了扭轉未來太空軍的發展方向如何精心策劃太空暗殺,像談論蕭峰為了宋遼息兵而自盡于雁門關外一樣談論羅輯如何在荒郊獨自向三體人喊話並以自殺威脅迫使對方放棄侵略以免兩個物種同歸於盡。正如金庸的成功不僅是因為他熟諳傳統文化,更因為他寫出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劉慈欣的成功也不僅在於他奇異而宏大的技術想像,更因為他寫出了中國氣派的星空浪漫主義,通過激動人心的虛構時刻,將我們對古代、現代和未來的中國英雄的想像勾連在了一起。由於高等教育的普及與全民科學素養的提升,同時也由於科技的發展使得不少過去的科幻場景正在變成現實,今天的人民大眾對科技話題的興趣日益濃厚,對太空時代的人類命運也更加關心,劉慈欣為這樣的讀者講述了古老農耕民族的覺醒和新生,譜寫了人類在太空時代的光榮與夢想。
當然,這絕不是説,劉慈欣的作品是完美的。相反,如果以最高的藝術標準來衡量,他的小説有著顯而易見的不足。這很正常。在由遠古的神話、莊子的寓言、屈原的賦、李白的詩、東坡的詞等所構建的華夏文學長河中,偉大而浪漫的心靈雖然一次次奏響過生命的律動,創造了眾多不朽的篇章,但如何用現代漢語去表現科學革命之後的時空之廣袤、探索之艱辛、定律之奧妙、技術之恢弘,抒發現代中國人的豪邁和悲憫,則是一個多世紀前才出現的全新任務。劉慈欣的作品,只是中國作家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探索之後取得的階段性成績,有其里程碑式的意義,但也映襯出中國科幻整體實力的相對單薄。
在當下,還需要思考這些問題: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如何引發科幻藝術的新變?在科幻與現實的對照下,中國的科學幻想,該如何理解自己的當下處境,思考未來的出路?下一個能夠切中時代脈搏、道出人們內心深處的憂患與憧憬的作品會是什麼樣子?當開闊的胸懷、進取的豪邁、大無畏的勇氣、為追求真理和為人類福祉而奉獻的決心等曾經推動科幻走向輝煌的核心精神在全球諸多角落呈現凋萎之態時,我們是否還能充分汲取現代文明成就中的“原力”,實現民族精神的茁壯成長,進而在人類進步的道路上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願我們勉力前行,並用岡恩的這段話不斷提醒自己:
科幻小説就像是來自未來的書信,寫信人是我們的後代,敦促我們小心保護他們的世界。
(作者:飛氘,係科幻作家,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似是故人來
似是故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