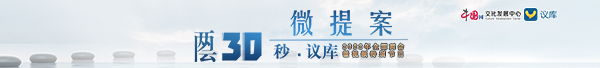音樂與中國古代詩歌
主講人簡介:
趙敏俐,首都師範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中國樂府學會(代)會長、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早年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獲博士學位,師從著名文學史家楊公驥教授。主要科研方向為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中國古代詩歌、中國現代學術史。主要著作有:《兩漢詩歌研究》《文學傳統與中國文化》《周漢詩歌綜論》《先秦君子風範》《漢代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等,主編《中國詩歌史》《中國文學通論·先秦兩漢卷》《文學研究方法論講義》《中國文學研究論著彙編》等數10部,發表論文100余篇。其科研成果獲得過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等多種獎勵。
編者的話: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音樂,與中國古代詩歌有著緊密的關係,特別是先秦兩漢時期的《詩經》、楚辭與漢代詩賦。《尚書》中有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由此可知,這一時期的詩歌與音樂幾乎不分,可謂“詩為樂心,聲為樂體。”為此,音樂對中國古代詩歌的形成、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本期講壇邀請趙敏俐教授以先秦兩漢詩歌為例講述音樂與中國古代詩歌的關係。
詩樂同源,中國古代最早的詩都是可以歌唱的,有些甚至是配合舞蹈表演的。《尚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禮記·樂記》曰:“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些論述,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古代詩歌與音樂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但是,由於時代技術的原因,古代詩歌的音樂表演形態沒有保留下來,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古代詩歌,僅僅是它的文字部分。這使得後人在學習和欣賞古代詩歌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它的音樂形態。古代的音樂雖然不存,可是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生發展曾經産生過重大影響卻不能否認,有些至今仍然沉積在詩歌文本中。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古代詩歌,不能因為音樂表演的形態不復存在而忽視了這種影響。通過現存的歷史記載,可以儘量做一些歷史的還原,更好地探求中國詩歌的藝術本質,也會增強我們對古代詩歌藝術的理解與鑒賞。
音樂與《詩經》
《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本身就是詩樂一體的藝術。《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最初就是音樂的區分而不是文體的區分,《左傳》記載吳季札到魯國觀樂,魯國樂工為他分別演奏了各國的《風》詩、大小《雅》和《頌》,就是最好的證明。孔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可見,孔子曾經整理過《詩經》,他的工作就是從“正樂”開始的。因為有不同的音樂,用於不同的場合,自然這些音樂也就會有不同的風格,表現不同的內容。到了漢代以後,由於音樂的失傳,後人才從詩歌內容角度來對《風》《雅》《頌》進行解釋。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説:“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他講的正是這個道理。
《詩經》的音樂雖然不存,但是它對《詩經》藝術形式的影響還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章法上來看,《周頌》裏的詩,幾乎都以單章形式出現。《雅》詩都由多章構成,《風》詩雖然也由多章構成,但是大多數《風》詩的章節數都少於《雅》詩,每一章的篇幅也較《雅》詩要短。這種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現象,顯然都是由《風》《雅》《頌》這三種不同的音樂演唱體系決定的。再從文辭的角度來看,《周頌》裏的詩句有相當數量都不整齊,詞語也不夠文雅,但是大多數卻非常古奧。而《雅》詩的句子則整齊規範,詞語也特別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風》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通俗又是其語言的基本風格。這些不同,也與其演唱方式不同有直接的關係。
關於《詩經》的演唱,歷史上有許多記載,我們結合具體作品,還可以從中發現由此而形成的藝術形態的不同。如《周頌·清廟》一詩,從文本來看,句式既不整齊,也不押韻:“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似乎缺少詩歌藝術的美:可是,古人卻把這首詩排在《周頌》的第一篇,認為這是專門用於祭祀周文王的祭歌,地位特別高。祭祀周文王的祭歌叫做“清廟”,取其“清靜肅穆之意”。《禮記·樂記》對《清廟》的演唱有這樣的記載:“《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也。”孔穎達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他説:演奏《清廟》的瑟是經過特製的,它染紅的絲弦是經過煮熟的,所以發出的聲音很濁重。瑟底的音孔距離比較大,也是為了使它發出聲音變得遲緩,“一倡”是指一人領唱,“三嘆”是指三人或者很多人跟著合唱。假如我們把這個演奏的場景在腦海中簡單的復原,或者將其想像成佛教寺院或者基督教教堂裏的宗教歌曲演唱,回過頭來再看《清廟》的文辭,它以敘事描摹為主,一句一層意思,用簡潔的語言展示了祭祀活動時的場景和人物的神態,再配上一唱三嘆而又遲緩濁重的樂調,多麼符合當時的祭祀表演,一定也是莊嚴肅穆而感動人心的。
《詩經》中的《雅》詩語言最為典雅,形式最為整齊。因為它們最初大概都是用於各種朝廷禮儀。所以,高雅、雅正、文雅等等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詞彙,一直傳承至今。《大雅》中那些歌頌祖先功業的詩篇,如《文王》《皇矣》《大明》《生民》《綿》等詩篇場面宏大,氣勢非凡,甚至如《板》《蕩》那樣的諷諫詩也有典雅高嚴之氣。而《小雅》中的一些燕饗詩則盡顯優雅從容之美。如《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據説,這首樂歌最早用於周王宴享群臣,後來被廣泛用於周代貴族社會的宴饗禮儀。全詩三章,首章以林野間的鹿鳴起興。鹿的性情溫和,被古人認為是仁義之獸,據説鹿如果發現豐盛的肥草必呼伴共食。詩人用以為比,説明主人若有好的酒食,也一定會與嘉賓共用。他不但以鼓瑟吹笙的方式歡迎嘉賓,送上禮品,表達了主人對嘉賓之愛,同時也希望能得到喜賓的惠愛,為自己指明做人的正道。二章重點寫嘉賓有美好的品格。三章寫宴飲場景的快樂。賓主之間就在這種互敬互愛、和樂融洽的氣氛下宴會暢飲。全詩語言文雅,韻律和諧,情調歡快,韻味深長,鮮明地體現了周代社會的禮樂文化精神。這首詩整體的藝術之美,我們也只有放在周代特有的禮樂文化中才能體悟。
而《詩經·國風》則是世俗的“歌”,內容的世俗化和詩體的簡潔明快是它的最大特色。在此我們以《周南·芣苢》為例略作分析:
采采芣苢,薄言採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這雖是《詩經》中形式最簡單的詩歌之一,但卻深受人們喜愛。清人方玉潤説:“讀者試平心靜氣,涵咏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為什麼一首如此簡單的詩,讀者會生發出這麼美好的藝術聯想呢?就因為這首詩不同於文人的案頭之作,充分體現了“歌”的特點。我們看這首詩雖然有三章,卻用的是一個曲調。因為有了曲調的重復,於是就有了語言的重復。同時為了歌唱的方便,這首詩還用了歌唱時常用的套語,實際上只是“采采芣苢,薄言×之”這兩句套語重復了六遍。那麼,在這種不斷重復的演唱中,詩又是如何進行修辭煉句的呢?原來詩人採用的是置換中心詞語的方式。這首詩描寫的是採芣苢的勞動,所以詩人在詩中只換了六個動詞,“採”“有”“掇”“捋”“袺”“襭”。《毛傳》説:“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以手輕握植物的莖,順勢脫取其子);“袺,執衽也”(手兜起衣襟來裝盛芣苢);“扱衽曰襭”(採集既多,將衣襟掖到腰間)。那麼,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孔穎達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解釋:“首章言採之,有之。採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採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盛之處,或袺之、或襭之,歸則有藏之。”原來,就是通過這六個動詞的變換,就把採芣苢的整個勞動過程生動地描寫了出來,由此才會引發讀者的聯想。這就是歌的藝術,也是《詩經》不同於後世詩歌的獨特之處。可以説,如果不從音樂的角度入手,我們是很難體會《詩經》藝術之美的。
音樂與楚辭
音樂與楚辭的關係也十分緊密。我們讀楚辭,會發現楚辭各體的形式大不一樣。那麼,這些詩體是如何形成的呢?原來也和音樂有關,關於楚辭詩體的類型,我們也需要根據它與音樂關係的遠近來認識。
楚辭中和音樂結合最緊密的是《九歌》。從題目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它是用於歌唱的。《九歌》的形式源遠流長,傳説它特別好聽,最早是夏啟從天上偷下來的。《山海經·大荒西經》:“開(啟)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楚辭章句》中説,過去在楚國的南郢之邑和沅湘之間,民俗信鬼神而好祭祀,祭祀一定伴有歌樂舞鼓,用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心懷憂苦,愁思沸鬱,看見俗人祭祀之禮和歌舞之樂,歌詞鄙陋,於是就據此而改作《九歌》之曲。王逸本是南方楚地人,他的説法可能有歷史根據。當然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九歌》所祭祀的諸神有些不應該出於楚國當時的南方民間,而應該是楚國的宮廷祭歌或者郊祀祭歌。但無論哪種説法,都不否認《九歌》的歌唱性質。《九歌》的歌辭也與楚辭其他詩體不一樣,每兩句一組,每句中間都有一個“兮”字,如《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的確有特殊的搖曳多姿的韻味。
第二類是《招魂》,也屬於當時一種特殊的歌唱文體。按王逸的説法,《招魂》是宋玉所作。宋玉哀憐屈原的遭遇,見其因為忠君反而被貶斥,憂愁山澤,魂魄放佚,生命將落。於是就作《招魂》,希望能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但是也有人認為這首詩是屈原招楚懷王之魂。因為楚懷王被騙入秦,客死他鄉,於是屈原招其魂魄。兩説雖有不同,但是詩中所寫的確是招魂之事,所用詩體也是當時招魂特有的語言形式。它是一種特殊的、呼喊式的歌:“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
第三類是《離騷》體,包括《九章》《九辯》。《離騷》為屈原的代表作品,它是屈原用生命寫成的詩篇。《離騷》體是從《九歌》體轉机化而來,它也是兩句一組,但並不是在每句中間有一個“兮”字,而是在第一句的末尾有一個“兮”字,如開頭四句:“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關於《離騷》是否可歌,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離騷》的結尾有五句“亂”辭,“亂”指音樂結尾,這説明它與音樂有關。但是據《漢書·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咏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可見漢人認為它是賦體。何謂賦?班固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何謂“誦”?“以聲節之曰誦。”可見,《離騷》是從歌中演化而成,用一種“以聲節之”的特殊方式誦讀的文體。
第四類是《天問》體。《天問》何由而作?據王逸所説:“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徬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可見,屈原的《天問》是詩人在宗廟祠堂中呵壁而問的書寫,它雖然以四言為主,有詩的形式,但以問句構成,不可能用於演唱,也不會用於誦讀。其開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全詩由170多個問題構成,上問天,下問地,中間問歷史和人事,它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歌唱的旋律,而是來自於深刻的哲思。
楚辭中還有《卜居》《漁父》兩篇,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對話體。它不但不能歌唱,也沒有如《天問》那樣的詩體韻味,已經完全變成了散文的形式。由此可見,在中國詩歌史上,楚辭的産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從此,中國詩歌和音樂的關係出現了分離,逐漸産生了一種遠離音樂的詩體。這種現象,到漢代更為明顯。
音樂與漢代詩賦
詩賦在漢代本是一家,它們之間的區別只在於口頭表達形式上的差異,“詩”在漢代又叫“歌詩”,仍然是可以唱的,“賦”則是“不歌而誦”的。所以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將二者放在一起叫“詩賦略”。
漢賦從大的方面來看可以分成兩種體式。第一種體式是騷體賦,以屈原的《離騷》等為原型。如傳為賈誼所作的《惜誓》:“惜餘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它的句式仍然為兩句一組,每組第一句的末尾有一個“兮”字。它不但從句法形式上和《離騷》一樣,連抒情模式也相同,可見這一類賦與《離騷》一樣,還深受音樂的影響。
漢賦的第二種體式是散體賦,它和屈原的《卜居》《漁父》有直接關係,往往以散體的對話方式開頭,接下來會有鋪陳的描寫。如宋玉的《神女賦》,寫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楚王果然在夢裏與神女相遇,於是,這篇賦就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並且有對神女容貌的鋪排描寫。其後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的散體大賦都是在此基礎上的發展,變成了完全和音樂沒有關係的一種文體。
而漢代的歌詩則繼續沿著與音樂相結合的道路發展,産生了三種主要體式。它們的分別最初不是由於文體上的差異,而是來自於不同的音樂樂調以及與之相關的演唱方式。
漢代歌詩的第一種形式是楚歌體,它主要繼承了《九歌》的藝術形式。每兩句一組,每句中間有一個“兮”字。如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項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和劉邦都是楚人,所以他們唱起楚歌來得心應手,也深得楚歌之奧妙。由於劉邦是楚人,愛楚聲,所以楚歌在漢代初年特別流行。漢武帝劉徹也是楚歌高手。他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由自然季節之秋而聯想到人生之秋,藉以抒發人生短促的生命感慨,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名作。楚歌后來逐漸衰微,但是終有漢一代,仍然一直在傳唱。
漢代歌詩的第二種形式是鼓吹鐃歌體,本是來自於異域的音樂歌曲形式。細分又有鼓吹和橫吹之別。劉瓛《定軍禮》雲:“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班固《漢書·敘傳》説:“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後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班壹是班固的先祖,他的記載是可靠的。可見,鼓吹最初起源於北狄諸國,是北方少數民族的音樂。而橫吹則來自於西域。《樂府詩集》曰:“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節,乘輿以為武樂。”可見橫吹曲是來自於西域的音樂。現在傳世的《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就是鼓吹音樂的存留。其代表作如《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戰城南》:“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嚎。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仔細比較就會發現,《漢鼓吹鐃歌》十八曲在詩體形式上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不同於《詩經》以四言句式為主,也不同於楚歌有以“兮”字嵌于每句中間的固定句式,它們完全是雜言的形式,每首詩都不一樣。可以這樣説,中國古代雜言詩成為一體,是從漢代的橫吹鼓吹開始的。不僅它們在詩體形式上與傳統的中國詩歌不同,在藝術風格的表現上也有差異,如我們上引的《上邪》和《戰城南》,感情表達的激烈和想像的奇特,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此,陸機的《鼓吹賦》有過生動的描述。
而相和歌則是漢代新興起的一種新的歌唱藝術。《晉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以絲竹作為兩種主要的樂器來演奏,唱歌的人手中還拿著“節”這種樂器伴奏,這與鼓吹和橫吹曲大不相同。《宋書·樂志》:“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可見,相和歌最初起源於漢代的民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南可採蓮》等幾首名曲。它最後流入宮廷,又有較大的發展,形成眾多的相和歌曲調。有“相和六引”“吟嘆曲”“四弦曲”“平調曲”“清調曲”“楚調曲”“瑟調曲”“大曲”等,演唱方式非常複雜。《樂府詩集》曰:“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七種。”“又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如此複雜的演唱方式,説明它們從一開始就屬於專門用於表演的藝術。我們現在流行的説法把這些漢樂府詩稱之為“漢樂府民歌”,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它們與當時真正流傳於民間的歌與謠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只有結合漢代社會的實際表演情況,才能對這些樂府詩進行準確的解讀。如我們非常熟悉的《陌上桑》,就是一首典型的樂府詩。它是時尚文化的産物,是漢代的流行藝術而不是民間藝術。《陌上桑》是歌,它的文本是按照歌的表演需要而寫成的,它採用了片斷敘事、場景敘事等藝術手法。
要而言之,從《詩經》中《風》《雅》《頌》的區別到楚辭的各類詩體,再到漢代詩賦的分流以及楚歌、鐃歌與相和歌的産生,我們可以看到音樂與中國古代詩歌的關係之大。這要求我們學習和欣賞中國古代詩歌,一定要考慮它們和音樂的關係。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對其做出正確的藝術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