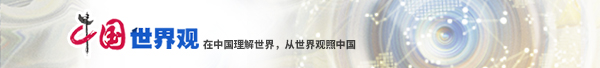中國古代為政智慧探微
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在漫長政治實踐中積累了豐厚的為政智慧。這些智慧將成為我們今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
循道。道是萬事萬物之源,也是為政之源。為政之緒萬端,一以貫之者,循道而已,其他所有活動均應循道而為。道法自然,人法天道。如果説自然之善在萬物生生卻縱橫交錯而無隔閡,那麼,國家和社會之善則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縱橫交錯而無隔閡,引導人向善。凡為政者,必本於此法而求乎斯境。所以,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莫不重視為政之道。例如,荀子就強調,只有得道以為政,方能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反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甚至有之不如無之。那麼,究竟該如何循道而為政呢?概言之,道主一陰一陽,政貴寬猛相濟,也就是孔子講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強調的是仁、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猛,強調的是制、法,所謂一民之軌,莫良于法。但是,強調仁、德,並不是毫無原則的仁慈包容。仁,如司馬光所講,人君之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而是要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強調製、法,也不是一味的嚴刑峻法,而是在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的基礎上,做到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寬猛相濟,也就是文武兼重,但其運用要因時因事有所側重,不能簡單化。漢高祖劉邦剛剛得到天下時,陸賈經常在他面前説起《詩》《書》,這位草莽出身的皇帝就不高興,説:“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就給他講,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這才是長久之術,再説秦,如果其法先王、行仁義,你還能得天下嗎?劉邦一下子被點醒了,他就讓陸賈把秦以及過往各國成敗原因總結一下給他看,結果陸賈就寫了十二篇,高祖每聽奏一篇都稱善。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敗亡的原因,“仁義之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也。”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秉公。公是道的本質規定,秉公是循道為政的自然要求,是為政的魂之所在。公的一般含義,如武則天所言,是“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無私為,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公在為政方面的理想樣態,就是《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同”境況: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他皆有所養等等。秉公為政,從人君的角度講,就要像堯、舜那樣,明于公私之分,其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就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一事,明確地講: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舊異情?還批評房玄齡説:你今天不論其能與不能,就直言那些人的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秉公為政從人臣的角度講,就要做到理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貸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人臣秉公為政的最高境界是公而忘私,如《康熙政要》所説:為清官者惟潔己不要錢,猶是易事,若論公而忘私,誠為難得。
重民。民是為政之本,重民是循道為政的自然要求。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早就認識到民之於政的極端重要性,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後來逐漸有了較為系統的認識,例如賈誼就明確論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得民心者得天下”。漢代劉向曾講到齊桓公和管仲的故事,説桓公問管仲“王者何貴”?管仲回答説“貴天”,桓公就“仰而視天”。結果管仲告訴桓公説: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宋朝的石介進一步指出,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那麼,實踐中如何得民心而不失民心呢?孟子的回答言簡意賅: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惡勿施爾。這具體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開源富民、簡行利民、節用愛民、因時使民、裁力取民等等。管子説: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憂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誠哉斯言!另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曾與大臣們議論如何止盜,有人建議太宗用重法禁之。但太宗認為,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我應該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部為盜,安用重法耶!
用人。人為天下之極,用人乃為政之要,所以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高度重視人在為政中的重要作用。這種重要作用,關鍵在於人才關乎天下得失。據《史記》所載,劉邦當了皇帝後,有一次跟大臣們論起為什麼是他而不是項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等人從“利”的角度做了應對,説陛下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但劉邦卻認為他們的説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進一步説道:要論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這裡講的,就是人才在得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人才在治理天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唐朝時,憲宗李純曾問宰相崔群,玄宗李隆基之政為什麼先理而後亂。崔群就回答説,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崔群的這番話,充分道明瞭用人在治理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用人智慧內涵非常豐富,包括人才常有而患不識,識人重在聽其言觀其行,用人應德才兼備、因才使用、用之不疑等諸多方面。關於人才常有而患不識,唐代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之不常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關於識人重在聽其言觀其行,《呂氏春秋》中的“八觀六驗”,論得極為精到。所謂八觀,即“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氣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所謂六驗,即“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關於用人應德才兼備、因才使用、用之不疑,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説起“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時,魏徵回答説:“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懼兼,始可任用。”論的就是用人方面的德才關係問題。宋朝司馬光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最為鮮明,主張“取士之道,當以德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明朝高拱所論是較為週全的,他説:“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均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備之人,而闕其一者,斷不可以為也。”
憂患。患,無論其顯或隱,都如影隨形與歷朝歷代相伴。憂患,自然就是為政者必須內具的一種自覺,或為政的一種心態。古之聖王,莫不常懷此心。孔子就講: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常懷憂患意識,就要謹其始,慮其終,明察秋毫,防微杜漸。墨子提出“國有七患”: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交,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墨子這七患,足以令所有為政者警醒。《明太宗實錄》中也有很中肯的告誡:亂生於治,何也?非治能生亂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亂生於所忽也。是故,天下雖有磐石之安,當常懷隉杌之懼。守滿持盈,居高思危,謹其始,慮其終,則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常懷憂患意識,就要以史為鑒,深明治亂興衰之理。漢朝賈誼對此有精闢之論,他説: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人之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探究中國古代為政智慧,目的是使其成為新時代的為政之資。清朝王夫之説: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故論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縣于室,無與炤之者也。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為政也必須“循道而為”,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立足於“人間正道”;必須堅持公權力姓公,決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確保人民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來考核、使用領導幹部;全黨同志必須時刻居安思危,以史為鑒,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業長治久安。
(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