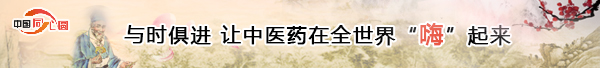他們敘述著中國的故事

圖為2019上海寫作計劃駐市作家與上海本地作家交流。資料圖片
核心閱讀
因為上海寫作計劃,每年總會有一批海外作家不遠萬里,住在居民小區,正兒八經在上海生活兩個月。街巷里弄的煙火氣、歷史遺存的厚重感、海納百川的國際范兒……作家們在這座城市行走體驗,將他們的感受匯入上海的故事,又將這裡的故事帶到各地,讓當下中國更真實地進入世界視野。
對著一張張不同膚色、不同發色,但無一例外有點兒迷惘的臉,作家陳村關照道:“希望大家能夠在上海過得愉快,玩得高興。”
他面對的是11位來自波蘭、義大利、英國等國的海外作家。因為上海寫作計劃,在剛剛過去的秋季,他們扎紮實實在上海生活了兩個月。“我很感激上海寫作計劃,它讓我能夠重新思考寫作之於我的意義。”2019上海寫作計劃駐市作家、俄羅斯作家圖盧西娃·埃蓮娜説。
從三五人到一百人,寫作計劃交到了更多朋友
2008年,上海寫作計劃正式啟動。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的3位女作家成了第一批參與者。“非常感謝她們,能夠注意到這個計劃,當時連我們自己都沒有信心呢。”作為上海寫作計劃最重要的倡導者,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王安憶這樣形容,“雙方都帶著怯意,還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熱的7月和8月的季節裏,拘謹地度過駐市時間。”
第二年,來了5位作家,時間也推遲到了天氣涼爽的9月和10月。寫作計劃,逐漸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就像水衝出閘門,事情變得順利起來。
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的上海寫作計劃,自2008年起接受國外作家申請,一批批外國作家,通過文學機構、使領館、出版社推薦或作家互薦、自薦等方式,經過審核、了解、篩選,最終獲得駐滬寫作生活的機會。12年來,已有100位來自38個國家的作家應邀駐市。他們成為遍佈全球的紐帶,連接起上海與整個文學世界。
舉辦上海寫作計劃的初衷並不複雜。王安憶曾參加美國一所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從那時起我就想,我們中國能不能有自己的寫作計劃呢?”
時任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的作家孫顒回憶,“當時我和王安憶説,如果可以堅持10年,定能産生一些影響力。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在不同的文學視野中會煥發出更多光彩。”
就這樣,上海寫作計劃逐漸成形。創辦伊始,王安憶曾自嘲,在全世界的“寫作計劃”中,“當初我們大概是最年輕無名的一個。”但上海寫作計劃有自己的特色——注重“駐市”概念,希望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們不僅是做客,而是能夠有充裕的時間進入上海生活的“芯子”裏,做一回實實在在的上海人,希望在上海的生活經驗,能夠成為駐市作家寫作的養分。
生活在街巷里弄中,認識一個日常的上海
寫作計劃曾嘗試邀請著名作家。然而,面對個別作家入住五星級酒店的要求,還是放棄了。“這違背我們的初衷,我們不是打造旅遊地,而是希望外國作家們生活在市民中間,認識一個日常的上海。”上海寫作計劃總協調人、上海市作家協會對外聯絡室主任胡佩華説。
印度的作家來了,俄羅斯的年輕詩人來了,非洲作家帶著她的鼓來了……他們在上海這座巨大的城市迷宮裏,經歷著各自的傳奇。
寫作計劃為海外作家們安排的是民居公寓,身邊就是十足的煙火氣。從窗口可以聽見市井聲,油鍋的香味飄進來;探出頭去,底下是店舖、車站、地鐵口;早上是晨練的人群,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媽的廣場舞開始了……
愛好書法的匈牙利作家,從居住的城西,直接徒步走到了城東,許多上海的年輕人都未必知道那裏有許多舊書店,還有文具店,他買了一大包宣紙,再汗淋淋地走回來。
“我在上海的公園裏學習太極拳,讀我的故事。我目睹有人用水在地上大筆揮寫中國文字。我在那跳舞,在那閱讀。”2011年駐市作家、墨西哥作家克裏斯蒂娜·瑞斯康·卡斯特羅回憶。
“我還發現自己有點對電視裏新聞和天氣預報的主題曲上癮了。”2016年駐市作家、美國作家麗薩·提斯利説。
有兩位北歐作家,認定朝東走去一定能走到東海,於是一路向前,走到銅川路的水産市場,以為是漁人碼頭,方才折返回頭。就這樣一直走,有一次走進劇場,臺上正演中國京劇;又一次走到一座古典園林,上演的卻是西方現代劇。期然和不期然的畫面,就這樣走到各國作家們的身邊……
作家們對上海、對中國,開始有了新的認識。“我來自人口不足500萬的紐西蘭。對我來説,聚集近2500萬人口的上海是無法想像的。”2016年駐市作家、紐西蘭作家海蒂·諾斯·貝利説,“但上海也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有著不可預測、引人深思的美。”
從陌生到熟悉,從新奇到日常,作家們突然意識到,兩個月的時間是那麼短暫。麗薩·提斯利説:“隨著我們的活動漸進尾聲,我感受到一種離別的隱痛,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把上海當成自己的家。”
沒有硬性創作要求,卻收穫更廣闊的書寫
上海寫作計劃,並不要求作家定時交出與上海有關的作品。“文學不是功利的,作家的創作是自發的、無法被約束的。”胡佩華介紹。從某種程度來説,正是由於這種無功利性,使得這項每年初秋如期舉辦的活動有了更廣闊、長久的生命力。
除在上海的居民小區裏住兩個月,寫作計劃安排作家們的活動包括舉行3場文學報告會,參加與上海作家的座談交流、訪問大學等。更多時間裏,作家們自行遊弋在這座城市。聽上去似乎有點散漫,但對於這些沒有特定目的、也不抱功利心的作家們而言,上海,是這個寫作計劃最有吸引力的因素。
雖説,寫作是寂寞的勞動,但換一個空間,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作家相互交流,這種碰撞,不論對遠來的駐市作家還是對上海本地作家,都是一次新的際遇。
“如果不碰面,化學反應不會發生。因為比起經濟的互通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要來得更複雜,也更緩慢。”上海市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作家孫甘露感慨。
王安憶曾在歡迎會上表示,許多年來,“功夫”“紅燈籠”等符號讓世界對中國的解讀過於單一,而上海也在“007”等電影中成為一個傳奇但失真的舞臺。要讓中國、讓上海更真實地進入世界視野,就需要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來體驗、書寫不一樣的故事版本。
12年過去了,收穫超乎預期。這些作家不僅將他們的經驗匯入上海的故事,也將上海的故事帶到世界各地。保加利亞作家茲德拉伕科·伊蒂莫娃回國後,將趙麗宏的詩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憶的小説《小飯店》以及孫未的3篇短篇小説翻譯成了保加利亞語,與保加利亞讀者分享她對這些作品的喜愛。2016年駐市作家、丹麥作家福勞德·歐爾森寫下新作《辣斐德路上的克萊門公寓74號房間》,這部非虛構作品穿插了他在上海尋訪歷史建築的親身經歷,並在《收穫》上首發。他説:“麥家、余華都是我欣賞的中國作家,他們的敘事技巧給我不少啟發。”
就像水衝出閘門,12年過去,上海寫作計劃,靜水流深。
《 人民日報 》( 2019年12月09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