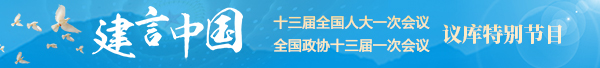龍墨:用時間打磨幸福
◆龍墨簡介:
第十二、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原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主任醫師、聽力師;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殘疾人康復協會聽力語言康復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科學雜誌》主編;《聽力學及言語疾病雜誌》編委。
孩子有點緊張,家長急切地表達訴求。龍墨一邊調試人工耳蝸,一邊詢問情況。她那溫和的聲線安撫著對方的情緒:“如果有經濟條件,可選配無線調頻系統。如果有這方面的慈善資助,我也會聯繫你們的。”
回去後,家長給龍墨發了一條資訊:“龍老師,孩子們有你,真好!”
這是3月裏發生在聽力師龍墨和患者之間的一個小故事,它是龍墨20多年來為聽障孩子及其家庭服務的一個小小縮影。
到今天,中國的專業聽力師也僅有數百位,他們面對的,卻是數十萬名聽障兒童以及總數達2780萬的聽障人群。
每天面對著聾兒和家長,千萬次地讓孩子發同一個音,千萬次地回答家長同樣的“為什麼”……他們時常感到孤獨,甚至因孩子難以康復而感到無助。每當有孩子順利完成康復訓練、達到理想效果,他們又會感到滿滿的幸福。
作為中國第一批聽力師之一,龍墨職業生涯中最熟悉的滋味,就是這種在幸福與無助之間的“搖擺”。她將畢生心血投入聾兒康復事業,見證了20多年來的迅猛發展。一線門診、科研學術、知識傳承、人才培養……龍墨幾乎參與到每個環節,歲月催生了華發,也醞釀了故事。
在龍墨眼中,多年來,無數聾康人秉持“匠心”,以康復改變命運,成就孩子的一生,這是最大的價值所在。多年來,她和同行們耐住寂寞,滴水穿石般積累的創新,如今正生發出更大的能量。
時間的味道
1995年3月5日,剛剛褪去夜班疲憊的龍墨,走出宣武醫院兒科辦公室,直接去了新單位中國聾兒康復研究中心(現為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報到。換工作的理由其實很簡單:一是自己喜歡孩子,新工作正好與兒童相關;二是有時間照顧家人。
新工作滿足了這些需求,然後,她就一直幹到現在。
那時,“聽力師”這個職業幾乎沒人聽説過。1996年,龍墨得以進入澳大利亞麥加利大學、首都醫科大學和北京耳研所聯合辦的國內首所聽力學校,當時一位教師在課堂上説:“中國真正的聽力師為零。”這讓初次聽聞的龍墨既深感震驚,也意識到發展聾兒康復事業的艱難。
聽力學是個交叉學科,身為一個聽力師,不僅要具備聽力和基本的耳科方面的知識,還要學習心理、聲學、語音、康復等方面的知識。因而到今天,全國範圍內,國家真正培養出來的、接受聽力學專業培養的聽力師仍然只有數百人。這個職業不會引來人們羨慕的目光,多數人更希望成為耳科醫師。
從兒科醫生轉型為聽力師,龍墨還面臨不小的困難,年近40歲的她接觸一個全新的領域,不僅要學習聽力方面的知識,還要接受全英文教學環境的挑戰。
面對這些,龍墨沒有牢騷,憑著一股韌勁堅持了下來。不久後,中國有了第一批專業的聽力師,她是其中一員。
很難説是“少説話,多做事”的個性造就了事業,還是這一職業賦予她踏實的性格。這23年,龍墨在聽力這個領域打磨、沉澱,熬出了一種“時間的味道”。
她見證了聾兒康復領域翻天覆地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模擬信號助聽器是主流設備,後來發展成電腦編程助聽器和全數字助聽器,如今,人工耳蝸已廣泛應用。”
聾兒助聽設備佩戴率逐步提高,康復目標也從早期的“能聽會説”到如今的“全面康復”,這其中有科技進步,也有政策變化。在和緩的音線中,10餘年的變化被娓娓道來:“這個領域大約從2000年開始,就有了國家層面的救助;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救助從2009年的‘十一五’開始,國家為符合條件的孩子提供免費助聽器和人工耳蝸;到‘十二五’期間,救助的規模和社會關注力度也越來越大,‘愛耳日’宣傳活動逐漸開展,人們對人工耳蝸、聾兒康復的了解度明顯上升。”
如今,我國已步入“十三五”時期,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殘疾人一個都不能少”方針的進一步明確,殘疾人康復事業也逐漸步入“精準康復”模式,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2000年,龍墨去陜北地區調研,她發現當地條件較差,工作人員在舊窯洞和老建築中開展聾兒康復,至於語訓,因為缺乏助聽設備,靠的是“玩命地大喊”或看口型。
如今,她在各地調研時看到的景象已不一樣,隨著大量資源的投入,一些地方新建的康復機構寬敞、明亮,設備十分先進,專業的康復人員也越來越多。
“我相信,聾兒的全面康復已非遙遠的夢想。”龍墨説。
外部環境變化顯著,但龍墨還是那個龍墨,她守著自己的“初心”:“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沒有特別高的定位,只有一個基本的自我要求:做好分內的工作,盡力做到最好。”
如今,雖然承擔機構的管理工作,也以論文、著作等被聘為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兼職教授,但只要有時間,龍墨還堅持在一線門診積累經驗。
康復事業的發展讓更多年輕人加入進來,這讓龍墨逐漸意識到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像當初老師無私地帶她一樣,她也希望利用自己的專業和管理的平臺優勢,為更多想做事的人“搭臺”。“無論是作為具有高級職稱的專業人員還是領導幹部,都應為年輕人的成長搭建平臺,並通過言傳身教去影響他們。”
龍墨以自己的名義申請到科研項目,再將項目交給年輕的團隊去做,定期為他們提供指導,給予機會並盡力解決實際問題,讓他們迅速成長。在論文指導方面,她不惜精力地提供修改意見,但從不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幫助年輕人特別重要的是,少一點私心。這個事業是一代代聾康人創造下來的,也應一代代傳承下去。”龍墨像個忠實的園丁一樣,盡力澆灌著年輕的“樹苗”,期待在聽力這個領域,有更多“大樹”成長。
幸福與無助之間的搖擺
每年,有200多個聾兒來到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接受康復訓練。相比其他殘疾群體,聾人最難與別人正常交流。因而龍墨經常引用國外一項研究的表述:“世界上最孤獨的群體是聾人。”
她認為,面對聾兒這個群體,聽力師最需要的是愛心、耐心和責任心。
“沒有愛心的人不要選擇這個職業。首先要愛孩子,然後才能對這些特殊的孩子有愛心。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龍墨深深理解,“孩子們的理解和表達要快於口語表達,表達不出來很容易發脾氣,很多內心的感受無法與你交流,這就需要愛的力量,應盡可能地理解包容他們。”
耐心也是聽力師必備的素質。比如,對一個1歲的聾兒開展康復訓練,孩子不可能完全按照老師們要求的去做,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很短,有時候,一個詞需要每天反覆地説幾十遍,與做普通幼兒園的老師相比,聾兒康復教師需要足夠的耐心。
在一線門診,龍墨經常見到家長們的眼淚,以及眼淚背後的種種焦慮和心酸。一位來自山東農村的孩子接受國家助殘項目的救治,然而康復效果並不理想。有一段時間,家長帶著孩子到中心“討説法”,甚至坐在龍墨的辦公室和她一起“上下班”,在情緒激動時表示“要帶著孩子一起跳樓”。
龍墨理解這種痛苦,她沒有生氣。在家長情緒平復時,她與對方嘮起了家常,她的同理心和溫和讓家長漸漸敞開了心扉:“孩子聽力有問題,我無法忍受別人的那種目光,在村裏連家門都不敢出。我帶孩子出來,打工、租房,再苦再累也不在乎,就是希望帶著能完全跟人交流的他再回家……”龍墨心知,要幫助這些家庭減少痛苦、增加快樂,聾康人的責任感太重要了。她自己總會拿出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把工作做在康復之外,與家長一點點地交心,逐漸讓家長正確理解孩子的聽障問題,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問題。
幾十年堅守著聾康人陣地,但龍墨能夠理解頻繁跳槽的人,“這是時代發展賦予人們自由選擇的機會。”在她的職業觀中,責任心又是一個具有統領意義的關鍵詞,“既然在一個崗位上,就要盡到責任,即使將來離開了也不留遺憾。這種負責任的態度將永遠影響一個人的職業生涯。”
孩子的特殊性造成了聽力師、康復教師職業的獨特性———每天面對家長同樣的“十萬個為什麼”、日復一日地重復訓練,甚至要面對一些家庭的悲劇,幾十年裏的經歷,難免讓龍墨生發出孤獨、無助和無奈之感。
有一次,一位聽障女孩在植入人工耳蝸後能聽到聲音,但經過康復後,語言理解和表達卻很差。為了搞清楚症狀所在,龍墨與工作人員反覆診斷,最終發現是聽神經存在問題,非現有技術能完全解決。最後,龍墨只能無助地看著孩子離去。“這種無助感蔓延在心中,時刻煎熬著我們。但我們不能被挫折擊倒。”
每一個遇到聽力障礙的聾兒都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而人的問題是最複雜最難解決的。“唯有長久堅持、盡力而為才能迎來更好的結果。”為著這個更好的結果,龍墨一直在用溫和的力量感染著聾兒家庭,這種力量往往是相互的。
一位來自河北的孩子,長得特別漂亮,被診斷為極重度耳聾後到中心接受康復訓練。龍墨漸漸發現,父親來看望孩子的次數越來越少,不久後,父親難以承受壓力最終導致離婚。孩子的母親需要工作,姥姥帶著孩子堅持康復。所幸,最終孩子進入普通小學,如今已經成為品學兼優的學生。
去年8月,在加拿大多倫多上大學的恒恒(化名)回國,前來看望龍墨。恒恒是聽力障礙患者,植入人工耳蝸後,經過康復訓練,在國內普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高中選擇到加拿大就讀,最終考取多倫多大學。看著這位22歲的年輕女孩青春洋溢的面容,龍墨心中喜悅。回家後,她有點激動地寫了一篇文章分享這次會面的感受:“和恒恒一樣的孩子讓我覺得工作這麼有價值,讓我體會到許多人體會不到的幸福,讓我體會到被人需要、能給人帶來幫助是一件多麼快樂的事情……”
如今,每年在中心通過康復訓練得以進入普通幼兒園、小學的孩子,比例達到了95%以上。龍墨的信心來自不斷地自我肯定和被肯定,“這項工作的最終意義,就在於改變了人,成就了人。”
情到濃時,事入細處
職業生涯中,龍墨經年累月在門診積累經驗,也為引入國際技術與經驗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聽覺口語法(AVT)”是國際上較為通用並認可的康復方法,起初,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引入的是碎片化內容,而系統引入需要龐大的工作量。區別於英語等其他語言,漢語是有調語言,僅此一點,該方法的漢化不僅需要翻譯,還需要新的研發。
10年前,龍墨就參與到與台灣等地的機構合作之中,將此方法引進中國大陸地區,並根據發音特點進行完善,形成完整的聾兒個別化教學體系。如今,這一方法在中國大陸聾兒康復工作中已被廣泛使用。“一點點地引入、研發和應用,才有了今天的局面,無數聾康人為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這幾年,中國聽力語言康復研究中心受中國殘聯委託,承擔了一個組織編寫六類殘疾兒童康復訓練教材的大型項目。在聾兒康復訓練方面,中心的辦公室裏經常出現這樣的場面:龍墨和她的團隊成員們一次次地討論,一次次地否定,一次次地修改。
比如,學前階段聾兒康復訓練所用的挂圖是什麼樣?這個問題甚至讓設計廠家改到快“崩潰”的地步。根據挂圖對應的年齡不同,究竟應該用什麼樣的色彩對應多大的年齡?是用實物的圖像還是用動畫的形式呈現?如果是動畫,這個卡通形象孩子喜不喜歡?從孩子的認知角度考慮,這幅挂圖是否能讓他們一看到就能聯想起對應的內容?等等。
就是這一套基礎性的教材,其編寫過程經歷了繁複的細節討論。儘管如此,龍墨仍有點忐忑:“我不知道最終效果是否理想。要將教學實踐上升到理論,能夠作為一種指導性的內容予以出版,這是一個很踏實、需要磨煉工夫、耐得住寂寞的過程。”
“借鑒和創新,是這樣一點點地‘摳’出來的。”龍墨認為,創新和引領並非飄在雲端的奇思妙想,而是由基礎工作的無數次漸進促成的,是在一代代聾康人為之奮鬥努力奉獻的基礎上積累起來的。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後,龍墨覺得,自己在聽力這個領域紮根多年,為聾兒群體鼓與呼是自己的責任。漸漸地,在履職過程中,她的關注面越來越寬,也意識到更大的責任:“我最初關注聾兒,後來關注所有殘疾兒童,進而關注整個殘疾人群體以及殘疾人工作者。某種程度上,我是他們的‘代言人’。”
政協委員的身份與職責打開了更大的視野。龍墨多次參與無障礙環境建設的討論,去年6月還參加了全國政協召開的雙週協商座談會,圍繞“無障礙環境建設”建言。她那研究型、積累型的職業習慣,為委員履職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甚至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只要一齣門,龍墨就像得了“強迫症”似地觀察身邊的地鐵、商場、街道等公共場所中的無障礙環境。眼看到自己的婆婆因為膝蓋損傷,上下樓不方便,這啟發了龍墨,她特意去地鐵站仔細查看,發現地鐵扶梯邊安裝了輪椅滑軌,卻被塵封起來。由此,她建議,無障礙設施硬體有了,但軟體(管理)也不能缺,助殘要“軟硬兼施”。
情必近乎癡方始真。龍墨還有個“怪癖”,她上街特別愛看別人的耳朵。一家人散步時,她會一邊看一邊跟家人討論:“你看那人是不是戴的咱中心的人工耳蝸?”“這人是戴的助聽器嗎?”看完後覺得很親切,“就像觀察人們戴眼鏡似的。”
龍墨眼中,履行政協委員職責與聾兒康復工作有相似之處,馬虎不得,建言獻策應該建立在翔實的調研基礎上,建議要清晰,還要融入真情實感。
2017年全國兩會前夕,龍墨收到一封來自河北省崇禮縣的來信。一位老人在信中跟她傾訴自己的煩惱,外孫今年讀高一,畫畫很好,因為佩戴人工耳蝸,她擔心外孫在藝考當中被不公平對待。老人“一宿一宿地睡不著覺”,她希望將自己的擔心轉達給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如果我的孩子能(考)出去,我死而無憾。”這封來信深深打動了龍墨:“殘疾人也好,聾人群體也罷,其實裏面都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他們的個性、需求各不相同……”
2017年全國兩會上,龍墨以《多舉聯動精準扶助讓更多貧困殘疾兒童幸福快樂成長》為題所作的大會發言,其中有一句話打動了許多人:“儘管我們每天接觸聽障孩子,但當聽到孩子經過康復清晰地喊出‘媽媽’‘老師’,還是禁不住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