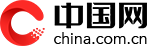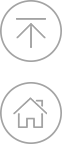摘要:儒家思想曾深刻影響了西方“自由放任主義”的內涵,而其本身在經濟上也存在著鮮明的“自由放任”傾向。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儒家承認人之自利心的存在,並認可人們積極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二是遵從勞動分工,認為不同分工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反對干預人們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對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稅收政策,主張發展自由貿易;四是反對政府直接從事生産經營活動,主張限制稅收進而限制政府開支和規模。這些鮮明的“自由放任”傾向,與強烈的倫理取向,共同構成了儒家經濟思想的重要特徵。
關鍵詞: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儒家;
引言
重義輕利是儒家的一般形象,以致於人們將古代中國經濟發展遲滯、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歸咎於儒家經濟思想的阻礙。但陳煥章發現儒家在經濟政策上不僅贊同“社會立法”,還贊同“自由放任”【1】。唐慶增也認為儒家之財政學説有兩大特點:“一曰放任主義”,“二曰薄斂”【2】。“自由放任”是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朱家楨認為用它來概括儒家的“開禁民利”思想並不妥當【3】。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自由放任”的內涵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深刻淵源,便會相信用它來闡釋儒家經濟思想的傾向性並無不妥。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形成,離不開法國重農學派對“自由放任”概念的闡釋和鼓吹,重農學派從他們的自然法哲學推衍出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張,而其自然法哲學又與中國儒家的思想傳統存在著深刻淵源【4】。並且,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認為,儒家的經書就是自然法典,是中國的基本法,儒家中國就是一個完全按照自然法統治的國家,人們完全按照自然法則進行生産和生活【5】。不言而喻,根據魁奈的觀點,信仰自然法並對自然法有著最高水準理解的儒家,在經濟思想上必然也是一種“自由放任主義”。古代中國當然不像魁奈描述的那樣美好,儒家也不是完全的經濟自由主義,但説儒家經濟思想中存在“自由放任”的傾向,卻無不可。
1912年,陳煥章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第一次使用“自由放任”一語指代儒家社會主義運動遵循事物之“自然發展進程”的特徵【6】。1936年,唐慶增在他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一書中也指出儒家財政學説具有“放任主義”特點,認為儒家的“自由放任主義”就是“藏富於民”,反對官辦營業與民爭利【7】。陳、唐二氏皆留學美國學習經濟學,他們發現儒家經濟思想的“自由放任”特徵顯然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在陳、唐之間,胡適、熊夢也曾用西方的“自由放任主義”分析老子的經濟思想【8】。但重農學派對“自由放任”這一概念的闡釋與發展,畢竟是受了儒家思想而非老子思想的影響,而且魁奈還將老子與道教混為一談而進行了嚴厲的批判【5】。1983年,侯家駒出版《先秦儒家自由經濟思想》一書,分別討論了孔子、孟子、荀子的經濟思想及其“自由放任”特徵【9】。1992年,談敏出版《法國重農學派學説的中國淵源》一書,比較了重農學派和儒家“自由放任”思想的異同【4】。1998年,馬濤發表《論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文,簡單考察了孔子、孟子、葉適、丘浚等儒家人物的自由經濟思想【10】。同年,胡寄窗出版《中國經濟思想史》【11】,2016年盛洪出版《儒學的經濟學解釋》【12】,也都提到儒家經濟思想的“自由放任”特徵。
在這些研究中,陳煥章、侯家駒、馬濤等將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的經濟思想視作儒家“自由放任主義”的典型,似不妥。雖然司馬遷在學術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對人類自利心的認識也與儒家一脈相承,但他説的“善者因之”明顯是黃老“因循為用”思想的翻版,是漢初“與民休息”之現實政策的反映。而談敏將孔子説的“無為而治”視為儒家的“自由放任”思想,本文也不認同。因為孔子所説的“無為而治”是一種領導藝術,指君主“為政以德”,選賢與能,使賢能各敬其職,從而垂拱而治,而不是指經濟管理的“自由放任主義”。不僅儒家,老子的“無為”也不是經濟自由主義,因為老子之“無為”是要遏絕人欲,根本反對發展經濟,遑論成為“自由放任主義”的中國淵源?本文認為上述研究主要有兩點貢獻:一是指出了儒家“自由放任”主義的自然法基礎,即儒家的天道思想;二是指出了儒家“自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即孔子所説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研究的不足之處,除了誤將儒家的“無為而治”等同於“自由放任主義”,將司馬遷的“善者因之”視為儒家“自由放任主義”的代表,主要是缺乏對儒家經濟思想之“自由放任”傾向的系統考察。
本文的目的,不在於提出新觀點,也不在於發現新材料,而在於努力用舊材料論證一個較少為人們注意的老觀點,盡可能全面地去展示儒家經濟思想“自由放任”傾向的具體內容。正如盛洪所説,“自由放任”的深層含義是“遵從自然的秩序,遵從自然秩序演化出來的結果”【13】。遵從自然秩序,遵從自然秩序的演化結果,必然意味著要尊重個體追求物質財富的努力,尊重因個體差異而産生的勞動分工,保障自由貿易,減少政府的干預。這些正是現代“自由放任主義”的基本內容。本文即從這幾個方面切入,詳細考察儒家經濟思想的“自由放任”傾向。基於篇幅限制,本文的考察範圍主要限制在先秦時期。
一、儒家式的“經濟人”
魁奈認為,“社會的基本法則是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則”【14】,人類遵從自然秩序的法則完全是出於自利心的自覺行為,因而每個人在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必然客觀地促進著社會的整體利益。這就是重農學派“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主張的邏輯,這個邏輯實際上也就是後來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儒家一向重視“義利之辨”,自然不是相信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然能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但儒家之所以重視“義利之辨”,也正是基於對個體之自利心的深刻洞察。
首先,儒家承認追求物質財富是人的基本情慾。
孔子認為,“人既是精神存在,也是物質存在”【15】。作為物質的存在,人必然有物質上的欲求。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禮記·禮運》)“飲食”是生存需要,“男女”是性的需要,二者共同構成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人之大欲。並且,人不僅欲飲食,欲男女,還欲美味,欲美色,欲富貴。所以孔子又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裏仁》)。人人皆是如此,孔子自己也不例外。
孟子對人之情慾抱持一種批判和改造的態度,但他的批判與改造正建立在追求物質財富是人的基本慾望這一前提之上。他説:“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孟子·萬章上》)。他批判告子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之説,只是反對將人的物質欲求看做本性之固有,以絕人之妄求,而非完全否定人的物質欲求。故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盡心下》)實際上是承認物質欲求亦是性之所有,只是現實中不能必如其願,故托于命而不謂之性。
荀子的欲求論思想更加豐富【16】,他將物質欲求看做人之本性使然,曰:“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榮辱》)“所生而有”者是性,性發而為情,故又曰:“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同上)《荀子·王霸》亦曰:“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綦,訓極,或以為“甚”之誤17。欲求得不到滿足,便會相互爭奪而導致混亂,故荀子以人性為惡,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荀子的類似表述無法一一贅舉,雖然他的最終目的也是要規範人的欲求,即“化性起偽”,但其“化性起偽”的努力仍然是以人的自利心為前提。
其次,儒家認可、甚至鼓勵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
既然追求物質財富是人的基本情慾,那麼便不應對個體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一概抹殺。事實上,儒家認可甚至鼓勵個體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孔子説“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裏仁》),其本意並非以義利判別道德意義上的君子小人,而是界定不同身份地位者的經濟倫理——至少兩漢的儒家學者都是這樣理解【18】,肯定一般民眾的職分就是追求物質財富。在孔子那個時代,人們並不諱言利,也不羞于求利。孔子自己也説:“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向來儒者多強調富貴的“不可求”,但孔子首先説的是富貴“可求”的情形,如果富貴可求,即便是為人執鞭駕車的賤役他也可以去做。孔子確曾做過委吏、乘田這樣的小吏,雖然並沒有因此而致富。孔子自己雖然沒有致富,但他十分器重的弟子子貢卻“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19】。
不僅庶民階層可以積極地追求自己的物質財富,士大夫亦可以祿致富。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耕者力田,仕者食祿。故周室班爵祿,雖諸侯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必使“祿足以代其耕也”(《孟子·萬章下》)。先秦時期,士不從事生産經營活動,失其位則失其祿,也就失去了生活來源。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孟子·滕文公下》)對於士來説,“無君”便沒有了工作,也就失去了生活來源,所以“皇皇如也”,親友皆來慰問。為了生活,不得不努力找工作,所以“出疆必載質”。子張曾“學幹祿”(《論語·為政》),三千弟子幾人沒有幹祿之心呢?孔子認為士在治道清明的時代就應該積極入仕,並可以坦然接受由此帶來的富貴,曰“邦有道,榖”(《論語·憲問》)。宜於出仕卻不出仕,以致于身處貧賤,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堯曰》),説的便是周有天下,大封于宗廟,賢者得祿而富。儒者積極出仕,非為祿廩,但德配其位,材堪其任,得祿而富,未為不可。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顏淵簞食瓢飲,原憲不厭糟糠,皆非惡富貴而好貧賤。
很多人批評儒家強調“義利之辨”,限制了人們的物質欲求,但儒家卻認為禮義這一套淵源自先王的自然法則,恰恰是成全人們的物質欲求的。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荀子·禮論》)荀子還嚴厲批評了當時的“去欲論”和“寡欲論”,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于多欲者也。”(《荀子·正名》)他認為人的慾望不可能消滅,也不可能減少,雖然慾望不一定皆能得到滿足,但有慾望並想辦法去實現慾望是人性之本然,是人之常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同上)所以,即使要防止個體求利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是去消滅或壓制人們的慾望,而是應該以道、以禮義去引導人們的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以使每個人的慾望都能得到更好的滿足。
所以,儒家政治以富民為首務,而富民就是任民自富。
物質財富是人的根本欲求,所以,滿足人們的欲求,實現人民富裕是儒家政治的第一要務。《周易·係辭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尚書·洪范》箕子陳八政,食、貨為先。孔子進一步提出了“求富”思想,認為“富民、足民是為政、治國的基本要求”【20】。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冉有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然後“教之”(《論語·子路》)。“富民之論,不但為孔子經濟學説之基礎,亦為儒家主張之一大特點”【21】。孟子發揚儒家的富民思想,認為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是“王道之始也”,曰“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主張明君必“制民之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論“富國”,以“富民”為基礎,認為“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荀子·富國》)。
但是,儒家之“富民”絕不是通過國家力量直接為人民分配財富,而是主張採取放任的政策,讓每個人自己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孔子曰:君子為政,“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論語·堯曰》)這個“惠”字,與子謂子産“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的“惠”字同義,皆是“愛利”的意思【22】。所謂“惠”,就是指政府應施愛利於民。政府愛利人民是“惠”,但又要“不費”,“不費”就是不必耗費公帑以富民。政府做到“不費”的途徑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之所以能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正意味著“民”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且正在自覺地追求著自己的利益。政府的“因”就是要順應人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為,放任人們自己去實現自己的利益。在這個“因”的過程中,政府所應該做的,只是協調人們的物質生産活動,為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提供便利。如此,則政府有施惠之名,卻無耗費之實。所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儒家式“經濟人”假設的最好表達形式。
二、儒家的勞動分工思想
亞當·斯密認為,引起勞動分工的原因是人性中那種“互通有無、進行物物交換、彼此交易的傾向”【23】,而不是不同的人存在著天賦才能的差異。所謂人性中的那種“互通有無、進行物物交換、彼此交易的傾向”,實際上就是個體源於自利心的多樣化欲求。但勞動分工之成為必要,即使不是因為個體天賦才能的差異,也是由於個體天賦才能的局限性,即由於個體滿足自己多樣化欲求之能力的局限性,因而不得不進行分工合作。儒家對勞動分工帶來的經濟效益有清楚的認識,因而充分尊重這種自然秩序演化的結果。
(一)君子與小人——腦力勞動亦創造價值
君子和小人,在先秦的很多語境中分別指貴族統治者和一般民眾。貴族統治者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一般民眾主要從事體力勞動。儒家十分重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認為腦力勞動也同樣創造價值。
如前所述,孔子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裏仁》),實質上強調的便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他一再告誡“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即謂作為腦力勞動者的君子,應該用心力於布道教化,專心做好社會治理工作,為體力勞動階級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而不是自己親自去從事生産勞動。所以,當樊遲請學稼為圃時,孔子不僅推託“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還批評他説:“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孔子並非否定農業生産活動之價值,只是他開創私學實欲培養治國平天下的君子。社會上不缺少能夠為稼為圃的體力勞動者,真正缺少的是能夠治理國家天下,創造良好的社會秩序,保障勞動階層安居樂業的君子。如果君子好仁好禮好義好信,將國家治理好,則天下的勞動者自會“襁負其子而至矣”,又何必親自從事體力勞動呢?他創造的社會價值又豈是收穫多少糧食可以衡量的呢?
荷蓧丈人批評孔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論語·微子》),實際上是對腦力勞動的歧視。農家學派也認為“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孟子·滕文公上》),抹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別,抹殺腦力勞動的價值。孟子完全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批評他説:“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同上)在孟子看來,不僅物質生産部門內部不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物質生産部門和精神生産部門之間,即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如果沒有腦力勞動者對社會的有效管理,不能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體力勞動者就無法安定地生産和生活。在這次辯論中,孟子代表儒家,“充分肯定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24】。彭更也疑惑“士無事而食”,孟子再次強調了腦力勞動的社會價值,認為腦力勞動者絕對不是不勞而獲,坐吃白食,而是在創造著人類社會健康運轉所不必不可少的精神財富,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孟子認為應該“食功”而不是“食志”(《孟子·滕文公下》)。
(二)士、農、工、商——不同分工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孟子和農家學者的辯論,不僅強調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工的意義,還強調了不同體力勞動者之間分工的重要意義,就連農家學者最後也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來,勞動分工極大地促進了生産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如果沒有勞動分工,人類社會恐怕還停留在茹毛飲血的原始階段。故曰:“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同上)
荀子繼承併發展了儒家勞動分工的思想,對勞動分工的社會意義闡述最為詳細。他説:“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荀子·富國》)為了避免社會的“窮”和“爭”,“則莫若明分使群矣”。“明分”有制定“度量分界”的意思,所以人們一般將“明分”看做荀子的分配思想,但實際上它也包含著勞動分工意思。“明分”就是明個人的職分,農夫眾庶,將率百官,聖君賢相,各有其職分。人人各明其分,各盡其職,天下才能富足。故曰:“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草殖谷,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兇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同上)人人各明其分,各盡其職,則天子可以垂拱而治。職分既明,“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荀子·王霸》)。荀子將“農農、士士、工工、商商”等勞動分工體系,看做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等倫理等級體系及“貴賤、殺生、與奪”等獎懲體系相輔相成的天下“大本”(《荀子·王制》),認為它們是共同維持社會運轉和發展的基本秩序。荀子對勞動分工之社會意義的論述,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助於“使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提高社會生産力;二是促進專業化,有助於改進生産技能,提高産品品質;三是有助於“消除人們之間在物質利益方面的爭奪”【25】。
不同勞動皆創造價值,共同推動著社會經濟發展。孟子與農家學者辯論的重點便是闡明這個道理。《周禮·考工記》亦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整個社會由六個勞動部門組成,體力勞動部門不僅包括農、工、商的勞動,也包括女性的勞動,與王公、士大夫的腦力勞動一樣,都是社會價值創造的有機組成部分,共同維繫著社會的運轉和發展。《周禮》由戰國儒家雜取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制度編撰而成,但作者的目的不是為了彙編史料,而是要設計一套理想的制度,所以它實際上反映了戰國儒家的政治社會思想【26】。
(三)因民自利——放任人們自由地選擇生産經營活動
陳煥章已經指出,根據孔門的經濟理論,人們普遍享有遷移的自由和選擇職業的自由,享有選擇生産經營活動的自由【27】。這正反映了儒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經濟管理原則,打破了管仲“四民分業定居”的靜態理論。
儒家推動人們的地域流動。在儒家思想中,能否招徠四方的人民是檢驗政治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孔子認為君子好禮義而講誠信,“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不必親自從事生産勞動。因為招徠四方之民,可以發展本國的生産。《禮記·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七曰“來百工也”,八曰“柔遠人也”,“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説的便是招徠他國工人、商旅和勞動力以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到了孟子的時代,人民的遷徙似乎已經相當自由,故孟子曰:“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孟子·梁惠王上》)國君“發政施仁”之所以可以吸引到四方的人才,當然是建立在人民能夠自由遷徙的前提之上。《穀梁傳》曰:“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莊公三年》)儒家倡導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放任人民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自由地選擇仁義之君,自由地選擇自己從事生産和生活的地域。
儒家還認可人們自由地選擇職業。到了戰國時期,勞動階級不同職業間的流動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了。孟子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職業不同,其所利者亦不同,“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孫醜上》)。能夠“不可不慎”,意味著個體應該慎重地選擇職業,也意味著個體可以選擇職業。陳煥章説:“根據孔教徒的理論,人每人平均應享有選擇其職業的自由,而自由選擇職業在古代已是確鑿的事實。”【27】此論雖不免誇大其辭,但説自由選擇職業是儒家的基本思想傾向,則無不妥。荀子曰:“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荀子·榮辱》)“注錯”即措置之義,此處指人的選擇。又曰:“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斫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荀子·儒效》)雖然職業皆由學習積累而來,而除了習慣與環境的影響,學不學則在自我的選擇,選擇的根據完全在於對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慮,確實已經沒有強制繼承的意味在其中了。
人們從事什麼樣的生産經營活動,在何處從事生産經營活動,政府不應隨意干涉。《禮記·禮運》曰:“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鄭玄注:“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疏雲:“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敝困也”【28】。強調的便是政府不得干預人們因居住環境不同而選擇的生産活動。既然政府不能強迫居山狩獵者去以舟楫渡人為業,不能強迫居渚販賣魚鹽者去務農耕稼為業,當然也不能強迫農人去從事陶冶,不能強迫工人去從事貿易,不能強迫商人去從事農耕,而應放任人們去從事自己認為最有利的職業和工作。這也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應有之義,邢昺曰:“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于財也。”【29】邢昺的解釋,概括言之,就是遵守自然法則,順應因自然差異而産生的分工。
三、儒家的自由貿易思想
勞動分工意味著生産專門化,意味著生産率的提高,意味著個體的多方面欲求可以得到更好地滿足,但同時也意味著一個人無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勞動産品生存下去,因而不能獨佔自己的勞動産品,必須用自己生産的剩餘産品去交換他人生産的剩餘産品,於是貿易成為必然。“自由放任主義”主張自由貿易,即取消對貿易的任何阻礙,推動商品在國內與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自由貿易有利於優勢互補,儒家對優勢互補原理尚無清楚認識,但對貿易帶來的物質生活的豐富卻有深刻的體驗,因而堅決地主張自由貿易,反對徵收商稅。
(一)不抑商,鼓勵商品貿易的發展
儒家重農但不抑商【30】,儒家文獻中多有鼓勵商品貿易的記載。《尚書·益稷》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説的是禹治水時,后稷教民耕種,並鼓勵人們交易有無,解決了生存問題。《尚書·洪范》八政“二曰貨”,其中也包含著發展商品貿易的內容。周公告誡康叔:“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尚書·酒誥》)就是鼓勵民眾在農閒時去遠方貿易。西周之末,鄭國與商人共同開拓新疆土,並訂立了世代相守的盟約。子産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左傳·昭公十六年》)又葵丘之盟,曰“無遏糴”(《孟子·告子下》),規定各國不能阻礙糧食貿易。西元前562年,鄭與晉、宋等盟,曰“毋蕰年,毋壅利”(《左傳·襄公十一年》),規定各國不能阻礙糧食貿易和商品流通。
孔子對商品貿易持一種積極的態度。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後儒狃于重義輕利的成見,認為這是孔子在批評子貢。但實際上這句話中的“命”當如王弼之説,釋為“爵命”,即殷仲堪所謂“不受矯君命”,江熙所謂“賜不榮濁世之祿”【31】。子貢曾仕于魯、衛,蓋見道之不行,乃“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32】,在孔門中最為富有(《史記·貨殖列傳》)。孔子也曾以商賈自況積極入世的心情,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説,遠者來。”(《論語·子路》)《禮記·中庸》曰:“柔遠人。”所謂“遠者”“遠人”,指的便是四方商旅。
孟子的貿易思想反映在他的分工理論中。當他指出勞動分工的必要性時,也揭示了貿易的必要性。孟子認為沒有分工便沒有生産的進步,但如果沒有貿易,個體的物質生活需求仍不能得到多方面的滿足。並且,孟子還認為不同分工之間的貿易是平等互利的關係,不存在一方損害另一方的問題。他説:“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連續的提問,逼得陳相也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孟子·滕文公上》)因為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産率,而因為貿易,使每個人都可以享用其他勞動者的勞動産品。否則,只有分工沒有貿易,每個人就只能消費自己的産品,而無法消費他人的勞動産品,每個勞動者的剩餘産品就只能浪費掉。所以,孟子責備彭更説:“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
荀子説“工商眾則國貧”,要求“省商賈之數”(《荀子·富國》),但他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商品貿易的發展,而是出於工、商業的發展必須適應農業生産力發展水準的考慮。荀子高度讚賞商品貿易給人們生活帶來的極大豐富,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四海之間相距千萬里,其物産中國皆得而用之,正有賴於貿易的發達。澤人不伐木,山人不網魚,農夫不制器,工賈不耕種,而皆能通其用,亦是賴於貿易的發展。
(二)反商稅,主張減少對商品流通的阻礙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可能已開始對商品徵收關稅和市場管理稅、倉儲稅。《周禮·司徒》曰:“廛人掌斂市布、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布,是“列肆之稅布”;布,是“無肆立持者之稅也”,或認為是“守鬥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是“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是“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是“貨賄諸物邸舍之稅”【33】。又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徵廛”,“國兇札,則無關門之徵,猶幾”。“幾”通譏,是檢查之義。司關不僅負責徵收過往商品的關稅,還負責徵收儲存于關下之貨物的倉儲稅,只有在遇到饑荒或疾疫的年份才免征關稅,但仍然例行檢查。
徵稅必然會阻礙商品貿易的發展,《周禮》的作者編列了這些官職,表示他認同這些稅收,但儒家主要學者都明確反對徵收商稅的行為,尤其反對徵收關稅的行為。反對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儒家認識到商品貿易可以極大地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而徵收商稅,尤其徵收關稅,會限制商品貿易的發展;二是儒家有“柔遠人”“遠者來”的政治理想,而徵收關稅會阻礙其招商引資——招徠人力資本的政策。所以,魯大夫臧文仲“置六關”【34】以徵商旅之稅,而孔子責其“不仁”(《孔子家語·顏回》)。
孟子不僅反對徵收關稅,還反對徵收市場管理稅、倉儲稅。他説:“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矣。”“關譏而不徵,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孟子·公孫醜上》)按鄭眾的解釋,“廛”是“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即儲存商品貨物的倉庫。所謂“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就是“貨物貯藏于市中而不租稅也”,“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35】。“譏”是檢查過往客商攜帶的貨物,看是否有違禁物品。有違禁物品當然要查收,但不應該對合法貨物徵收關稅。《禮記·王制》亦曰“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徵”,很可能與孟子的思想存在繼承關係。孟子批評戰國諸侯置關以徵稅的行為,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孟子·盡心下》)古之關卡,唯檢查違禁物品,主要職責是保護過往商旅安全,而戰國諸侯因兼併戰爭的開支,不僅對農民徵收各種賦稅,還設重重關卡對過往商旅徵收重稅,其所以為暴也。
荀子也主張政府應該促進商品貿易的發展,免征關稅。曰:“關市幾而不徵,……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荀子·王制》)又曰:“關市幾而不徵,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財通,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荀子·王霸》)荀子認為“平關市之徵”是“國富”和“以政裕民”的重要措施。“平”是除去的意思,批評戰國諸侯“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徵以難其事”(《荀子·富國》)。
(三)反干擾,保護正常的市場競爭活動
儒家似乎已經認識到市場機制影響商品價格的規律,因而認為商品有貴賤是市場競爭的正常表現。孔子和子貢曾經討論過玉和珉的價格問題,君子“貴玉而賤珉”,子貢傾向於認為是玉少而珉多的原因,即供求關係決定的;孔子則認為是由於二者使用價值的差異,即二者帶給消費者的效用不同,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荀子·法行》)。無論供求關係,還是商品使用價值的高低,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市場機制運作的規律。
孟子與農家學者的辯論也涉及到市場定價的問題。農家學者主張以“數量”為標準規定商品價格,曰:“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但即使同類商品在數量上相當,它們在品質上也會存在美惡精粗的差異,能帶給人們的效用不同,生産者付出的勞動也不同。如果按農家的主張,生産者只有降低品質才能獲得利潤,最終必然導致市場上的商品皆粗惡不堪。所以孟子堅決反對農家的主張,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同上)張守軍認為“情”即“實”,與“名”相對,“名是形式,是表面的東西,實則是內在的東西;名是表現實的,實對名則有決定的作用”。因而孟子所謂的“物之情”,“就只可能是隱藏在商品價格的背後並成為決定價格的基礎的商品價值”【36】。這實際上已經觸及商品的價值問題,只是孟子並沒有進一步説明價值的實體是什麼。
孟子還提出了反“龍斷”(壟斷)的問題。他説:“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徵之。徵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公孫醜下》)在孟子看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是貿易的基本精神,對於這種正當的貿易活動,政府只需管理而不需徵稅。但是,當有人試圖操控市場,居積投機,追求暴利時,政府就應該通過徵收商稅的形式予以懲戒。“龍斷”本義是“岡壟斷而高者”【37】,孟子用以指市場中的高亢之地,商人登而以便了解整個市場行情,從而操控市場,以獲取暴利。當時的“龍斷”主要指市場投機行為,遠遠沒有今天的壟斷那麼嚴重,但它對正常的市場競爭仍然會産生破壞作用。
四、儒家式的“小政府”
放任人們自由地從事經濟活動,必然意味著減少政府的干預。“自由放任主義”認為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少的政府就是“小政府”。儒家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實際上也是強調政府不應該直接參與到經濟活動中去,追求的正是一種“小政府”的模式。在社會層面,“小共體本位”是儒家抵禦“大政府”的有力武器【38】;而在經濟層面,儒家則通過限制政府的收入與開支,從而客觀上約束了政府權力和規模擴張。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為政者和政府之間並沒有嚴格的界限,為政者的行為往往就是政府的行為,所以我們下面討論政府的行為時,自然也包括了為政者的行為。
首先,以義為利,反對政府通過任何手段與民爭利。
儒家絕對反對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掠奪人民財富。周厲王使榮夷公專利,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國語·周語上》)厲王不聽芮良夫的建議,最終被國人流放于彘。《國語》被稱為《春秋》外傳,芮良夫的這段話也成為後世儒家反對政府與民爭利的經典依據。周幽王重蹈覆轍,《詩》雲:“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經·大雅·瞻卬》)幽王奪民之土田子女,爭商賈之利,最終被犬戎殺于驪山。至周景王,廢輕錢而鑄大錢,等於將人民的積蓄歸零,其實質也是掠奪人民的財富。故單穆公強烈反對,曰:“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國語·周語下》)人民失去財富,將會流徙他方。《周易·解卦》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即謂為政者舍仁義而逐于財利,必招致寇盜禍患。
儒家也堅決反對政府直接從事生産或經營活動以與民爭利。孔子曰“君子喻于義”(《論語·裏仁》),要求“位居社會上層的官員與士人,倫理活動先於理財活動”【39】。臧文仲使“妾織蒲”(《孔子家語·顏回》),孔子批評他不仁。《禮記·大學》引孟獻子之言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即謂有祿廩者不得蓄養雞豚牛羊,有采邑者不得加徵租稅。加徵租稅等於直接掠奪人民的勞動成果,而使妾織蒲,蓄養雞豚牛羊,無論是送到市場上銷售還是留作自用,都是與民爭利。因為體力勞動者通過向腦力勞動者出售剩餘産品以獲得收入,如果腦力勞動者也從事生産或經營活動,必然會影響到體力勞動者剩餘産品的銷售,也就等於將他們應得的收入奪走了一部分。故《禮記·大學》又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政府直接從事生活經營活動,將使勞動者在競爭中陷於極不利的地位。董仲舒曰:天亦有所分予,人不能竭利而取,故“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如果為政者“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則人民完全無法與之競爭,“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必然導致“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産生動亂。“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40】
其次,主張什一之稅,反對政府隨意加徵賦稅。
儒家主張輕賦薄斂,反對對土地産品以外的任何物品徵稅。孔子曰:“時使薄賦,所以勸百姓也。”(《禮記·中庸》)使民以時,輕賦薄斂,可以激勵勞動者致力於生産活動。孟子亦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孔子所謂“薄賦”,孟子所謂“薄其稅斂”,皆是指土地産品稅。儒家主張實行單一的土地産品稅,反對對土地産品稅之外的任何其他物品徵稅。上文已討論過儒家反對徵收商稅,如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徵”,“關譏而不徵”,除此之外,孟子又説“廛無夫裏之布”(《孟子·公孫醜上》),即還反對徵收房産稅。荀子發展了儒家輕賦薄斂的思想,曰:“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徵,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荀子·王制》)荀子主張只對土地産品徵收什一之稅,除此之外,不僅不徵關稅,也不徵自然資源稅。荀子還認為輕賦薄斂可以裕民富國,曰:“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荀子·富國》)
儒家理想的稅收制度是建立在“徹”法或“助”法上的什一稅制。魯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論語·顏淵》)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貢”法是取若干年之平均産量為一固定稅額,不考慮年成好壞皆以此稅額徵稅;“助”法是井田制下的稅收制度,以公田上的收入作為稅收;“徹”法是根據每年的具體産量確定當年的稅額,隨年成好壞而有所增減。雖然三種稅收制度名義上都是十分之一的稅率,但“貢”法有豐年寡取、凶年多取之弊;“徹”法年年檢校,不僅浪費行政資源,還存在著檢校官吏舞弊的風險;唯“助法”公田私田分明,公私收入同隨年成好壞增減,又無官吏舞弊之風險。所以,三者之中,“貢”法最差,“助”法最優——這正是兩千多年來儒家唸唸不忘“復井田”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子主張“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同上),荀子亦主張“田野什一”(《荀子·王制》)。《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宣公十五年》)
在古代生産力水準極其低下的情況下,加徵賦稅會嚴重影響到人們的生産和生活。孔子過泰山側,曾有“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下》)之嘆。故儒家十分反對隨意加徵賦稅的行為。冉求幫助季氏加徵租稅,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禮記·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務財用”即務于增加財政收入,要增加財政收入必然加徵賦稅,儒家認為這是小人之政。《魯詩》曰:“履畝稅而《碩鼠》作。”【41】西元前594年,魯國“初稅畝”,即不廢公田,“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42】,由原來的十稅一變成了十稅二,故《春秋》三傳都嚴厲地批評這件事情。《左傳》曰:“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宣公十五年》)《穀梁傳》曰:“初稅畝,非正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宣公十五年》)“悉”謂竭盡民力。《公羊傳》則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宣公十五年》)孟子亦有“大桀小桀”“大貉小貉”的批評,並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荀子也批評戰國諸侯:“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徵以難其事。”(《荀子·富國》)
儒家主張輕賦薄斂,反對與民爭利,反映了其“藏富於民”的思想。唐慶增説,儒家的“自由放任主義”就是“藏富於民”【43】。魯哀公欲加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藏富於民”是儒家“富民”政治的必然結果,它要求限制政府在勞動産品再分配中的份額,進而限制政府的開支,即荀子所謂的“節其流”(《荀子·富國》)。
再次,量入為出,限制政府的開支和規模。
為了限制政府開支,儒家主張“量入為出”的預算政策,反對政府的任何浪費行為。“量入為出”就是根據賦稅收入決定開支和用度,而不是根據開支和用度徵收賦稅。《禮記·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冢宰每年在賦稅徵收完成以後做來年的財政預算,每年的收入在留出一部分積蓄之後才是下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冢宰根據年成的豐歉和可支配收入的多少預算下一年的支出。“祭用數之仂”,“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除祭祀外,豐年“多不過禮”,歉年“少有所殺”【44】。
在有限的預算下,政府必須節儉開支。故有土之君,除了在禮樂制度和喪葬祭祀事宜上不能節儉以外,“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禮記·哀公問》)。禹就是一個這樣儉奢得當的典範,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禹儉約自身而能夠用心於祭祀,致力於禮樂制度和發展生産,所以孔子對他無所非議。不僅君主,對士大夫也有同樣的要求。《禮記·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寢不逾廟。”“故”者,祭、饗之事。如非祭祀或饗賓客,諸侯不得殺牛,大夫不得殺羊,士不得殺犬、豕,庶人不得食卵、魚、豚、雁,平常飲食不能過於祭祀之犧牲,衣服不能過於祭服,室屋不能過於宗廟。政府的消費應該在“時”與“禮”的規範之下,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上》)趙岐曰:“食取其徵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逾禮以費財也,故蓄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45】不過在這一點上,荀子與孔孟存在分歧,把君主奢華享受作為維護其等級地位的標識。
基於“量入為出”的預算政策,儒家主張限制政府規模,反對人浮於事,機構膨脹。荀子曰:“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眾則國貧,工商重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荀子·富國》)主張減少士大夫的數量以節省開支用度。張勁濤認為,荀子使用“節流”一詞的含義,就是“節約財政開支”,不僅限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消費,“還有個節約政府機構的行政經費的問題”【46】。
結語
綜上所述,儒家承認追求物質財富是每個人的基本慾望,荀子甚至認為這種慾望源自人的本性,因而認可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高度肯定基於個體能力限制及為了滿足多方面欲求而産生的勞動分工,認為不同分工共同促進著社會經濟發展,放任人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職業和經濟活動,主張推動商品貿易,反對阻礙商品貿易的任何稅收,反對擾亂市場競爭的干預政策和壟斷活動,反對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或直接從事經營活動與民爭利,主張輕賦薄斂,限制政府開支和政府規模等,都清晰地展現出儒家經濟思想的“自由放任”傾向。陳煥章説,歷史上“中國人享有太多的理財自由,除去少數因社會的緣故而限制消費的法律外,民眾確實在做他們想做的事”,即使那少數限制消費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也形同虛設,“是風俗支配中國的商業社會,而非法律”【47】。風俗支配中國古代的商業社會,而儒家思想支配中國古代的風俗。儒家思想不僅支配風俗,還支配著中國古代的法律和政治。歷史上中國人享有的經濟活動自由,雖然有政府行政能力不足的原因,但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在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傾向,也顯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儒家經濟思想和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儒家並沒有將“自由放任”作為全部經濟活動的價值追求,儒家雖然承認人們自利心的存在,並認可個體追求物質財富的行為,但顯然並不相信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必然會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因而主張以禮義規範和引導人們的經濟活動,特別強調義利之辨。儒家反對政府直接從事生産經營活動,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不適當的干預,但儒家從來沒有否定政府在制度建設、保障和推動經濟健康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陳煥章所説,儒家既有主張“自由放任”的一面,又有主張社會立法的一面,儒家主張政府立法管理和監督經濟活動,主張政府公平地分配生産資料,保護人民的財産,進行社會産品的再分配,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等。儒家是在國家治理的整體框架下思考經濟問題的,首先考慮的是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平的問題。單純的“自由放任”政策並不必然能實現這些結果,所以儒家一直努力追求“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之間的動態平衡。在實際的經濟發展中,到底應該是“自由放任”多一點還是國家干預多一定,沒有一個固定的界限,而應根據當時的社會問題和實際需要調整政策。但無論何種情況,兩種政策必須保持相對的平衡。不然,要麼導致國家力量不足,要麼導致社會貧困,最終加劇整個社會的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