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近年來,中國的聲音藝術展覽不斷涌現,如由摩登天空BADHEAD廠牌主理人張曉舟與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副館長尤洋共同策劃《園音》,策展人歐寧策劃的《原音:太原的地方聲景》和《地方音景——蘇州的聲音地理》等展覽。這些聲音作品既有別於當代藝術主流的視覺傳達方式,又區別於傳統音樂的聲音媒介形式漸漸被更多觀眾所關注。但對普通觀眾來説,圍繞著聲音藝術仍有眾多迷霧,比如聲音藝術與傳統音樂有什麼區別、聲音藝術關注的方向、聲音藝術家的創作願景和實踐,普通人如何參與聲音藝術等等。聲音研究學者王婧不僅是聲音藝術理論權威,也親自參與了多項聲音藝術創作實踐,同時,她也進行了多場聲音藝術科普演講,對觀眾迷惑的聲音藝術問題有深入淺出的解答經驗。近日,王婧接受了藝術中國記者獨家採訪。

王婧
如何理解聲音藝術
藝術中國:可能很多人會有疑問,聲音藝術和音樂是什麼樣的關係?
王婧:這很難一下子説清楚,有的時候同一件作品即可以被當作音樂也可以作為聲音藝術。聲音藝術的概念比較模糊,一個原因是傳統意義上也早就有聲音藝術的叫法,比如播音、朗誦。我在學校教書,能時不時感覺到大家對聲音藝術日常意義上的理解,比如有的同事認為我可能是教唱歌的,或者是做電臺的,這是他們理解的“聲音藝術”,我想這代表了較多人的印象。但也不能説唱歌就不是聲音藝術,因為聲音藝術裏面也有關注嗓音(voice)創作的,也有無線電藝術(radio art)。但我們所説的聲音藝術確實和傳統的不一樣,比如傳統音樂要識五線譜,學習和遵守器樂演奏的既定規則。而當代聲音藝術的一個起源是對音樂經典的一種反抗,它想挑戰傳統音樂的定義。激浪派的事件樂譜(event score),也是音樂(music),但通常會被劃到sound art(聲音藝術)裏面。聲音藝術有時候也用於表達一些政治態度,它與其他類型的當代藝術都有共通之處。

中歐聲學生態網路,R. Murray Schafer 圖片來源:網路
藝術中國: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聽從大自然中採集來的聲音,這算不算聲音藝術?
王婧:你説的是田野錄音或者實地錄音。聲音藝術有幾個源頭,一方面根植于先鋒藝術,同時聲音藝術發展到今天,與聲音技術、聲學發展是分不開的,比如各種特殊功能的錄音機、話筒的技術更新,這些才能讓我們有可能去錄各種聲音。除了先鋒藝術作為一個源頭以外,它還是藝術、音樂和科學的跨界學科聲音生態學的衍生。聲音生態學強調我們如何從聲音的角度去研究自然環境,城市鄉村變遷等問題。它跟音樂的關係還是挺緊密的,提出和推動聲音生態學(acoustic ecology)的默裏·謝弗(R.Murray Schafer)本來就是一位作曲家,他的聲景作曲(soundscape composition),是將錄來的環境聲音作為聲音素材,在其基礎上作曲。

John Cage 圖片來源:網路
當然還有實驗音樂(experimental music),實驗音樂與聲音藝術的關係也十分緊密。有這樣尷尬的局面,傳統科班音樂人可能會不承認實驗音樂是音樂,又有當代藝術家認為實驗音樂不是藝術而是音樂,所以有時候,實驗音樂就似乎成了一個獨立門派。但它也不時被歸為聲音藝術,很簡單的一個原因是做實驗音樂的人有很多都是聲音藝術家(sound artist)。當然也有實驗音樂人拒絕聲音藝術家身份,他們覺得白盒子式的當代藝術是資本化的藝術,這裡就不展開説了。
什麼算是聲音藝術?其實答案一直在變化。早期國外的藝術學院中,聲音藝術歸於雕塑係,也就是説聲音藝術作為一種塑形藝術。近幾十年,已經開始有獨立的聲音藝術(sound art)專業。聲音藝術中也有越來越多人在做網路聲音藝術,還有將聲音藝術與歌劇結合,女歌劇藝術家(Juliana Snapper)用非常規的發聲方式去表演歌劇,倒立、水下發聲等等。我覺得凡是用聲音素材做一些藝術上的實驗創新,都可以把它很鬆散地描述為聲音藝術。名稱只是為了傳播與溝通之便,並不應該成為具體藝術作品創作上的條框。

《聲音與感受力》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藝術中國:您曾經在演講中提出不贊同“聲景”的概念,認為聲景和視覺聯繫比較多,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判斷?
王婧:其實我並不反對視覺,聲景(soundscape)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應用範圍也很多,但如果作嚴肅學術討論的話,它有一個認知範式的錯誤,它還是在用視覺思維去理解聲音。聲音和光是兩個不同的媒介,聆聽和觀看是兩種不同的感知方式,聲音與聆聽可以帶給我們不同的智識範式,如果我們還用基於視覺的認知範式去詮釋聲音與聆聽,是不是挺可惜?這是我質疑“聲景”的主要原因。
聲音藝術與當代文化
藝術中國:您曾經説過,在某些原始社會,如非洲的桑海和大洋洲的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雨林部落中,聲音對當地人更為重要,而在城市系統裏,視覺遠比聽覺更為發達,這是為什麼?
王婧:我們建構的環境會塑形我們的感知方式,城市幾乎都是以視覺為主的方式去組織的,城市中傳達訊號和規劃的方式大多是視覺化的。據我了解,建築師在設計建築時,基本上不太考慮空間聲音的問題。城市中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構建的環境中,為了生存、適應環境,無形中我們的視覺訓練就更多,也會變得更發達。但國內也有很多不同於城市的環境,比如我經常去的西北戈壁灘、沙漠環境,在那裏就會立刻發現視覺上並沒有那麼多資訊需要處理,反而需要更多地去聽甚至去聞。而熱帶雨林本來就是一個視覺很受干擾的地方,茂密的樹木、霧氣等等,要生存下來要更多依賴聽覺、嗅覺和觸覺。所以感知方式與感知能力與我們所處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1979 年 7 月 1 日,新力的Walkman 發佈——作為第一款攜帶型磁帶播放器,它徹底改變了我們聽音樂的方式。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的迪克劉易斯/紐約每日新聞檔案
藝術中國:您曾經提到過英國學者Michael Bull一個觀點,他認為和之前的家庭客廳廣播式的聲音相比,隨身聽更加個人化和私密化,這種聲音設備的整體轉向,對於整個社會或者時代性的影響,是不是非常重要?
王婧:當然,從廣播開始,聲音設備就開始改變我們的家庭結構甚至文化結構,然後再到隨身聽,變化更加明顯。存在這樣的批評,認為年輕人經常戴著耳機聽隨身聽,不與他人交流,每個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個bubble(氣泡)。我覺得未來隨著聲音技術的發展會有更多的社會文化影響,例如將更廣泛用於社會監控和管理的聲紋技術(voice print)等等,都會改變我們的日常行為甚至社會文化結構。
藝術中國:目前網際網路音樂對人的影響就很大,人們在網際網路音樂平臺上聽音樂,大數據會不斷推送你喜歡的某類音樂,另一方面,這似乎也遮蔽了你對其他音樂欣賞的可能性,您覺得這樣的技術是否會造成某些不利的影響?
王婧:現在音樂平臺上的推送演算法不斷在增強你的某一個品味與認知方式,在我看來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正在單一化你的審美感知。我覺得人需要不斷地豐富自己的審美品味和認知,要不斷去突破自己的舒適區才能夠擴展世界觀。
我自己儘量避免依賴這種音樂推送,我一般聽音樂都會主動去挑選,隔一段時間我會找一些自己從來不聽的音樂,也是儘量減少習慣於自己一直聽的東西。這就像旅遊,你見過的人和你覺得異樣的事物越多,視野就會越開闊。永遠在一個地方,所有的東西都是越來越熟悉,越來越安全,心中的墻很可能就會越來越牢固、越來越高。
中國聲音藝術家

《天堂向下》現場演出,2017
藝術中國:您一直對中國聲音藝術家做理論研究,您認為這個文化的集群,不像中國早期的搖滾音樂宣揚的那種核心精神,是某種感性的、精神的、更加基本的需求促使他們進行各種聲音實踐活動,這其中涉及一個關鍵詞—自由,如何理解這兩者的差異?
王婧:“自由”是我博士論文的題目中的關鍵詞,就像電影學院的學生拍的第一部片子,可能都會與墓地、死亡的主題有關係,我覺得自由對當時的我來説意義重大,自由是一個我自己當時很想弄明白的概念,但也是因為在田野調查中,我發現自由這個詞眼出現的頻率非常高,不光訪談中,在活動海報上,不同城市的演出場地也可以看到。我對自由的解讀並不是政治性的,它是身體式、精神式的。

顏峻在《原音:太原的地方聲景》的作品,圖片來源:千渡長江美術館
崔健其實是一個非常知識分子式的搖滾樂手,他有社會責任感,他的歌曲裏面傳達的是公知式的資訊。聲音藝術家顏峻也有知識分子氣質,但是他的批評又跟崔健式的不一樣。殷漪也關注公共性,公共空間問題,這是很有政治性的議題,顏峻和殷漪在作品中更多的是反思性和批判性,表達方式更加含蓄。批判和批評還是不一樣的兩件事。概括地説,聲音藝術並不像90年代搖滾樂那樣,沒有那麼直接的政治性表達,也有不少聲音藝術作品純粹追求某些特殊的聲音發聲方式、聲音質感,甚至通過聲音傳達某種宇宙觀等等。我個人覺得聲音藝術家的創作訴求要超出政治性,當然肯定有政治性,但是完全不同層面的,它更加豐富,這可以説是一個整體知識結構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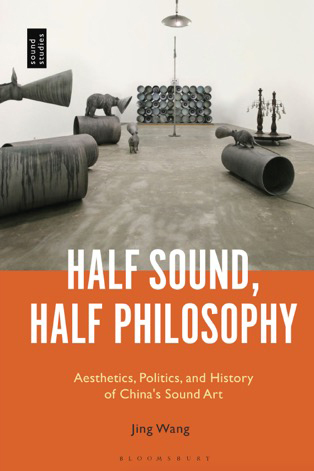
Half sound,Half philosophy, Bloomsbury, 2021
藝術中國:您對於中國聲音藝術史做過詳細研究,您覺得國內的聲音藝術家相比于國外有什麼樣的特點?
王婧:我的新書Half Sound,Half Philosophy (2021)裏面也在集中寫這方面內容。在美學和精神敏感性方面,中國聲音藝術家是有自己的特點的,比如其中一章我寫了實驗藝術和山水精神。實驗音樂中如何體現出這種山水的思想脈絡,我覺得這是中國實驗音樂的一個特點。另一點是中國的聲音創作中有一部分趨勢或者敏感性是捕捉那些怪異的、神秘的、魑魅魍魎的東西。我書中將這些趨勢和敏感性,一方面跟中國古典文化的一些元素關聯,一方面也和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巫術當代化關聯。現在的一個學術趨勢是關注後人類,跨物種問題。而後人類和跨物種最早就出現在巫術裏,中國古代那些鬼故事裏面的狐仙啊,還有聊齋故事啊,其實就是跨物種的,後人類式的想像。這些趨勢反映在創作中就會呈現出一些特別的美學特性。當然我在做作品分析的時候,還是儘量避免過度地誇大中國聲音藝術,事實是,與中國以外的、尤其歐美的聲音創作量相比,目前國內優秀的聲音藝術作品數量並不多,還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但是,個性與特點已經在慢慢地展現出來。
古代聲音藝術
藝術中國:您對中國古代的聲音也做了深入研究,這裡也會涉及到山水、宇宙觀這些問題,一般人對中國古代聲音可能更沒有認知,這個能給大家介紹一下嗎?
王婧:我做古代的東西,也是因為我想從學術上重新提出一個新的認識聲音的哲學系統。我在新書裏就提出中國古代聲音的哲學是“氣”的哲學,中國古代的聲音觀或聲學觀是根植于“氣”的宇宙觀和氣的哲學。這方面古代的文本中論述不少,我現在只是做了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我在書中已經做的就是去總結一些關於中國古代聲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這些聲學技術如何跟“氣”的哲學相關,“氣”的哲學如何去引導和形塑各種各樣的聲學技術。這樣做也是為了論證,我們可以從“氣”的哲學出發,去重新理解聲音,重新理解今天中國聲音藝術家的創作。

敦煌榆林窟聲音錄製,2017
藝術中國:您曾經對敦煌文化中的聲音做了大量研究,比如聽經的部分,一般人只是從圖像認識敦煌,從聲音角度研究敦煌還是非常新穎的。
王婧:對,2016年開始我就想做敦煌的聲音研究,我開始是申請一個小項目,進展也不是很順利,因為我覺得敦煌的東西越看越多,看不完的感覺,目前還在弄,也是因為敦煌的聲音研究的啟發讓我有了太原那場聲音表演的想法。敦煌藝術中有很多跟佛教有關係的密語,咒語等等。還有就是壁畫形象中出現的與聲音和聆聽有關的元素。
藝術中國:中國古代音樂和現代音樂不太一樣,比如中國的禮樂文化強調音樂在古代有很重要的教化功能,這方面您能説下嗎?
王婧:這方面我沒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但在書中也是有涉及的。可以説中國古代儒家的音樂思想的政治功能遠高於娛樂功能。除了儒,還有道。道教音樂主要就是養生修仙,比如“哮”,“哮”在古代道教是一種養生的發聲技巧,它並不是唱歌表演。
聲音與地方

浙江聲音項目,小組播客錄製 2017
藝術中國: 2015年,您在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創立了“聲音實驗室”,致力於孵化跨學科聲音實驗項目,這方面能簡單説説嗎?
王婧:那個聲音實驗室目前主要做一個比較長期的項目,就是收集浙江的聲音,想做浙江的聲音檔案庫,我會不時地邀請藝術家,錄音師、音樂人一起去我們想去的地方錄音。每個人有自己的錄音方式,每次錄完以後,我們會對田野錄音的技術和一些相關的問題作一次討論,最終這些討論是想作成一個播客節目。目前整個計劃因為實驗室裝修、搬遷,以及疫情原因暫停了一段時間,還沒有完成。

秦思源《時言》
藝術中國:去年您參加了《原音:太原的地方聲景》,這個展覽涉及到聲音與地方的關係,當時形成了一個比較熱的討論現象,您在展覽中負責哪些工作?哪些藝術家的創作給您印象較深?
王婧:這個展覽是歐寧老師的項目,他也一直很關心地方、烏托邦、鄉村這些主題。太原這個地方古建築很多,文化歷史也獨特,所以《原音》希望從聲音的角度作一個關於太原的展覽。我當時是因為參與了歐寧老師策劃的在蘇州寒山美術館的聲音項目,然後歐寧老師又邀請我參加太原這一次。我跟大家一起考察太原各個地方,去看著名的歷史建築,聽地方戲曲、非遺音樂等等。在太原,我的主要角色還是學者,提供學術方面的資源,然後跟藝術家一起討論,我覺得藝術家大多數都能夠意識到一個問題,如果不是生活在太原,只給一個星期或幾個星期的時間,讓你去做一個跟太原地方相關的聲音作品,是很難的事情。
我看到藝術家在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也其實都有一個共識,就是不想直接把在田野調查期間錄來的聲音做成作品,因為這些聲音與藝術家之間的關係是可疑的。聲景創作常見的做法是去到一個地方,把此地的聲音錄下來,再用不同的平臺呈現,比如數位地圖(digital map),首先將聲音素材上傳到Google map,作出一種視覺化的可點擊的“聲音地圖”。再或者把聲音收集來,做成比如可互動的聲音地圖裝置(sound map installation),觀眾走近就會聽到聲音。但這次大家都在避免作這樣的作品。
我們當時第一次在太原作田野的方式其實有點兒像旅遊團,有一個嚮導帶著我們去主辦方認為我們應該聽聲音的地方。當然我覺得主辦方是花了很多心思帶我們去各種地方,去認識各種各樣的人和事。這些資源是很好,沒有問題,但是這些資源一下子無法與藝術家關聯起來,要轉化成作品就很難。這次基本所有藝術家的作品最終也都是在其本來的系統中的,與藝術家自己有關聯,這種關聯體現在主題、情感、或者聲音的美學的連續性上。

孫瑋《聲寺》
藝術中國:也就是説,聲音與地方的關係上,聲音藝術家還是希望有一個自由創作的空間。
王婧:我覺得藝術家需要找到這個聲音跟他自己的關係,否則就變成了宣傳運動(propagandism)了。我覺得所有藝術家都有這個意識,最後呈現的作品都跟藝術家自己的創作脈絡有一些關係。比如秦思源一直關注的是聲音與記憶的問題,他在做北京特色聲音的收集工作,收集那些即將逝去的聲音,他在太原也是延續相關的主題,作品是請太原的語言學者用晉方言朗誦山西古代唐代到清代的文學著作,這是關於方言的聲音與地方文化。還有孫瑋的作品《聲寺》,視覺上比較引人注目,它是一個巨大的倒扣的漏斗形的裝置作品。孫瑋是一個對聲音感知很細膩的藝術家,他長期做田野錄音。這件作品的聲音來源是寺廟暮磬的聲音,孫偉把400赫茲以上的聲音處理掉了,這種細微的詩意的聲音美學是貫穿在他的很多作品中的。我們在太原的第二次工作坊時,我跟他是一組的,我個人對太原煤礦的歷史很感興趣,我們去了煤礦博物館,我覺得聲音、能源和地理環境的關係很有意思,當時就想“誘導”他去做一件跟太原煤礦相關的作品,我們也去了考察了當地的煤礦廠。但他最後還是作了和他最有關係的作品,我覺得挺好的。
聲音藝術實踐

即將到來的公共空間,聲音影像裝置,2016 上海當代藝術館亭臺項目,A-Sphere 2016

17.8°C,A-Sphere,2014年,田野錄音專輯
藝術中國:您除了做聲音學術研究以外,您也直接參與了很多聲音藝術實踐,比如您與杭州的新媒體藝術家鄧悅君做了一個組合A-Sphere,一起合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和澳大利亞全女性的實驗音樂人參加了《女兒書》(The Book of Daughters)演出,您參加這些演出是出於對聲音藝術的熱愛,還是一種理論的實踐需求呢?
王婧:我自己是有創作欲的,也可能是因為自己對創作的興趣導致延續做這方面的研究。我的創作方式很多時候是理念先行,我通常的想法輸出就是文字,寫成論文或書,但是很多時候文字輸出的東西,我並不覺得很對,所以我覺得藝術創作作為一種理念或者情緒的輸出對我來説是一個挺好的平衡,所以我很喜歡和享受創作。

女兒書表演 2017
藝術中國:您給大家的印像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很難想像您在做聲音表演時的狀態,您的表演能介紹下嗎?
王婧:我的表演都是首先會有一個比較抽象的理念,基本上會設計一個簡單的發聲機制,再加上我自己的人聲完成現場表演。《女兒書》的表演,我當時在思考如何用聲音的方式去表達精神分析裏面的一些核心的病症,比如弗洛伊德認為女性有一種叫做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精神疾病。那段時間,我在寫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我當時的創作就想如何用聲音現場表演的方式去表達或者闡釋女性和歇斯底里症的關係。我作了一個小的發聲裝置,也是偶然機會在校園散步時撿到了幾根有分叉的樹枝,我用它們作骨架,上面綁了一些乒乓球,在乒乓球附近擺放了一些可以敲擊發聲的界面,用一組小風扇來吹動乒乓球,我可以控制風扇風的力度和開停,讓這些乒乓球跟平面做碰撞。同時,我自己寫了一個聲音文本,關於歇斯底里症的,類似于聲音詩,我會用人聲表演出這個文本。那場演出是我和澳大利亞的實驗音樂人James Hullick,瑞士的聲音藝術家CharlotteHugs的即興表演。

voices within 2021.8 《原音》 攝影:張安定
藝術中國:您最滿意的聲音表演是哪一場?
王婧:我還是挺喜歡在“太原原音”展覽中的表演,我接下來的創作還想繼續延展這場表演。太原那一場表演叫“Voices within”,當時我寫完第二本書,開始思考“默讀”和“祈禱”的聲音問題,比如我們在過生日許願的時候,腦子裏會有一個聲音,別人聽不到,但是你知道這個聲音存在在那兒,我很好奇我們在心中發出這個聲音的時候,是在跟誰對話,還有,我們在看書默讀的時候,腦中的那個聲音的功能和內容是什麼?當時就在想這些問題。“Voices within”的裝置部分很簡單,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在想究竟用什麼工具去表達無聲的聲音,忽然就想到蠟燭,蠟燭常用在祈禱、許願中,發聲的氣流會影響蠟燭火焰的跳動,而這種跳動正好是旁人聽不到的聲音的節奏載體。跳動的燭光證明聲音的存在,使用蠟燭也正好滿足了我不想在現場使用音箱擴聲的想法。我就決定用蠟燭做演出的主要的樂器,用錄影機實時投影燭光。我的聲音表演內容是自己寫的散文詩,夾雜著不同宗教的各種常見咒語,表演現場是全黑的,只有一個投影,一根蠟燭。
藝術中國:對於那些對聲音藝術感興趣的朋友,他們怎樣去實現聲音藝術的創作?
王婧:我覺得聲音藝術創作除了進入藝術展覽或者藝術市場以外,還有療愈的功能。有很多方式可以進入聲音創作,比如現在人人都可以錄音。在錄音的過程中,創造力就發生在你決定錄什麼、錄的方式、以及錄音用來做什麼。可以憑直覺去錄你喜歡的聲音,可以用最簡單的聲音軟體去處理這些錄音,可以作簡單的聲音拼貼,即使沒有音樂教育背景,也可以作曲。也可以用錄來的聲音或者你自己的人聲,配合自己的攝影做成影音作品。這是可以用手機去嘗試創作的。再複雜一點,可以做發聲裝置,改裝一些小玩具等等,實驗音樂中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酷的自製器樂,可以先多了解一些。

Pauline Oliveros,圖片來源:White Fungus
還可以嘗試聆聽。比如我自己上課的時候經常帶大家去做深度聆聽練習,深度聆聽是美國實驗音樂人保琳•奧利維洛(Pauline Oliveros)提出的一套方法,奧利維洛與約翰· 凱奇(John Milton Cage)是一代人,她使用的是手風琴。她通過各種各樣的小練習,讓我們體驗深度聆聽自己的身體,聽周邊的環境。
即使是沒有時間專門去一個戶外的環境,也完全可以作聆聽練習。我有一個技巧就是,自己下意識地把當作資訊聽的聲音當成音樂來聽(即information turn to background music),或者反過來。這就是一個日常生活中我們隨時隨地可以做的聽覺模式轉換練習。
(受訪人:王婧,採訪人:劉鵬飛,圖片來源:王婧)

王婧,藝術人類學者,聲音研究學者,聲音實踐策展人。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 MIT 人類學訪問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訪問學者。美國俄亥俄大學跨學科藝術博士。出版專著《聲音與感受力:中國聲音實踐的人類學研究》(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 通過對中國聲音文化的人類學研究,探討了自由、情感和聲音的概念。最新出版專著《Half Sound, Half Philosophy: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China's Sound Art》(Bloomsbury, 2021)。在國際學術期刊包括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Representations, Leonardo, Leonardo Music Journal, Journal of Popular Music Studies, Organised Sound 等,在國內學術期刊包括《新美術》,《音樂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目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聲音研究,感官研究,藝術人類學。2015 年 1 月創辦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聲音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