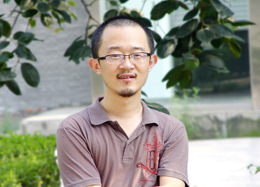
本文原題為《民族主義情緒下的理論黑洞》,寫作與2002年6月(當時我對所謂的批評界沒有任何興趣),是當時看了王南溟的所謂的“後殖民主義批評”系列罵人文章後寫成,後曾組織在其他文章中予以發表。算作此次對王的回應。
世紀之交,中國的文藝界碩果纍纍——1999年蔡國強在48屆威尼斯雙年展上獲得金獅獎,2000年劇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同年李雲迪獲得肖邦鋼琴獎。這樣三項國際藝術界的最高獎一時集中于華人身上的現象可謂絕無僅有,但是當時國內的文藝界對這三項獎項的反映可謂有天壤之別:高行健的得獎引起了中國文學界的集體抗議,最直接的反應是認為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仍堅持意識形態的對抗論,評審受著某些大國的控制;蔡國強的得獎則直接引發了四川美術學院的控告,認為他的《威尼斯收租院》侵權,更甚之,有些批評家認為他的“火藥”系列作品在打“國牌”,從而換取藝術上的成功;而李雲迪的得獎則得到了大量的讚譽。
極為類似的獎項為何有著極不相似的評價?李雲迪獲得演奏獎,他是將西方古典曲目加以表述、闡釋,有些人認為:西方古典音樂評判標準以及權威在西方,那裏有古典音樂的完整機制,因此做為一個中國人在古典音樂的演奏方面獲得最高獎是值得國人慶賀的事情!只要過激的民族主義者還沒有將古典音樂列入“西化、後殖民主義”的行列,那麼他們在這裡就無法找到闡釋自己理論的地方。而蔡國強的境遇卻沒有那麼樂觀,有一些人認為蔡國強在打“中國”牌,暗含之意是他在把老祖宗的東西顯擺給外國人看。面對蔡國強的作品以及成功,處於弱勢國家中的國人很容易想到:女人是如何展現自己的“女性”特徵向男人獻媚並得寵的!那麼按這種邏輯,任何弱勢國家的藝術家的成功都是一個錯——無論你的藝術手段是什麼,問題是你是“女人”!問題已經遠遠跨出藝術領域,泛政治化的思維模式已經牢牢套住了一些批評家,這樣在批評界就形成了一個深不見地的理論黑洞——民族主義假像下的失重心理。
建國以來,美術就被塗抹了過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70年代的“星星畫展”,80年代初期關於“形式”問題的討論,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等事件都和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了深層的理論敏感區,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80年代特殊的政治環境使許多人都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官方批評家以及民間的理論家都有意或無意地結合或分裂美術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從而贏得自己的話語權,時隔十幾年,文革思維模式在評論海外藝術家的批評家言語中仍可以察覺到,只是批評家穿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拿的是“後殖民主義”的大棒,整個套用的是文革批判文章的思維模式——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倒在地!
一戰以前,西方藝術中心在巴黎,二戰後轉到美國紐約,藝術家向藝術中心的靠攏本屬於無可厚非之事,難以設想如果1917年康定斯基不離開蘇聯,他以後的藝術發展道路會是什麼樣子?那麼為什麼在海外成功的藝術家在國內就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徐冰的藝術作品被列入美國美術教科書,蔡國強被日本人所崇拜,黃永砯被選為代表法國國家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五位藝術家之一,這些成績是民族之榮還是民族之辱,我想諸位自有公論,如果招來的仍是國內的一片罵聲,我想我們應該反思:是不是我們的腦子裏有了一點貴恙?
“墻內開花強外香”可以忍受,為何“墻外開花墻內香”就那麼難以接受?有些批評家總是要從美術作品中發現可以揮大棒的理由?可悲的是,一些批評家在評論藝術品時,“民族主義信念”極度膨脹,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外衣下面隱藏的是兩樣羞于見人的東西:利益分割的失落、文革思維的慣性。也正是這兩點構成了這些批評家“民族主義情緒下的理論黑洞”。
“全球化”似乎已經席捲了全球的各個角落,不知何時,我們的神經開始變得脆弱起來,乞丐面對施捨者的“廉者不吃嗟來之食”的舉動似乎就完全代表了民族自尊心,任何弱勢國家國人的成績都似乎使“民族主義者”的神經近繃起來,“我們也可以這樣子嗎?”——這裡隱藏的是對自己民族能力自信心的徹底喪失,他們一方面吹捧民族文化的偉大,另一方面在面對一些藝術家利用民族的智慧取得的成功時卻大加指責,理由自然是“販賣民族符號”,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批評家缺少的恰恰是對自己民族的自信,有的只是窩裏鬥的衝動——奴性真正表現!
在國際的藝術生態系統中,我們的一些藝術家扮演了強者,這可能是最大的錯誤。黑洞不是真空,它有著巨大的品質和吸附力,我們的理論黑洞裏面隱藏的是什麼呢?他使“星體”消失的能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