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代中國畫壇,的確有著某種兩難處境:或者是繼續著傳統的程式,傳統的審美習慣和標準,傳統的工具和材料,這種較為保險的做法較易受到展覽中評委們的肯定,也有相當的群眾基礎,甚至,也可能有畫商光顧,賣個好價錢。但沿襲著與傳統大同小異的面貌,要在成千上萬的也是大同小異的、甚至技巧也可以是不錯的“國畫家”們中樹立起自己鮮明的個性十足的藝術形象,卻是相當困難的事。尤其是要在各類條件大體不變的情況下有較為突出的新意則更困難。另一類畫家則以打破既有的傳統程式、審美習慣,乃至改變工具和材料,試圖立足於民族繪畫的一些基本的因素,大刀闊斧地改革中國畫。但對這些畫家的學識、修養、膽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非此而不可能在真正的中國畫改革上闖出一條紮實的能經受歷史考驗的獨特之路來,儘管掉花架子,逞怪炫奇,徒務新奇以唬人倒也容易。這條路子,新則易新,但容易怪誕。綜觀現當代中國畫壇,大致可分為這兩大類。兩類中又都各有其傑出的代表。前者可以齊白石、黃賓虹為代表,後者可以林風眠和潑彩後的張大千為楷模,而當代畫壇風雲際會,波譎雲詭,中青年一輩畫家或精研傳統,欲以功力勝人;或變革觀念,時出奇兵,以新標高;更有搬來外國東西“狐假虎威”者;當然,綜合多種因素而出以創造者大有人在…… 以此畫壇背景去看何水法先生的花鳥藝術,或許會有個更準確的印象。

何水法先生應該説屬於那類知難而進,硬是要在傳統繪畫的範疇內闖出一條新路來的人。何水法的花鳥畫屬於由明代末期陳白陽、徐謂開其山的水墨大寫意花鳥畫一路,當然也是此後比之山水畫逐漸佔據上風的文人花鳥畫一路,這是一條可以從陳白陽、徐謂、八大山人、揚州畫派李蟬、李方膺及清末吳昌碩集其大成的海派諸大家一直數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的大師輩出,才濟濟的道路,也可謂擁擠而難行之路。這基本上又是一條講究文人素養,以筆墨的功夫為主,詩書畫印結合,程式化頗為分明的有著較為確定的藝術標準的道路。唯其如此,要在這條路上獨樹一幟又何其難哉!何水法先生的花鳥畫的確比較多地屬於這種文人花鳥畫範疇。在這個領域,何水法先生無疑應屬佼佼者,他有著較強的筆墨功夫,把各種關於筆墨的優秀評價加之於他的花鳥畫應該是不會錯的;他又有極好的全面的藝術修養,詩、書、畫、印諸般皆精,這在當代中國畫家一輩當屬少見,大有江南才子的氣度;其畫講究意趣,文氣十足,這在當今文化尚且不足,奚論修養的同輩中更是翹楚之才…… 如果説,這些需要花費長期的修煉方能得到的長處已經可以讓一位畫家有其立身之本,那麼、作為一位名家,或者,更準確地説,作為有創造的能獨樹一幟的著名畫家來説,這就僅僅是一個應有的基礎。作為真正的名家,還應該有其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個性表現之所在。而何水法先生的花鳥畫本來是有著這種一望而知的個性特色的。這個特色,我以“雄秀”二字概之,以“雄”而稱名者多矣,這幾乎就是當代風氣,為稱其雄,畫法愈來愈放,愈來愈野,畫幅也愈來愈大,大到美術館難於陳列。放、野、大好辦,中下才智的人都不難辦到,但是要在放中有收,野中有雅,雄中有雅,雄中有秀就非才氣橫溢具上智之才者而不能。
何水法的花鳥畫的確有一種雄強大氣的氣概。他的用筆儘管仍偏中鋒,但卻並非吳、齊、潘那樣較為嚴謹的書法中鋒,而是多用枯筆,多飛白,多“毛”,這是一種或凝澀頓挫,或迅疾飛掃,多牽絲露白,呈現巨大力量和強悍氣勢的個性化用筆方式。比之同樣用枯筆講究“毛”、“澀”的典型的“四王”用筆來説,後者仍然氣韻平和、中庸、有板有眼,而前者顯然多了若干氣勢、力量、強悍乃野霸。這無疑是其“雄”風之所在。然詳視其用筆,何水法又極盡變化之能事,我們很難在其畫的任一局部找到一以貫之缺乏變化的筆線。一筆之中變化無盡,筆與筆間變化無盡,這就是一種精微的安排、細膩的處理,耐人咀嚼的藝術魅力,當然也是雄中含秀之所在。或許,這種強悍大氣而又以雄為主,雄秀兼之的用筆,也的確突破傳統文人畫那苦澀的嘆苦嗟卑的傳統型個人情結,,而帶上了某種如火如荼的現代情感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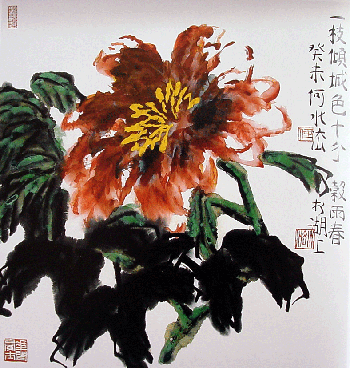
就“墨”法而論,要説何水法諸般墨法皆精,也決無誇張溢美之嫌。但我認為,水法先生之“水法”則猶精。的確,水法長于用水,他往往大潑其墨,而水意盎然。他更多的時候似乎是以潑色去代替潑墨,他的潑也是水意點濃重,而且,與其虎虎生風的強勁用筆相諧和,他的潑墨與潑彩也同樣有一種翻江倒海飛雲播雨般的淋漓痛快氣勢。他的潑墨潑彩往往由於含水量大,而呈現某種淋漓朦朧之狀,儘管何水法精研過宋畫工筆、也長于花卉寫生。但他卻一任情緒的宣泄,在“潑”中取氣取勢,而弱化形似的準確。這種大“潑”其墨其彩之法顯然是使其“"雄”風依然。有趣的是,儘管何水法的大寫意花卉並不斤計汁較相似,但其“水法”卻極為講究。色、墨、水的乾濕濃淡變化安排,色墨在形態和色相墨相上變化多端的水痕色跡墨印的交錯、重疊、嵌合、滲潤,都給這種潑辣雄肆之風增加了幾許細膩與精微。尤其是那大量色彩的潑灑與點垛,那明艷的迎春的嫩綠,金桂的金黃,紅楓的赭紅,牡丹的燃燒的紅花,金黃的花蕾和明麗的綠葉,卻在一片淋漓恣肆的潑墨潑彩中憑添幾多嫵媚。值得強調的是,何水法先生的花鳥畫這種雄肆之風還得力於他的別具一格的構圖。傳統花卉畫多為折枝式,或一枝獨秀,或二枝交疊,或三枝穿插,畫面講究虛、空、白,所謂計白當黑,所以簡潔、空靈者多。但何水法的花卉畫結構卻有突出的個人特色,可稱之為“叢生式團塊結構”。他的畫並非古典式簡潔的折枝式,往往以密集叢生的樹榦、花枝密密叢叢地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直楞楞地撲向畫面,然後又舒枝展葉著花,朝四面延展鋪開,構成佔據絕大部分畫面的一大團團塊結構的花叢或樹叢。這種與傳統結構大相逕庭的現代花卉畫結構,充滿著堅實的團塊的力量,又有著分明的向四方擴散的張力。這當然又構成了一角度的雄肆之風。自然有如何水法對筆墨色水的精微處理一樣,他的這種雄放的結構同樣有著精微的處理。由於何水法十分注意結構的虛實關係——這本身就是他熟捻的傳統章法分章部白的手法,再加上他大量使用明快的色彩,這種淺色度的色彩和深黑的墨線、墨塊之間除了可以共同構成團塊之外,同樣也可以構成因色度而分明的虛實關係。這種聰明的做法,使其結構因堅實的團塊而新穎,又因此而和傳統章法保持著審美情趣上的聯繫。
何水法先生在傳統文人畫基礎上的創造是令人饒有興味也頗具啟發性的。他繼承了文人畫的從審美到形式技法的許多重要的因素,又對其進行了若干或大或小的改進,使這種古老的繪畫樣式在表現當代人的情感和情趣上再現出迷人的現代魅力。歷史是在承傳與變革中前進的,何水法先生對文人花鳥畫的變革與再創造,則對傳統繪畫的現代轉化之可能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
(作者:林木,四川大學教授、美術評論家)